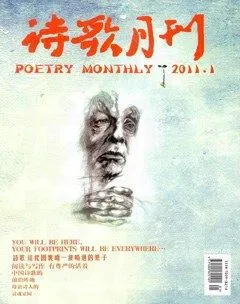郑玲的诗(21首)
正在读你
我正在读你
因为我也有个长夜
读你 如坐春风
去赴酒神的节日
连狂欢的虎豹都拉着载酒的车子
你可以想象得到我的陶醉
人家说 书上印的
并非你真实的名字
管你是谁 被诗选中的人
绝不会为流行时尚精选一副面具
我看见的只是个出远门的
把孤村情结
拴系于月光下的故园
闯入世界之都热恋且冷战
爱与恨 悔与悟
耻辱与缺失都暴君般将你奴役
你挣扎 你奋斗甚至逆来顺受
把自己变成蛹 让痛苦层层包裹
咬破了茧 才开始飞翔
人家以为你天生就有翅膀
其实 是你明白
不管天翻地覆 人 总得要生活
你也明白
胜利不属于个人
胜利属于时间
夕阳的流苏何其绚丽
谁能抓住她飞逝的披肩
低下头来 长跪在无限面前
从苦闷的怀疑中
你找到了神的恩宠
缪斯赠你一支魔笔
你为叹息留下真正的叹息
把叹息化为颂歌
让人类的心灵怡然共处
因此 同情在我们身上
融入血液、目光和手势
我一眼便认出
你就是沙枣树下的那个小弟弟
里尔克的眼睛 上帝的儿童
正在地上画一些秘密通道
并琢磨 该从哪里走出迷宫
我的梦 已飞回那个蓝润的夏暮
为你最初的沉思欢呼!
陶土的灵魂
诗人啊
你的寓言使我震撼
那个被拴在车轭上的童工
和你自己多么相似
那孩子朝夕搅拌着黏土
日夜流着眼泪
火将黏土
烧成精美的陶器
火将眼泪
烧成欢乐的笑声
会笑的花瓶 碗碟
成了稀世珍品
这个非人的人
成了陶土的灵魂
诗人啊 你是不是
也有一滴眼泪在火中凝炼
所以才写出那些无用的
却教人永远动情的诗
我被梦找到
梦比夜长
我被梦找到:
从巴山夜雨中启程
为赴约 夺门而出
鸿蒙未开的那边
沉睡着我盟订三生的爱人
等待我去唤醒
我必须恪守诺言
幸运和厄运
都不能惊残我的好梦
前路微茫不定
傍晚的天空又冥合下来
月亮睁着一只冻僵的眼
望着寥落的篝火取暖
已曾得见一些飘忽的身影
但那种装扮和言语
仿佛是临时人类
道路漫长
经世纪的寂寞
鬼魅的荒原 人面的荒原
荒原永远不诉说
但是 为唤醒而来的步履
不能迟疑
神圣的相约
只能太阳一样如期升起
啃了最后的干粮
盛满红酒的银壶已破
去复活岛的清泉
洗净我身心的尘埃与怯懦
清洁最珍贵
清洁使人面对困顿而自我感奋
向着坚实和完成
春天来了
春风带着鲜花和筑巢的故事
呼唤着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
使我尘沙迷蒙的眼睛
顿然炯亮
老远就看见:
延亘无边的沙浪之中
驶来一艘船
闪光的桅杆上
悬挂着“好梦成真”
我明白 这是幻船
它能载你抵达你的意愿
如果你有能耐
跳上它的甲板
天堂到底在哪一个角落
高更眼中的法兰西
繁华、热烈而堕落
文明使它
失去了生活的神秘
高更走了漫长的路
去沐浴塔希堤的月光和泉水
从蛮荒的白马的梦态里
找到了盖世的瑰丽
他的画笔征服了法兰西
高更临终之前
看着孩子们做游戏
一个孩子问:“天堂在哪一条街”
所有的都回答:“天堂在别处”
这个高贵的野人轻轻叹息:
天堂到底在哪个角落?
我寻找了一生
何曾得见 那苍穹中的
天堂的尖顶!
相遇尼采
散步的时候遇见尼采
他正从湖畔的树林中出来
我想跟着他走
又怕把世情看破
人说他儿童的双眸
曾经把大理石的墙
看得纷纷倒塌
在罗马
在喷泉淙淙的凉廊上
他听到了“夜歌”中的叠句:
“为了不死而死”
百余年后的今夜我也听到了
微妙的战栗传到脚尖
一种蓝天的孤独
逼我再一次和尼采相遇
我仍然想躲开他
但总也躲不开查拉图斯特拉
他从高山下到尘寰
长袍飘举 视线可达星辰
闪电般的雄辩和警句
向着谁也没有预测过的未来
发射!
他把不朽的深度带到我面前
不由你不倾听他
倾听了他 便乱了秩序
我暮年的这块休栖地
不但不肯再作死亡的演习
竟长出莽莽春愁
我的另一个我
在应该结束的时候
突然准备出发
并且想把道路卷起来
随身带走!
普鲁斯特的蔷薇
逝水年华已成追忆吗
河水逝而犹在
普鲁斯特旧居的野蔷薇
盛开如昔
朝圣似的 全世界的人
都来到孔布蕾
为摘一朵普鲁斯特的花儿
佩于心旁不让萎谢
而这个由诗意造成的人
在有眼睛之前就先有眼泪
他自幼被疾病所困
只能把沉沉帷幕撩开一线
窥视天空
但他的目光
并没有茫然若失
痛苦与回忆
做了他的两位缪斯
失去了广度却获得了深度
这个柔弱的人
毫不柔弱地开采了他的矿脉
隔着世纪的黑夜 蔷薇如火
照着我读他的杰作 看见他
以一种重压下的优雅步态
从书里走了出来
明亮的黑色的眼睛
带着淡紫色的眼圈
忧伤 沉默
蕴涵着 大海的负担与忍耐
乔治·桑
她像一股驱逐死亡的春风
穿过肖邦委顿的长廊
即将凋零的花儿
魔化成鸟群
气势如虹地飞向广宇
从那狂欢的琴键之上
梅诺尔卡岛的炊烟
结束了它的黑夜
阳光 白云和清风
向生命向爱情
撒下了音乐之雨
再没有比最能匹敌的人相爱
更为美满的了
可太美满的世界总嫌太窄
未来 悄悄地破坏着现在
这个沉醉的女人的胸襟里
醒着一个无法餍足的天才
天才是独来独往的灵魂
只能自由地服从缪斯
烛光幽微的香巢
岂是终老一生的所在
当两翼生风的黑马
在下弦月的深邃里嘶鸣
她剑一样的灵魂出鞘了
冷不防伤害了她的至爱
于是这位“自由女神”
这位“眼睛如月光”的女人
一夜之间
成了“音乐的戕害者”
成了炸药和引信
历史
总是囫囵地吞下了许多谜
然后长成使人怅惘的词汇
其实 两个人两个星系
相吸又相斥
人间天上从来如此
乔治·桑啊
你是否也曾叹息
你的《康素爱萝》
安慰了那么多心有创痛的人
怎的不能安慰你自己
梦见邓肯
梦啊,请你留个余地
我怕不得醒来了
我的心灵微震
我的凝视幽远
——我梦见邓肯了
邓肯站在海滩上
赤裸着四肢
烟云中飘下一袭轻纱
一条澄川,萦绕着她
受了天启的前额
立即神采飞扬
灵魂的黑眼睛
露出激越的狂喜
柔波的双臂
伸向辽远的天际
她,月光般地荡漾起来了
升浮起来了
不知从何处而来的音乐
在她莹洁的身体内流动
被音乐之雨洗涤过了
这月亮国的女皇
更显得清辉四溢
清辉的流动不可捉摸
比灵感的出没
比花香的明灭还要幻魅
纵使能让石头沉思的罗丹
也难以凝定她舞蹈的风韵
我只觉得她轻纱扇出的微风
平息了我灵肉的创痛
我只看见她轻纱透明的影子
越过世界的原野
所有的高峰
都在她的脚下
最初的崇拜
——怀念一个无名的抗日英雄
记忆的河岸画卷般舒展
一匹黑马飞奔而来
穿过闪光的雨云远去
那个在马背上思想和睡觉的人
今宵要到哪里
我闭目驰神
努力追忆他的面貌
坚挺的下巴略带冷峻
眼睛里的微笑
一缕晴空中的凉风
眉宇间笔直的皱纹
有一种不自觉的尊严
纯粹一个 有家有室的男子汉
他的锚 落在和平的港湾
只因为敌人的铁蹄
踏碎了他的山河
深重的悲痛
凌驾在他全部的情感之上
这个平凡的人便舍己忘我
便去雪耻去救亡
去拼掷他高贵的头颅
何须青史记载他的名字
他和他捍卫的土地一样常青
没有知音的英雄只是偶像
而他 遍地都是知音
我的光荣是:喊他三表叔
我在那研究星星的年纪
需要膜拜这样的人
三表叔到敌人后方去了
这是大人们最兴奋的话题
那阴霾笼罩的峡谷
终年是山鬼悲啼 风嘹月唳
自从一支游击队从天降临
林莽 这个巨大的墓地
脱腐朽而重生
初醒的曙光 恋栈的夕阳
都轮流在这里守护
黑夜的篝火 思接千古
火种里升起的风云
从昔日叱咤到如今
那座峡谷又远又近
近得与乡亲们共一个胸膛
呼啸的牛角 秘密的切口
都在这共同的胸膛里奔突
一切出奇制胜的故事
天籁般抚慰着不眠之夜
驱除恐怖 报着平安
沿着所有的路径
向着所有的窗子
可惜当年我太小了
只能在梦中追随他的马
当我懂得做亡国奴的痛苦的时候
真想到他战死的疆场
抓回一把染着他碧血的黄沙
而我这个未出过远门的幼女
对英雄的血 只能用眼泪铭记
谁知这热血 这泪水
竟是我成长的滋养
当我在人生的逆旅
遭到灭顶之灾
将我复活又将我高举的
竟是这最初的崇拜
所以 我不能说
“今天没有英雄”
我总觉得 透过当代的负重者
昔日的英雄依然带着春光
走进我的严冬!
风的回忆
——纪念蔡梦慰①烈士
浑身绑着匕首的夜,
披着黑色的大氅,
匕首的尖端透了出来,
一排排食人的牙齿
在大氅上闪亮。
这是蜀国的一九四九年的冬夜
淹没在血泪里的最后的日子。
那一夜,
我在歌乐山上愁惨地徘徊,
呜咽着,飞旋着,
去和蔡梦慰诀别!
可是我来迟了,
我的诗人已经倒在松针上了,
他那配戴桂冠的头颅,
为中国的解放戴上荆冠了。
只有那双渊默的眼睛大睁着,
若有所待地望着天际。
从他才华横溢的心中,
流出的每一滴血,
都渗入了大地的胸膛,
大地伸出双臂,
拥抱着战斗归来的儿子。
可是我来迟了,
只能吹下一片树叶
去轻轻覆盖他的伤口。
我怎能离开他呢?
从前,我经常是与他同往的。
那时,蓝色的嘉陵江
从晨光中初醒,一缕阳光
瀑布似地倾泻在水面上,
他站在扬着三角帆的船头,
开始一天辛勤的奔走。
我吹拂着他蓬松的头发,
他吸入我醇酒般的芬芳,
他的心,鹰一样振奋,
飞向高远的苍穹。
波浪竖起千万只耳朵,
谛听他对苦难的生活
唱出的欢歌。
就为了这首歌,
他被关进了黑牢
我从瓦缝里去探望他,
他仍然在唱:
“即使剪了翅膀,
鹰,曾在哪一刻忘记了飞翔?”
听,他的歌声仍在回荡啊,
巍巍的古松啊,
你的枝头栖息过雄鹰,
你最了解鹰的天性,
诗人在就义之时,
把他的诗篇藏在哪里呢?
踯躅在无边的荒原上,
我萧萧瑟瑟地寻找,
找遍了树梢和低枝,
找遍了荆榛和石穴,
终于在一丛蓬蒿中
找到了烈士的手稿。
第二年春天,
蓬蒿中长出一株蔷薇,
两片齿形的大叶,
像带着镣铐的双手,
托起一朵如火的蔷薇。
我被它的馥郁 召唤来了,
我被它的壮丽 征服了
从此,我从这里吹到那里,
做一个传播真理的风媒。
注释:
①蔡梦慰:四川人,新闻记者。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牺牲。在赴刑场途中,他将长诗原稿——《黑牢诗稿》抛留荒草丛中,重庆解放后被发现。
与石像语
总以为你坚不可摧
只能站在山坡下仰望你
如今发现了你的裂痕
才感觉我们是同类
才径直走向你
走近了
细看你头上的桂冠
原来是嵌进血肉的荆棘
怪不得
你要以天老地荒的忍受
来冷酷你自己
走近了
说些什么好呢
虽然心灵面对心灵
是永无休止的潮汐
然而 谁能撷除你的荆冠
时间无能 财富无力
你的痛苦
是与你的艺术同生共长的
不过 我已经走入你的创伤了
又怎能退回原来的位置
我只有 将我的胸怀
碎成一片梦土
浇下我的泪雨
试为你 长出息痛的灵芝
诗人之爱
——祭曾卓
不开追悼会
不作告别①
诗魂远行
大美无言
在你深爱着的这个世界
你曾经输得铁骨铮铮
也许正因为如此
灵柩前的那片月光
才不肯将你悄悄埋葬
从百合花里传出笙箫
那个神秘的王国
派遣光明使者来迎接你了
盛赞你一生为爱而讴歌
洒下满天流星的壮丽
而我们呢
突然失去了你
连旧时的创伤都一一裂开
任何慰藉的香膏均是徒劳
不管你能否听见我们的呼唤
我们的梦魂跋山涉水
幸而知道忘川不是你的归宿
便奔向高峰寻找你的足迹
历史无情 将人变成草芥
历史有情 将草芥变成大树
根 扎在悬崖的缝隙深处②
枝叶 覆盖着天堂
我们打开这传世之作
你便从诗里走了出来
站在苍凉与磅礴的背景之前
一个强劲的率真的天性
尊严 仁爱 兄弟般亲切
依然穿着如茵夫人给你制的
那件玫红色格子衬衫
入世而瓢逸
尤其令人激动的
是嵌于你眼角的
一颗千年的琥珀液滴
那是“老水手”③
用来为浩海的船只镇住风暴的
——一颗大忧患大悲悯的泪
一颗属于人类的爱之泪
它非权威 它不雄辩
更没有刀光剑影
然而它使所有诚实的心灵相信
唯有爱(这内在的光明)
才能教人变成自己
唯有爱(这人性的精华)
才能维系人类的文化永远不死
注释:
①曾卓遗嘱:“不开追悼会,不向遗体告别。”
②③参看曾卓的诗:《悬崖边的树》和《老水手的歌》。
桥上的铜像
火把 枪刺
押着他来到桥上
仍然是那样庄严的天庭
不可辱的眉宇
他手抚胸前
嘴唇紧闭
暴君的大臣
最后一声命令:
说 说出王妃忏悔的秘密
不说 沉江而死!
而他 是神父
——上帝的使者
他倾听过忏悔者灵魂的哀歌
必须忠于职守
出卖别人是自己的耻辱
大节不可夺
当生命与正义不可兼得的时候
还有别的路吗
阴云密布的天空
骤然绽出一道月光
河面上
亮出一条路的形状
他纵身一跳
沉没 升起
他的荆冠永远在水上飘流
崇敬舍生取义的人们
为他铸了一尊铜像
他忧郁的眼神
悲悯地望着这个世界
好似他
刚从合拢的漩涡中
上升起来
晨光中
钟楼里飞出一声洪钟
你又挨过了一个黑夜
天意微茫 难测你的去向
一枝短笛
从背囊里探出头来
仿佛在听
那群马奋蹄的回声
我猜想你
是因为泥足的巨人坍塌
再没有偶像来寄托梦幻
所以要去寻找并完成另一个自己
光与光之间互不相碍
人不能孤立存在
未来的某一天
当我从动荡不定的船上下来
走上信心的大陆
也许能和你
在“吗哪”降临于荒漠之时
惊喜地相遇
背影
他站在山岗上
背影 比山更为凝重
完全浸入深沉的静止
石像似的 一动也不动
在看长河的落日吗
也许江水正沿着夕阳的光线
丰沛地注入他的心中
从那向后飘拂的头发
我看见了他思绪中流动的风
他在想些什么呢
一种参不透的沉默
横亘在我们之间
这沉默 像充满大气的
草木的馥郁
我不愿意把它驱散
虽然 我看不见他的脸
但我知道 他从来没有
比这石化了的时刻更为活跃
那被壮丽山河激起的热情
连同明丽的夕照
都在他的目光中熊熊燃烧
诗与现实的联合王国
(这伟大的双重世界)
已在他的眼前展开
我不敢走近
更不敢呼唤
此时此刻 他属于他的创造
我只能远远地 远远地等待
等待这一尊云石的雕像
如何容光焕发地
转过身来
读一张照片
站在异国的街头
如入无人之境
你的凝眸幽远
想必是那种被史诗和童话
所主宰的人
街头 是梦想出征的策源地
在天空与混凝土之间
你以东方的文静
掩饰着心中的那一团
沉默的烈火
看起来你大概已经领受到了
在大都市里的贫困与孤独
比任何穷荒绝域的生存斗争
都来得更为酷烈
昨宵 你宿在哪里
我仿佛看见你步履匆匆
穿过一街霓虹的光晕
消失在林荫道的尽头
是不是
要找一角宁静一张长椅
去读你背囊里的那本
华工奋斗史
过自己的独木桥
悲伤身上总是有着童年
诱惑人远走的又催促人回归
盲老人眼前一片漆黑
而渴望 高举起
浇了树脂的火炬
回家的路
凌空一条独木桥
那儿有座断崖
如猛兽张开巨嘴
桥下的深渊伸出手来
拽走了多少英雄剑客
但是 儿时放摇篮的地方
不就是人最好的葬身之所吗
他必须回去
谁的一生
都要过自己的独木桥
面对着畏惧这个顽敌
他开始武装自己:
把鞋子脱下
用草绳串起来
搭在肩上
赤足 就有了立锥之地
如同张弓拔弩
把全身的毛孔张向亘古
赤足顿成了猿人的利爪
抓紧了桥身 抓紧了命运
一步一步 向前走去
急流飞石的喧嚣
都消逝天外
他的专注
犹如创世纪太初的上帝
幸存者
幸存者是被留下来作证的
证实任何灾难
都不能把人
斩尽杀绝
戴着死亡的镣铐
走出灰烬
在宿鸟都不敢栖息的废墟
重建家园
不管昨夜的狼烟
如何使你一无所有
当黎明到来的时候
仍然充满感激
因为每个黎明
都给希望准备一个天堂
朝着黎明
走在已埋葬的岁月之上
幸存者不诉说回忆
心中的要塞
沉默如雷:
生活永远始于今天
在应该结束的时候
重新开始!
囚禁在记忆里的画
我把这幅画 囚禁在记忆里
而它 如大漠的飞镝
总是出人意外地发射出来:
乌桕树 鸟巢
落日下一座孤坟
孤坟不孤
守护着它的
是一个老妇的凄怆的眼睛
人对神位的窃据
所造成的那片屠场
早已被春风秋雨清洗干净
无辜者躺在死亡谷里
嘴巴再一次被泥土封上
而这个失去亲人的母亲和妻子
仍然孤悬人海
把被打成碎片的自己
重新拼合起来
每当红日从鸟巢后面坠落的时刻
她便走出篱栅
走入云色风声之中品尝灰烬
围着那合葬父子三人的土堆
上百次 上千次地绕圈
不是几天 不是数年
整整大半辈子
她就这样
睁着一双凄怆的眼睛
围着那座坟墓绕圈
荆棘开花了
刺痛了自己
荆棘喊道:
停住,时间!
神石
枣红的岩石 恐怖
灰黑的岩石 饥饿
苍青的岩石 冷如坟墓
这三个前朝的遗老
每当薄暮时分
等待着一个老妇人
老妇人总是准时到达
轮番坐在这些石头上
坐进生命的初始
深深地 深深地
喘一口气
久而久之
岩石上出现了人的手印
与那已经消逝的
巨兽的脚印重叠
印记的四周
还有些古怪的铭文
或许只有猞猁的眼
才能看穿它们
于是 这座山 成了名胜
旅游业点石成金
有一天寒鸦传递紧急情况
乡长来了 宣布一条禁令:
谁都不许坐在这些神石上
违者严惩!
但同时给老妇人以安抚
送她一张红木椅子
而她的心 一直沉入井底
她不敢在山里号啕大哭
怕加速雷雨云的形成
只是紧紧地 紧紧地
倚靠在岩石上啜泣:
“这是我的苦难石
你们把我的痛苦抢走了
叫我到哪里去休息?”
小河梦
我睡熟了,忽然感到寒冷
周围是浩淼的海水
星光辽远,风却很近
我渴望有棵挡风的树
渴望使幻景长得很快
比电影上的花开更为神速
茶几上小小的圆柏
顿成千丈扶桑
扶桑发荣在旸谷之岸
太阳在旸谷里沐浴
那幽冥的声音又飘过来
“我想去上古的温泉过冬天
窗外的小河太冷了”
窗外的小河有株柳树
自从苔丝特蒙娜唱过“柳之歌”
河水变得可怕的冰人,因此
不能使奥菲莉亚温暖过来了
奥菲莉亚月光般的裙子
永远在河面上漂流
今夜也有月光
月光雪似地落在河谷
不,月光不是落下来的
是从我们心中渗出来的
——十八年前的一夜
我和一个扮演奥菲莉亚的姑娘
曾在这河边徘徊
把月光吸到心中去来
那一夜,我们向往火
可是,血红的彗星划过天空
只发出一阵火灾的呼啸
不几天,她就在河里沉没
老弯了的柳树更显得凄凉
那幽冥的声音又飘过来
“我想到上古的温泉过冬天
窗外的小河太冷了”
我被冷醒
朦胧中摸到滑落的被子
窗外的小河很温暖
在初升的丽日下冒着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