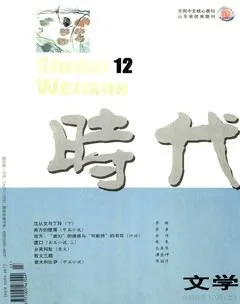《潜伏》让人性绽放
摘要:《潜伏》以全新的角度诠释了信仰和人性,让观众在受到两位地下工作者余则成和翠平革命信仰感召的同时,也感受到人性的光辉,从而使当下的人们重新认识了革命者的形象——有血性、懂爱情、人性化十足的英雄。
关键词:《潜伏》;信仰;人性
时下热播的一部谍战片——《潜伏》,让我们认识了两位个性鲜明的地下工作者——余则成和翠平。他们的形象与以往的影视作品中革命者的形象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源于剧中对革命者本身除了革命以外的情感的细致刻画,这对于以往的影视作品传统表现手法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种创新。也正是这种创新,引领着我们试图从余则成和翠平的成长轨迹中,找寻对信仰和人性的重新定义。从过去的交完党费再死,到现在的金刚式的轰然倒下,一直以来,影视作品在脸谱化革命者的形象。在这种脸谱化中过于强调革命信仰在人物内心的重要位置,却弱化了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革命者所应有的情感形态,比如脆弱、犹豫、挣扎、痛苦等,而这些情感形态虽然负面,却是人性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而革命者形象的伟大,不应在只在于一心革命,而在于处在负面的情感形态中,仍然坚持信仰。人性从来不是单一的,复杂的人性的斗争才是最真实最有价值的。而《潜伏》作为影视作品的成功,也在于细致真实地刻画人物性格,描绘人物形象。换言之,《潜伏》让人性绽放。
余则成:老谋深算,人性十足
在《潜伏》里,余则成是一个文弱甚至有些木讷的知识分子形象,和以往高大全人物形象有极大反差,但同时,这也是一个有血性、懂爱情、人性化十足的英雄,是一个内在力量非常强大的真正的英雄。他会当机立断开枪除掉绊脚石,也会一遍遍读着左蓝的日记深情怀念她;他会在等待消息时紧张地撕烂报纸,也会在从电台里听到国民党“占领”延安的消息后浑身瘫软,慌乱中跑到联络站询问情况……
余则成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愿意投身共产党,最初他只是为了完成老上级(公开身份是余则成的科长)、已牺牲的老地下党员吕宗方的托付去接头地点,但却意外与恋人左蓝见面长谈,此时的余则成只是把此次接头看作是私人托付。这就如同老吕被杀后激起了他只身刺杀汉奸李海丰的勇气一样,心中有的只是私人复仇的血勇与基本的爱国观念,就如汉奸李海丰死前所问:“你是重庆的还是延安的?”余则成的回答是:“我是抗日的。”这时候的余则成是一个有爱国观念但没有坚定信仰、对时局相对漠不关心的人。就如他与左蓝所说:“我没有什么信仰,如果说有信仰的话,我信仰良心。”此时的余则成除了自己的特殊职业外,其实与许多普普通通的国人一样,希望抗战胜利结婚生子,过太平安定的小日子,不愿意卷入政治,只想柴米油盐。当左蓝劝他去延安时,他只关心:“你到底是真心爱我,还是共产党的美人计?”
在后来继续执行军统潜伏日伪期间,在执行了上级利用情报与日伪政权交换为私人谋利的“战斗任务”后,他对自己所服务的军统及自己的工作价值产生了怀疑与动摇。这时他又有了接近共产党的倾向。在受刺被救后,主要还是基于对左蓝的个人情爱而接受了共产党交付的潜伏任务。应该说,这时候的他还不是一个自觉的战士。
当与余则成接头的秋老板被捕后,面对收买与严刑也不出卖同志,并且说出:“谁也不能战胜我的信仰,我可以去死,但我绝不会出卖我的战士!’为了坚定余则成的意志和让敌人绝望,秋老板咬断自己的舌头。余则成内心震动了。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这应该是剧中余则成内心第一次海啸。秋老板精神上的强悍与伟大,把为了个人情爱而工作的余则成推向了要抓住什么的边缘。虽然要抓住什么还不是很清楚,但这为余则成的转变进一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左蓝为了弥补敌人布下陷阱时自己与余则成所漏出的破绽,宁愿冒着危险去化解余则成的危险、意外牺牲时,余则成又一次被震撼了。面对死亡,左蓝是坚定的、微笑的,用自己的生命去坚守对爱人的爱、对同志的爱和对党的忠诚。当余则成去医院时,看见的只有爱人冰凉的尸体,此时的他伤心欲绝,内心激流涌动却只能保持一副平静的表情。刚刚还泪水奔涌,可一走出太平间,面对着李涯,他竟主动拍了拍他的肩膀,很“灿烂”地一笑,而后异常轻松地劝李涯放轻松。他在心里默默地提醒自己:“悲伤尽情地来吧,但要很快过去。”应该说余则成看见的不仅仅是爱人的尸体,而是一具战士的尸体,这让他初步读懂了爱人的精神与信仰。
爱人的牺牲让余则成变得伤心和沉默,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与寂寞。当特务把搜查和调代表办事处撤离后留下的物品交给余则成,他在里面发现了一本《延安文集》,第一篇是《为人民服务》,他默默地翻阅,然后慢慢地轻声阅读,继而节奏越来越快,声音越来越高亢。在读的过程里,他应该想起了老吕、秋老板,想起了左蓝,想起了千千万万为中国独立强大而努力奋斗的民众和同志。他是其中的一员,他并不孤独。
回到家里的余则成反复地阅读、反复地重复着:“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左蓝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志,比泰山还重……”这时候的余则成已经完全与自己的爱人左蓝实现了精神上的相通,左蓝没有死,反而在他的心中复活了。这种精神与信念从此便一直支持着他坚定地战斗下去,直到永远。
当组织最后用明码呼唤余则成安全撤离时,为了更重要的情报他坚持继续战斗,这就已经是一种自觉与坚定了。就如余则成曾经回想起左蓝所说的话:“选择这条路都是为了你。”另外一位同志说:“你已经是一个有信仰的战士了。”这就是对余则成成长为一名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战士的最好诠释和注脚。当他和装扮自己妻子的翠平对话时谈到身边的党通局(原中统)人员为了私利买卖情报为自己留后路时说:“有钱就有人拼命。”翠平的回答是:“我们都不是为挣钱,我们一样也敢拼命。”余则成说:“对,因为我们是有信仰的人。”
余则成虽用智慧赢得了谍战的胜利,其看似圆滑世故的处事方式也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有人说,“余则成也有油滑的一面,只有他才能左右逢源,以老好人的姿态在情报战中获得一席之地 ,领导倚为心腹,同事被他卖了还要帮他数钱,立过功,得过奖,社会各界都吃得开”……相比之下,一心要查出地下党的马奎和险恶用心尽露的李涯倒显得有些“直”。笔者并不认为余则成本人是世故的,因为那是他的一种自我保护,那是他为了自己的信念,对于自己身份的一种保护,是一种无奈下的伪装。
翠平:莽撞隐忍可悲可叹
余则成作为一个国民党军统特务,因为对左蓝的爱,开始对中共产生好感,而左蓝却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离开了余则成;当余则成真正成为一个中共的卧底人员潜伏到敌人内部时,组织上却给他派来了翠平给他做冒牌夫人并共同生活在一起 。在那个年代,不知道有多少像余则成、翠平这样的情况,为了执行任务以夫妻名义住在一起,不过《潜伏》第一次生活化地描写了两位年轻的革命者的生活细节,原来他们不光是每天在一起讨论革命理想、接听密码电报、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他们有那么多不默契、不理解、不合适,他们甚至彼此讨厌,回家就大吵大闹。
该剧的笑点大部分都在翠平身上,然而,翠平反而是全剧中最令人动容的悲剧人物。当翠平开始帮助余则成完成潜伏任务时,当目不识丁的她勇敢机智地与敌人周旋时,当她骄傲地回忆妹妹却不知妹妹牺牲时,当她真正爱上余则成后,却因身份暴露不得不与余则成永远天各一方时,她的隐忍与牺牲和先前的滑稽莽撞形成鲜明对比,这个人物的结局可以说比死亡更悲伤。
大字不识的单纯的女游击队长翠平是受上级领导指派顶替意外身亡的妹妹担负起掩护余则成的责任的。她没有文化,习惯了抽烟袋、大口吃饼的她连睡衣都不知道怎么穿,也不能接受城市里官太太们的生活方式,换上一袭旗袍那一刻居然大喊着别人戏弄她。天真质朴头脑简单的农村妇女登上纷繁复杂的地下斗争的舞台,从开始的鲁莽坏事到中间与余则成的合作无间,最后二人情愫暗生,翠平在保持鲜明个性的同时也进化和成长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相守让他们之间的突兀化成自然,配合也更加默契,到最后居然水到渠成地拜了天地入了洞房。其实如果仔细想想,翠平和余则成也有相似之处。他和她都是好人;虽然他们都不高喊主义,但他们都是坚定的革命者,翠平也许说不出信仰是什么,可是她的言行向余则成传达了她的信仰;他们都为自己认为值得的事业付出了很多很多……
翠平这个女游击队长大大咧咧、心直口快,心中所想常常直接就体现在脸上,莽撞冲动同时又容易轻信他人。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她的存在就是埋藏在余则成身后的“炸弹”,时时给余则成增添新的隐忧。两人之间这种强烈的反差,产生了一种比较明晰的强烈喜剧效果,令人发笑,但是两人又是处于这样一种危险的境地下,因此,这种喜剧效果是心酸而且黯淡的,苦中作乐。这是对以往互帮互助的革命夫妻关系的一种突破,因为它是反着的,不仅不能互帮互助,反倒是添堵添乱。
有两个啼笑皆非的片段让人记忆犹新。当翠平受生活圈的影响穿上旗袍,而后问余则成怎么样时,余则成赞曰:真像林黛玉。谁知翠平听后,嗓门大提:“又是哪个野女人!”还有,余则成与地下工作人员配合进行一次暗杀活动,余则成与翠平心情忐忑地在家等待消息。可是迟迟没听到枪声。余则成就推测是不是用了消声手枪。这时,翠平一脸认真地问:“有没有消声冲锋枪?”余则成也不失时机的以幽默还以颜色:“消声手榴弹你要不要?”
就这样,带着一点荒诞不羁和黑色幽默,《潜伏》颠覆了传统谍战剧的格局,令人嗅到战争残酷的同时,也笑中带泪地感受到了生活的原色和质感。
梳理两人的情感脉络,可以用真情、深情和至情三个阶段来概括。真情者,真情真性,互相真诚以待却又不断因为“真”而制造麻烦;深情者,相濡以沫,不离不弃,可同享富贵也可共赴患难,两人从摩擦到慢慢地适应,最后终于结成夫妻;而到了最后,当误以为翠平已死的余则成看到近在咫尺的翠平却又无法相认,只能假扮公鸡跳舞来暗示她情报时则无疑达到了“至情”阶段,大情大性,却又可离可弃,相顾无语,惟有泪千行。两人这种无语的分离是最大的悲剧力量,也是牺牲主义达到极致的表现。正如导演姜伟所言,牺牲生命是一种牺牲,但是牺牲者并不痛苦,像余则成与翠平这样牺牲了个人家庭、个人利益却是漫长而痛苦煎熬的。在喜剧的外壳下内在却是一种荒诞的心酸,这种明喜实悲的极致更彰显了主人公为了理想而殉道的壮烈。他们的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与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其生活时,整个身心也便为之而浸透,见义忘却生死。
现代影视作品强调表现内心,这来源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上的非理性色彩。它的最大的特征是突出人的感觉、欲望、情绪、本能。因为人是通过自我认知去把握自身和世界的。通过社会动荡的重重危机和矛盾,深刻揭示出被扭曲和异化的人的精神世界。电视美学本性是最大限度地再现客观世界,最大限度地表现主观世界。丰子恺曾经说过:“有生即有情,有情即有艺术。”[2]电视艺术是诉诸于人的情感,以情感人,以情动人。尽管它不可能直接参与对社会的改造,但其在使受众获得审美享受的同时,已于无形中向受众灌输了是非善恶观念,唤起人们的艺术良知,并帮助人们树立起正确的审美理想。
参考文献:
[1]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2)。
[2]丰子恺.《艺术从话》序言.良友出版社.1935。
(作者单位: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