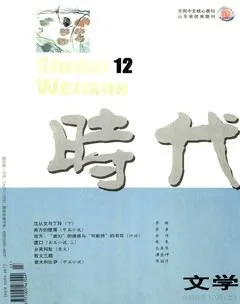木偶叙事——镜像儿童的文化读解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意识形态以其极强的广延性和纵深性掌控人们的生活,作为人民电影事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儿童题材影片从一诞生就高扬社会学主义现实主义的大旗昂扬地走在康庄大道上。镜像儿童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国家意志的“被儿童”,但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儿童的“本质力量”。
红色语境下的政治儿童及其镜像叙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镜像儿童主要是“红孩子”和“好孩子”形象[1],影片展现的就是小主人公从一个(群)普通自在自为的群众成长为有组织守纪律被政党所接纳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叙述主体是“我们”,叙述轨迹方略呈现为从无为到有为的提升。故事也大多是刚刚结束的战争事件,这样的镜像展现既可以唤醒刚刚逝去的记忆,又能搭建起英雄与平民身份相互跨越的平台。《红孩子》、《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等影片中都围绕小主人公展开叙述,这些孩子大多有苦难的出身,带着浓重的阶级胎印。他们对共产党具有超越先天的信赖,懵懂中稍加点拨就会义无反顾甚至会舍弃生命加以追随,一颗红心在小小的躯体内翻涌着家国仇民族恨的巨大能量。
这些红孩子浓眉大眼,贫穷但却整洁,他们机智、勇敢又充满童趣,但这“趣”和“智”主要也是为反衬对手的愚笨的有效存在,他们的善与不善完全源自于阶级,其话语资源除了鬼子、地主老财、党员大叔就是毛主席、延安等国家大事。小小的脑袋里运行的是非好即坏的鲜明的二元对立思维。此期的儿童题材电影主要是借重电影,揭露和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卑劣行径,强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建国宝典,反映着无产阶级革命和战斗的儿童观。
好孩子镜像应新中国成立而生,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下,孩子们放飞着共产主义理想。第一部国产儿童题材影片是《祖国的花朵》。“影片从1952年林蓝接受编剧任务,到1955年严恭摄制完成,总共用了三年时间。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求儿童电影成为培养和教育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重要工具,儿童成为了儿童电影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服务对象和接受主体。但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某些“功利性”,又使儿童电影进入了“教育儿童”的话语时代。[2]
孩子们的话语言说领域由战场过渡到操场,影片以粉红色为基本色调,明快、欢畅、轻松、愉悦。尤其是《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主题歌更使影片充满诗情画意。
为制造波澜,影片设置了98%的先进与2%的后进的对比阵营,完成后进到先进的提升,实现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的主旨,最后全体孩子全家福般地聚拢在少先队队旗下。“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和爱护公共财产”,成为合格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成为他们的话语资源,而那2%的孩子则因淘气(孩子的天性)和不合群(某些孩子的天性)成为被改造改造的对象,直到他们把天性的东西剔除干净,才有资格加入少先队,完成“大合唱”。
红孩子和好孩子被演绎成为听命于政治和政策的木偶,前者印证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后者张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包括儿童在内的人民得到真正幸福的社会主义本质。它迎合了当时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现实,较好地实现了电影的工具性质。
伪装“人——“问题儿童”的别样书写
20世纪80年代,政治解禁、思想解禁,“人”的觉醒以其狂飙突进的态势掀起一个个思想解放的巨浪,“这一时期的教育成长叙事也体现出了鲜明的崇尚理性、注重社会教化的特点。”[3]为学校教育正名是此期儿童题材影片的主要功能。
作为对符号式镜像儿童的反拨,此期的儿童题材影视剧“以儿童为本”意识被凸显出来,武术队、工读学校、弱智残障、传统技艺以及世事艰难等先前的题材“雷池”被一一打破,“儿童视角”不再是一个虚妄的名词。在主题的开掘上也不再仅仅是向政党与政策的中心靠拢。“后进生’、“坏孩子”概念被淡化,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精神导师力图与孩子站在相等的视点上,发现真理,一道去追求真善美。
此期的儿童题材大多数以喜剧形式存在。通过迷途者知返、强硬者归顺、失足者幡然醒悟达到好孩子的标准——好学、上进、诚实、走正道,成全最后的大团圆结局。以往同类影片中尖锐的敌我、阶级对立被置换为持两种不同教育方法的教师的对立。
此期的儿童画题材影片进入一种多重悖论存在,80年代初期的镜像儿童用顽劣——嘲笑缺陷、撒谎、贪玩、吹牛、不爱学习、打架、打小报告等承担对“问题社会”的控诉,暗喻“问题社会”所造成的心理缺陷比生理缺陷更可怕,进而张扬学校教育的必要。而这些又被诠释成“热情”、“活跃”、“有个性”的“人”的有效构成。影片的结局是经过行之有效的教育,孩子们的这些“可爱”的天性被否决,他们被修剪成中规中矩的同类产品。
囿于发现的“发现”——寻找回来的世界?
主题先行,说教味道太重,观众不爱看,艺术性太少,总是强调对儿童的心灵净化、洗涤,这种干瘪的说教是不受欢迎的,内容肤浅,无法打动孩子、、、这是一些儿童剧制作者在连续多年的金鸡奖、百花奖之儿童题材空缺之后的反思。
发现真正的儿童、寻找回儿童的真正世界是90年代儿童题材影视剧的主要追求。用所谓的“孩子气”装点某种大道理为创作大忌。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孩子的善与恶、崇高与卑下、真与假、邪与正,探讨如何从“人”的意义上塑造少年人格成为儿童题材的动力。这种寻找是否是真正的发现之旅,我们要在对影片的分析中得出结论。
1990年,为即将召开的亚运会而拍摄的《我的九月》为我们展开了本真生活中的儿童生活画卷。
拥挤的四合院、狭小的天井、院子里打闹嬉戏的成群的孩子、妈妈卷发的空心卷、双缸洗衣机、即将从台湾归来的爷爷、尊贵与卑微的社会身份、萌芽中的贫与富就在饶有意味的京腔京韵中拉开帷幕。基于发现的视角,影片设置了怯懦卑微、善良宽容、时时处处受人愚弄又从不反击的绰号安大傻子安建军和聪明事故、乖巧伶俐、惹人喜爱、左右逢源的中队干部刘庆来两个少先队员形象。影片围绕着安建军和刘庆来此消彼长的精神力量交锋展开。
作为朱文娟的精神兄弟,刘庆来继续着自私、谎言、讨巧、运作、审时度势,并因此占有优越的社会资源——中队长,并获得社会价值——盗取安建军的“功名”受到肯定——报纸上有名,受到学校的表彰。而安然的精神兄弟却不见了安然的锋芒,继续着闰土的木讷,承受着因卑微而造成(想要的荣誉旁落人家)的内心撕扯。支撑安然的活泼轻松的家庭被置换成同样隐忍无声的底层市民父母,影片中的妈妈低眉顺眼,甚至都不大声说话,每每爸爸要追问缘由的时候总是被妈妈的眼神阻止,于是安建军不断地糊涂下去、不断地怯懦下去、不断地被刘庆来欺负下去。我们看到命运的转机不是安建军灵魂深处“人”的意识的真正觉醒,给他“人”的待遇的依旧是外在力量——道德、正义、良知化身的教育者高老师。它所获得的人生价值实现的标志依然是加入组织——亚运会的团体操表演。
1994年,旅美多年后,导演吴天明归国创作《变脸》。影片塑造了狗娃这一知恩图报的小女孩形象。狗娃命运的跌宕起伏只因自己的女孩,重男轻女的陋习让狗娃们命如草芥,任人宰割。或许我们不应该对一个9岁的小女孩太过苛责,让她向造成她悲苦命运的封建制度宣战,但我们也不应该陶醉于民族的、传统的、国粹的张扬而忽略这个9岁的女孩恰恰成为封建制度的捍卫者和卫道士这样的触目惊心的事实。
安建军能走多远?回到船上的狗娃将飘向何方?小学毕业的魏敏芝(《一个都不能少》)会把一群懵懂少年带去哪里?拉得一手漂亮小提琴的刘小春(《和你在一起》)和他养父回到家乡之后怎么办?王小燕(《上学路上》)还会拼死拼活地挣下个学期的24.8元的学杂费吗?方枪枪(《看上去很美》)一旦获得小红花所给予的“好处”,还会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吗?这是90年代以及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镜像儿童带给我们的担忧。思想漏筐打捞上来的只是残缺的木偶零件,不要抱怨体制的桎梏,不要抱怨市场运营方式的陌生,根本原因在于在当代中国“儿童”还没有成为成人社会的思想资源,在这里,“表现什么”要比“怎样表现”重要得多,镜像儿童并不只属于儿童而是属于全人类,它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表现,它需要极高的艺术性更需要极高的思想性。
参考文献:
[1]凌燕.中国儿童题材影片的非儿童本位取向分析,《当代电影》,2006.6.135。
[2]张震钦.《祖国的花朵》:校园叙事话语的构建及其影响,《当代电影》,2005.6.78。
[3]杜霞.80年代:“花朵”模式的延续,《扬子江评论》,
2007.6.78。
(作者单位:北华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