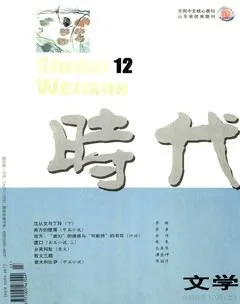性格与命运
摘要:本文揭示了奥瑟罗不可避免的悲剧不仅归咎于本人,还应归咎于剧中其他人物。尽管种族偏见和社会习俗加速了它的发生,但剧中人物的性情影响着其言行,是推动灾难发生与发展从而导致奥瑟罗和苔丝德梦娜脆弱爱情毁灭的关键。
关键词:脆弱的爱情;性情;悲剧;命运
莎士比亚剧作《奥瑟罗》深刻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具有现实的、时代性思考,一直为世人所传颂,让读者品味无穷。
奥瑟罗悲剧的发生折射了人物的一言一行决定于他们的性情,他们的言行酿造了周围的事态,所有这一切恰成了伊阿古恶毒计划实现的温床。尽管种族偏见和社会习俗加速了它的发生,但决定于性情的言行是影响灾难发生与发展从而导致悲剧的关键。本文着重分析人物的性格,并试图从这方面来揭示奥瑟罗悲剧的必然性。
来自非洲的黑人摩尔奥瑟罗,年复一年,经历了战争、围城,以及各种祸福。他遭遇过巨大的危险,有过独特的逃生经历。荒野的故土和尚武的职业养成了他诚实、正直、慷慨的品质和性急、单纯、无戒备之心的本性。他不谙熟白人“文明世界”的人情,他根据自己的品行去评断他人,一旦他相信某人或某事,便会完全绝对地相信。他以为貌似忠厚的旗手伊阿古是极诚实的,并且容易像驴子般地被人牵着鼻子摆布。伊阿古自始至终赢得了奥瑟罗的绝对信任。在奥瑟罗和苔丝德梦娜之间并没有取得真正了解的情形下。当崇高理想面临破裂危机时,他对他妻子的信任很容易动摇,很容易相信伊阿古的捏造。
一开始伊阿古就使用这样的语句:“哈!我不喜欢这样子”(Shakespeare III. iii. 35),并通过暗示、捏造、刺激,显出忠实,提供建议等手段在奥瑟罗心中播下怀疑的种子。起初,奥瑟罗的自信心仍很强。但这很容易动摇。紧接着伊阿古提醒他注意威尼斯妇女的伎俩,并提醒他留意苔丝德梦娜对其父使用过的威尼斯人的欺骗手段。勃拉班修的临别警告-“她欺骗了她的父亲,也许要骗你”(Shakespeare I. iii. 294),在奥瑟罗的心中增加了分量。伊阿古告诫这黑人异族说,待她神志清醒之后,把你和她同种且门当户对的男人相比较,或许要后悔。他也告诫奥瑟罗:留神你的夫人是否强烈地请求为凯西奥复职。奥瑟罗清楚这是事实,极重的疑心油然而生。从这时起,他在思索中迷失了,内心充满激烈的矛盾。他不明事实真相,甚而希望暗中受人欺辱也比略微闻风好过得多,他处在极度的痛苦中,不知所措。奥瑟罗十分明白自己不能长期忍受不明真相和怀疑的折磨。一旦疑心顿起,他便要明证并弄确实。
奥瑟罗要证据,伊阿古难以自全。但奥瑟罗义愤填膺,如此迷惑,竟不能看穿伊阿古孤注一掷编造的梦。进而伊阿古纯属捏造地说他看见凯西奥拿着一块绣着草莓的手绢擦胡子,并十分肯定地对奥瑟罗说是他夫人的。奥瑟罗是多么的绝望!他相信这是真的了。根深蒂固于他心中的忌妒之焰被煽起了。凯西奥英俊、年轻且多才多艺,奥瑟罗自知缺乏凯西奥所具备的这些优点,这无疑助长奥瑟罗的忌妒之心。“啊!杀,杀,杀!”(Shakespeare III. iii. 452)。感情冲动的本性在这里暴露无遗,尽管身经百战的经历赋予奥瑟罗镇定自若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但在某种场合,特别是生活的源泉--爱情破灭之后,热血便沸腾了。
此时,奥瑟罗抱着一线希望向其妻索要手绢,苔丝德梦娜的确拿不出,奥瑟罗对爱情自信心完全动摇了。丰富的想象刺激着他,怒火就快要大举喷射。处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奥瑟罗偷听了伊阿古和凯西奥的对话,这是伊阿古精心策划的阴谋。他笨拙的猜忌完全误会了凯西奥的神态和他听到的断断续续的话语,他甚而视这猜测为耳闻目睹。这些体现了他的武断、轻信和缺乏敏锐力。此刻,他再也忍受不了其妻的不忠,决意扼死她。
奥瑟罗的另一性格因素-极强的荣誉、自尊和自卑感,也促成了悲剧的发生。在战争纷乱的境况下,因为他行为勇敢且最知晓塞普勒斯,他被元老们认为完全可靠,并且是国家必不可少的人物,这个黑人异族靠着个人奋斗而凭军功受到重用。所以,在贵族及上层阶级中这黑人异族树敌颇多,忌妒者也不少。因而,在这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奥瑟罗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荣誉。同时,他是一个黑人,四周都是白种人的世界;并且同年轻、英俊、多才多艺的凯西奥相比,他自惭形秽。这导致了他深藏的自卑感。因此,当奥瑟罗确信了苔丝德梦娜的罪孽时,这些性格因素促使他下定决心扼死她,因为他觉得丧失了名誉,他的自尊受到刺伤。
奥瑟罗的疑与嫉、爱与恨、悲与仇、荣誉与正义、自尊与自卑感全绞织在一起刺激着他的热血。一旦它沸腾起来,“就象黑海里的寒流激湍,永不退潮”(Shakespeare III. iii. 454-6)。他的武断——这与他的军旅生涯密切相联,对其热血的沸腾起着催化作用。(正因为奥瑟罗在威尼斯军中的荣誉和地位,他非常自信,并养成了他武断的性情)。他一旦确信,尽管是错误的决断,也很难再改变。他不相信爱米利娅宣称她敢担保苔丝德梦娜是诚实的。他甚至不允许苔丝德梦娜为自己的无辜辩护以证明自己的贞洁。在这关键时刻,奥瑟罗复又热血萌动,感情用事,扼死了自己的妻子。
苔丝德梦娜因自己的品性也成了该悲剧的诱发者之一。她天性是如此的仁慈好施,她对凯西奥的恳求作出了承诺。我们决不要忽视她是新婚并深爱着奥瑟罗。很自然,她想行使自己的“权威”,并掂量自己在丈夫心目中的分量。因为她单纯、不谙世故,她决不会明白为什么奥瑟罗推阻凯西奥的复职。她下意识的心理和对凯西奥的同情使她超越了限度。她对凯西奥许诺说的字里行间显露出她的幼稚、淘气、自信和骄傲。他说要让奥瑟罗做一件艰难紧要的事以考验他的爱情。可是,苔丝德梦娜却不知道这助长了奥瑟罗疯狂的忌妒之心并引起了他的猜疑(孙家琇 1988)。
苔丝德梦娜忠实的爱使她决不会意识到自己已被猜疑,也决不会明白奥瑟罗为什么会大发雷霆。
而且苔丝德梦娜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没有谁,我自己,永别了。替我致意我的丈夫。啊!永别了!”(Shakespeare V.ii. 122-3)。这是她临终的话语,不再是对罪的否认,而是自我克制并饶恕了奥瑟罗。这种克己与豁免正是由于受了典范的基督教熏陶(Scott 1987)。
剧中邪恶人物伊阿古是该悲剧的关键炮制者。一开始他就以充满深仇大恨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眼前,他恨奥瑟罗,因为奥瑟罗贬黜了他,并提升了一个经验不足的官员置于他之上。黑人异族奥瑟罗事业的成功,令人羡慕的婚姻以及他所拥有的优势促生了伊阿古与日俱增的妒忌。并且,奥瑟罗是一个黑人,种族偏见加深了他的嫉与仇。他说那摩尔人使他戴了绿帽子,这纯粹是为了使罗德利哥深受蒙骗而编造的。同时,伊阿古妒忌凯西奥的副官职位并觉得凯西奥的生活中有一种优美的风度,显得他丑极了。所有这些都激起了伊阿古的妒忌,憎恨、深仇、邪恶和复仇之心(孙家琇 1988)。
为了成功地达到复仇的目的,伊阿古就必须伪装。“我不是像我表面上这样的一个人” (Shakespeare I. i. 65),这是他毫不掩饰的宣称。他的手段使是针对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伪装自己。
对奥瑟罗,他将自己装饰成一个忠心的下属,诚实的朋友。他利用奥瑟罗对他的绝对信任,不断变换策略来煽动奥瑟罗,他通过提出疑问、暗示等顿起疑心;有意吞吞吐吐,并不急于下结论来刺激其忧虑之心;佯装受屈并假意不愿对朋友诚实;狡诘地告诫奥瑟罗警惕绿眼怪物-妒忌;故意替苔丝德梦娜辩护;提醒奥瑟罗注意勃拉班修的警告;大大夸大威尼斯妇女如何背弃以及他们的放纵之事等。当他认为是紧要关头时,便拿出了证据,奥瑟罗轻易地就信服了(孙家琇 1988)8。
对凯西奥,他佯装成一个有同情心的伙伴和安慰者。他巧妙地向凯西奥进言,这恰是他恶毒的计划——充分利用“这老实的傻瓜”,把他们彻底消除。
对罗德利哥,他伪装成一位朋友和兄长。他激励罗德利哥并随意对他行骗。罗德利哥成了伊阿古利用的爪牙。
对苔丝德梦娜,外表上他显出同情和深切的关心。他附和她的猜想——国家大事烦扰着奥瑟罗,并叹息道:“嗳呀,真不幸!(ShakespeareIV. ii. 124)”(孙家琇 1988)。
除了人为因素外,社会因素也促成了奥瑟罗的灭亡。我们已知道等级观念和种族偏见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悲剧的发展。这里还有另一诱导因素。奥瑟罗曾说:“这是象死亡一样,无以躲避的命运:我们刚刚在胎里动的时候,绿头巾的命运就会给我们注定了”(Shakespeare III. iii. 275-7) 。难道这纯属是奥瑟罗对威尼斯妇女放纵行为的臆见吗?不,如果我们看看当时的社会习俗,就知道这决不是奥瑟罗的主观见解。正如伊阿古所说,威尼斯妇女“不敢让丈夫知道的勾当,她们敢当着上天的面去干;他们最高的道德,不是不干,是干了不让人知道”(Shakespeare III. iii. 202-4)。他强调说:“那么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城里,正有不少这样的畜类,还有不少的体面的怪物呢”(Shakespeare IV. i. 63-4)。当苔丝德梦娜问爱米利娅,是否世界上真有无耻地辱没丈夫的女人,她毫不犹豫的回答说这样的女人有的是。苔丝德梦娜又问爱米利娅即使有世界大的利益,是否愿干这样的事?爱米利娅相信她肯干。对这样的耻辱,奥瑟罗自己辩解说:“这正是贵人们的苦楚,这苦楚是贵人们比贱民更难逃免的”(Shakespeare III. iii. 273-4) 。这是一个真实的概况,在社会的低阶层里确实存在着毫无约束的婚嫁,而对上层社会来说,背弃爱情且有通奸行为并不是新鲜事。我们决不可忽视这种社会习气对苔丝德梦娜的遭遇产生了一定作用(孙家琇 1988)。
以上的分析展示了人与社会因素共同促成了奥瑟罗和苔丝德梦娜连同其脆弱爱情的毁灭。这个悲剧不是由于偶然的差错,也不仅仅是外来干预的结果。剧中人物各自按照自己的天性行事,导致了把男女主人公引向毁灭的各种情势的巧合。这里虽有外界环境的影响,但我们决不可忽视,也正是男女主人公的这些性格特征,不管它是肯定的或是否定的,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跟环境发生冲突,从而导致了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奥瑟罗和苔丝德梦娜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自己的本性决定的。这部剧作反映了真实的生活规律。
注释:
① 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