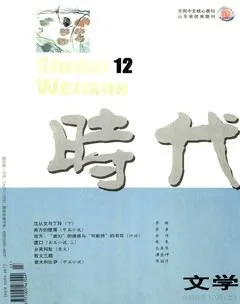听之如仙乐 观之若云霓
摘要: 隐喻是诗歌的灵魂。本文从诗性隐喻的认知视角切入,解读《致海伦》一诗如何通过感官义域的跨域转换,从音、形、典、意四个方面建构概念隐喻、交织成文,描摹出涤荡心扉的海伦之美。同时映射出诗人一生追求“唯美主义”的精神。
关键词:《致海伦》;诗性隐喻;感官义域;唯美
一、引言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方式,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是人们谈论和思维抽象概念的认知工具。“隐喻无所不在,它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中、思想中。其实,我们人类的概念体系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1]。我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普通概念体系本质上是隐喻性的,又被称作“隐喻概念体系”。以一个概念去理解、建构另一个概念,于是也以一个概念的词语去谈论、表述另一个概念,这就是概念隐喻。与普通概念隐喻相比,诗性隐喻是非常规性,“通过喻源结构投射至感官和肌动性质不一样的目标义域来创设两点之间的相似点”[2],人们刻意创造的相似性把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事物互相联系起来,从而使本质上有区别的事物形成非真值、非逻辑的联系。诗性隐喻常通过意象的使用,将思想转换为视觉语言,使不合逻辑的东西不自觉地出现于逻辑的思维中,促使诗歌实现焕发欢愉,令人享乐、满足的目标。巴菲尔德在《诗性词语》中说:经由个体思维和构建的隐喻,即诗性隐喻[3]。
胡壮麟先生也曾撰文详细讨论了诗性隐喻的典型性特征,即:原创性、在不可能性掩饰下的真实性、义域的不一致性、跨域性、美学性、趣味性与互动性,符号的完整性和扩展性。究其实,诗性隐喻的本质是用不同义域的词将两种本不相似的客观事实联系起来,彰显二者的相似性,其隐喻过程具有极强的原创性、新颖性、美学性等。隐喻是诗的基础,也是诗性语言的根柢,“没有隐喻的诗是很难想象的”。[4]
Edgar Allan Poe(1809-1849)十九世纪美国诗人,著名评论家和短篇小说家。父母早亡,童年生活孤独凄苦,由一个富裕商人抚养长大。爱伦·坡一生悲苦、命运多桀。虽然大部分小说内容灰暗、颓废,基调消极、低沉,充满了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和神秘色彩,但在诗歌创作却把现实和神话完美地揉和在一起,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显示出强烈的唯美倾向。坡的诗作善于使用“隐喻创建具有本义的和真实所指的隐喻世界”[5],诗性隐喻“让他的创造性奔腾流畅,让他的作品具有个人的印记和独特风格,栩栩如生…..表达的意义深奥莫测。”[6]。其脍炙人口的爱情诗篇《致海伦》,短小精悍,诗行整齐,诗中大量使用典故,尽显诗性想象,“诗性隐喻以一种可眼见、可触摸、可听到、可品味、可嗅到的方式”[7],带给读者感官上的享受和情感上的共鸣,创设出一种“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静谧、和谐的唯美境界。通过感官感觉的相通交融,从声、形、典、意四个方面描摹出涤荡心扉的“海伦之美”。
二、以声喻美
《致海伦》一诗中,诗人并没有使用常规的视觉义域的各种词汇:面容五官、身材体型直白地描写海伦容貌之美,而是泼墨重彩渲染听觉义域,“如花,其入目之形色,可以以音响以揣称之。”(钱钟书《管锥篇》第二卷)。通过感悟诗词的音响效果,体味其音乐性,领略“海伦之美”的底蕴内涵和风姿绰约。
诗歌就是音乐,诗的音乐性体现于诗的节奏和音韵,如明人陆时雍《诗境总论》所说,诗“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8] 爱伦·坡看重诗歌的音韵,他认为诗歌就是“有韵律的美的创造”, “音乐是诗歌灵魂的完美表现”, 也只有“在音乐中,诗的感情才被激动,从而使灵魂的斗争最逼近那个巨大的目标—神圣美的创造。”[9]
《致海伦》全诗以抑扬格四音步写成,节奏沉稳。在韵律上三个诗节并不完全相同:第一诗节的韵律是a b a b a ;压尾韵的单词为“me”,“yore”,“sea”,“bore”,“shore”,所压韵为【i:】【o:】 。第二诗节韵律为c d c d c ,尾韵单词为“roam”,“face”,“home”,“Greece”,“Rome”,所押韵为/【m】【s】。 第三诗节则为e f f e f,尾韵单词“window-niche”,“stand”,“hand”,“which”, “land”,压的韵为【d】【tf】。全诗共120个音节,其中长元音与双元音音节多达54个,第一诗节韵脚全部为长元音。长、双元音的交替使用拉长了诗行的发音,延缓了诗歌的节奏。圆润的元音,舒缓不乏强劲力度。充满生机活力的宏亮之音,让整首诗“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10]。金石铿锵,乐韵流淌。海伦之美似缥缈古远的乐曲,亦真亦假、如梦似幻。
第四诗行,诗人连用四个低沉的辅音【w】,与长、双元音相应和,实现了和声的完美,吟诵如歌,并且渲染出游子羁旅行役之苦,由声音逼出一种惶惑迷离之感,由此读者可以深刻地体味出孟浩然“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早寒有怀》)中那种怀乡思归的感伤与苍凉。沧桑的心,在见到归乡之船的刹那,被幸福、希望包裹、融化。感觉在悲、喜两极间跳跃,海伦之美恰似这跳动的音符。
与元音相比辅音灰暗沉闷,有噪音的效果。但是许慎《说文解字》中说“韵,和也”。第二、三诗节,叠用的鼻辅音和响辅音韵脚,不仅构建流畅、和谐的声响环境,同时使诗行上下连贯,一气呵成。整首诗意象生动,节奏鲜明,音韵和谐,既具有诗的文采和意境,又富于音乐的韵律气息,诵之如一首诗,吟之若一支曲,海伦之美就是这流动的乐章。
三、以形喻美
诗人把可及性较强的具体概念:芳香的大海、尼斯船、玛瑙灯、圣地映射到可及性较弱的抽象概念:海伦之美,由触觉、嗅觉通于视觉实现了由源域到靶域的映射,通过幻想、加工创造出一个朦胧含蓄、意蕴深远的美女海伦。
“芳香的大海”,联系多个心理空间内容,通过低级感觉和高级感觉的交相互动,产生层创结构:一指地中海,二暗示茫茫人海,三指海伦情结所系地。辽阔无垠的大海,时而温和恬淡,芬芳四溢;时而波澜壮阔,危机重重;大海的多个概念意义映射出海伦之美淡雅、壮观;海伦之美神秘莫测。
“尼斯古船”却非寻常之物,除视觉上产生一种古朴之美,更能给常年颠簸在广袤大海的游子带来生机,使他们绝处逢生。海伦之美恰似这古船,通过视觉向意义的转换,将源域—尼斯船自身所蕴涵的文化经验图式结构,投到抽象的目标域—海伦之美。看见海伦的美貌,仿佛拥有了漂泊绝望的游子即将归家的欢快心情,带给人一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此美摄人心魄、涤荡心扉;此美犹如黑暗中圣洁之光,让迷航之人找到方向。
“玛瑙”是吉祥和不朽的象征,而玛瑙灯能赋予永恒的魔力。此灯具有禅意,“灯”乃烛照人心,既指黑暗中指明方向的有形之灯,又指点亮人生的心灵之灯。“圣地”指基督教和犹太教者朝圣场所—古希腊、罗马灿烂文明、艺术和美的发祥地。此处诗人似以有形喻无形,实则以有形之无形喻海伦之美。
四、以典喻美
“语言包容着自然、神和人自身,也就是说语言、自然、神、人四位一体。”[11]。爱伦.坡使用诗性隐喻,把人与自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描绘出一个丰富、本色的存现状态。海伦之美,自神女英雄至大海古船,无所不感。其中隐喻典故交织纵横。
“海伦”是斯巴达王后,貌美绝伦。特洛伊王子迷恋海伦的倾国之貌,将其拐走,引发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海伦是西方世界永恒的审美标准,是世人公认的美的化身。“漂泊者”暗指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特洛伊大战之后,奥德赛在茫茫大海上漂泊十年,历尽重重劫难,重返故乡。“水仙女”(Naiad)是希腊神话中专司江河湖泊淡水的女神,一袭紫色秀发,俊秀飘逸。“普塞克”又称“赛琪”(Psyche)——希腊神话中司管人类灵魂的女神,美艳绝伦,爱神丘比特(Jupiter)钟情的对象。
运用神奇的典故,以美为靶域,经过多轮复合式映射,源域在希腊女神和勇士之间交织、迭加,扩大了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张力。由视觉通于精神意义,“海伦之美”是天仙神人美特质的集合体,是容貌美和灵魂美的完美结合。不仅投射出坡简·斯坦纳德夫人—坡“灵魂中第一位纯洁无暇,完美的爱”--理想女性的灵魂之美,也解读了诗人强烈、超前的“唯美主义意识”——对理想之美的向往和艺术之美的追求。
五、以意喻美
以有形之物和有形之无形为始发域构建概念隐喻实现了义域的跨域性,彰显义域符号的完整性、扩张性。而在第二诗节中,诗人则把思想转换为视觉语言,实现了非真值、非逻辑的联系。诗中“Thy hyacinth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