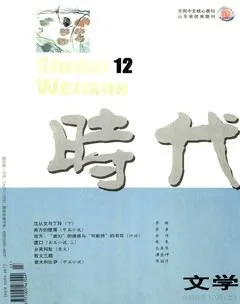心灵之窗与灯塔意象:《到灯塔去》解读
摘要:维吉尼亚·伍尔夫以其高超的意识流叙事技巧,深入挖掘了现代人精神层面的经验和感受,渗透了女权主义思想。长篇小说《到灯塔去》以“灯塔”为意象,揭示了拉姆齐夫人的女权失却之下的现实困惑及其精神追求,写意出爱与奉献的价值。
关键词:灯塔意象;精神感受;女权主义
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批评史,关于维吉尼亚·伍尔夫,有人视她为专事高雅的唯美主义作家,有人说她是本能反映社会现实的高超艺术家。而更多的批评家认为:沃尔夫对生活与现实有独特的认识和理解,她蔑视宗教传统和社会习俗,深感现代社会的混乱、无序和支离破碎;她极其敏感地关注现代人的处境,试图通过小说探索其内在精神上的深层经验和感受。同时,她又是一个有着自觉意识并积极倡导女权的一个典型的女权主义者。
伍尔夫成长于父亲为她提供的学者文人的学术和文艺环境。但她一生精神抑郁,深感孤寂。她自幼多病,生性敏感脆弱,常做病态的精神白日梦。故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沃尔夫的小说诗学渴求的是内在的意识和意象真实。她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醒地意识到了人类永不枯竭的丰富情感。……这里,我们将所有精力聚集在一起然后爆发;这里,我们不断拓展并且从四面八方汇集审慎的印象、累积的信息。”其目的按照普鲁斯特的说法便是:“作家只有摆脱智力,才能在我们获得种种印象中将事物真正抓住,也就是说,真正达到事物本身,取得艺术的惟一内容。”此中强调:外在的客观真实是浅表的,而超验真实或主观真实才是唯一的真实。这种“内在意象”的真实是由人类感性的无限丰富所决定的。因此,作家创作的视野不必驻足于客观世界中所发生的外部事件,而要敏锐地捕捉这些事件在人物内心深处的瞬间印象或真切感受,并竭尽全力以内在的、相对的、多元的艺术形式将其呈现出来,以期突出叙事文学的审美功能。她同时也主张非个人化的小说叙述视角:“在想象力丰富的文学中,角色为自己说话,作者并不出场,我们总是可以感觉到需要这种声音。”这显然是为了更加符合客观事实,更加尊重人物性格本身发展的逻辑,以便营造出一种多维视野的复调叙述的艺术氛围;通过作品人物内宇宙中心潮跌宕的剧烈体验,生动地表现出世间普遍的真理、永恒的规律和人生的真谛。“意识流是他们的新式武器,他们用它来向小说中的作者硬闯入故事的叙述方式开火。他们如实地记录下人物内心中的充满矛盾而且彼此毫不相关的思想,并力图避免像爱德华时代的小说家们那样一定要在作品中渗入自己的声音。”对此,伍尔夫指出:“对现代小说作任何考察,哪怕是作最随便最粗疏的考察,也难免产生想当然的看法,以为这门艺术在现代的实践中总会比从前迈进了一步。”其实,“倘从一个足以高瞻全局的山顶来看,却有点来回绕圈子的趋势。不消说,我们并不自以为占据了(即便是片刻占据了)那样优越的制高点”。因为在伍尔夫眼中,“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左右对称的马车车灯,生活是一圈光晕,一个始终包围着我们意识的半透明层。传达这变化万端的,这尚欠认识尚欠探讨的根本精神,不管它的表现会多么脱离常规、错综复杂,而且如实传达,尽可能不羼入它本身之外的、非其固有的东西,难道不正是小说家的任务吗?”惟其如此,“小说艺术有了生命”。伍尔夫对现代小说艺术品格的观点,强调的是现代小说的叙事重心从 “物质主义”转向“精神主义”,从外部世界的反映转向意识结构的表现。
在这种小说理论的催生下,伍尔夫创作了一系列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1927)是其典型代表之一。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作品围绕拉姆齐先生一家及其友人相隔10年的两次聚会及去灯塔远游,描写了一群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理。如果说小说有一个故事情节的话,便是“到灯塔去”。小说分为三章:窗口、岁月流逝、灯塔。故事情节仅仅是一个框架:“一战”前某天,拉姆齐一家及几位宾客在海滨别墅度假,本打算去海中的灯塔上游玩,谁知天气不佳,只能放弃了原先的计划。不料这一等就是十年。十年后他们终于登上了盼望已久的灯塔,完成了多年的夙愿,但此时已是物是人非:拉姆齐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