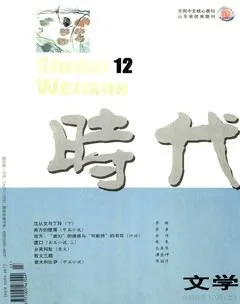积极互文性视角中的文学作品分析
摘要:互文性是文学艺术的重要属性。本文从积极互文性角度将巴塞尔姆的小说《白雪公主》与同名格林童话故事进行互文性分析。积极互文性融入文本之后,使其发生了“创造性的叛逆”并赋予创造性意义,融入了明显的时代内涵。在社会现实、文化和生命意识等层面的探索包含深刻的意蕴。互文性策略的使用让童话与现实融为一体,让读者体味颠覆传统审美、情感纠结的心灵盛宴。
关键词:积极互文性;巴塞尔姆;《白雪公主》;后现代主义
作为一个重要的后现代、后结构批评的标识性术语,互文性不仅指同一个文本中前后的呼应关系,也指文本和社会的印证关系。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女性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isteva)指出,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都不是独立的创作,而是对过去文本的改写、复制、模仿、转换或拼接,构成文本的每个语言符号都与文本以外的其他符号相关联,因此所有文学都是“互为文本的”(赵杰,2009),换言之,任何一个文本都不能脱离其他文本而单独存在,任何一个文本的意义都须要依赖其它文本的意义阐释。
之所以文本间呈现互文性关系,主要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指涉、相互映射的部分。但是,互文性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往往不是单纯地追求与原始文本的“求同”,而是“存异”。有可能新文本的标题、人物及某些故事线索嫁接自原始文本,但新文本则拥有自己独特的灵魂,产生了崭新的意义。互文性的价值正在于文本之间的异质性和对话性。如果原文本的一部分进入当前文本后,与原来相比没有产生异质性,在新文本中没有生成新的意义、形成对话关系,那么,这样的互文性就没有多大的研究价值。
鉴于以上理论与观点,互文性可分为积极互文性和消极互文性两种类型。这两个类型根据辞学家将修辞分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启示而提出的(陈望道,2001)。积极互文性是指当互文性要素进入当前文本后,发生了“创造性的叛逆”(creative treason),与原文本相比产生了新的意义,与当前文本形成了某种对话关系。文本相比产生了新的意义,与当前文本形成了某种对话关系。而消极修辞“必须处处同事理符合,说事实必须合乎事情的实际,说理论又须合乎理论的联系”( 李玉萍,2006)。相应地,消极互文性则是互文性要素进入新文本后,与原始文本相比意义没有突破性变化。
所有文学艺术中的互文性几乎全是积极互文性。巴塞尔姆的小说《白雪公主》具有LKISU91G14fsMeCbXa0VYRUAPqJxXHlU0ylIgeHdknM=文学艺术的独特性,而正是这种独特性决定了它的积极互文性特色,使它散发耀眼的文学艺术生命之光。唐纳德·巴塞尔姆是美国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家之一。他是一位文体冷峻,具有形而上学的反讽和沉思式的超然,对政治敏感,对后现代艺术和文学批评做出重大贡献的作家,被认为是“后现代作家的新一代之父”(王娜娜,2008)。在他的众多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白雪公主》是比较典型的。小说《白雪公主》故事另类新奇,颠覆原童话秉承的情节曲折而结局圆满的基调,整个文本彰显作者极强的个性(李玉萍,2004)。
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个童话梦,只因为每一篇童话都会以这样的话语结尾:“从此以后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即使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梦想或精神寄托仍寄居在个人的心灵深处。但打破人们心中仅剩的最后一道纯净之门的就是巴塞尔姆。掩书沉思,记忆中两位“白雪公主”轮流在眼前晃过,两个不同的故事情节、人物设定和结局让人情感纠结,对于心思缜密而敏感的人来说,巴塞尔姆的这种让人跳脱完美童话直视现实生活的风格可能会是一种不能承受的“叛逆”。但这种效果恰恰是积极互文性最好的体现。巴塞尔姆的小说从童话故事中汲取了不少因素,但是他的小说中也有对这种体裁的背离。普通的童话故事结构简单,情节单一。巴塞尔姆却将现代生活内容融人到长篇小说中,小说内容更关注历史和政治的社会现实效应,以及它们在艺术表现上的新探索和新话语,之所以童话形式讲述的往往不是强调童话内容,而是让人体会悲伤和害怕的现实故事。
小说《白雪公主》虽然仍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但已完全颠覆了人们对童话故事中人物的情感。这个白雪让人心寒,甚至厌恶,她不再是温柔、善良、单纯的公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腹牢骚、精神空虚、茫然甚至私生活不堪的家庭主妇形象。七个小矮人更是无赖的代名词,他们种种陋习、怪癖和恶行凸显了现代人浑浑噩噩、庸俗、猥琐的生活观。而王子呢,没有了英俊、勇敢及为追求真爱而不顾一切的美好品质,只留给读者了一个卑琐的无业游民又自视流有高贵血统的小人物形象。童话故事中的白雪公主和王子可谓一见钟情,是善良与勇敢的美好结合,而小说中的白雪盲目地以为童话故事中的圆满大结局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熟不知那二百年后的“王子”已不再是英雄,他甚至愚蠢到让自己死于一场可悲的“阴差阳错”。曾经,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直到老去;如今,王子死了,白雪公主过着寡妇一样的生活。格林童话故事中的白雪公主虽然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但至今这种至真至爱、战胜邪恶的永恒主题仍对后人产生重大影响,而它的延伸小说《白雪公主》更是不忌“世俗”,像一把利剑插在不堪现实而自我毁灭的人们的坟墓上。
互文性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原始文本与新文本间的隔空喊话或低吟倾诉是相互融入、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一问一答的境界中成全彼此。也正因此,文学艺术的这种对话性决定了其互文性是积极互文性(李玉萍,2006)。原始文本给予新本文生命,而新文本回报原始文本以崭新的生命姿态。由于互文性使小说蒙上的怪诞色彩让阅读小说的过程亦像是巴塞尔姆和读者间的游戏过程,让读者忍不住猜想互文使用的目的何在,这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逐渐领会小说所传递的深层含义。虽然嫁接自过去的经典童话,但如今的小说《白雪公主》能真实且深刻地揭露社会现实,向读者展示了二战后美国社会金钱至上、道德沦丧,人们精神生活极度匮乏、人际关系冷漠的荒诞时代。小说中的互文特性实现了历史与现实完美统一,即赋予了童话模式的永恒性又通过现代人与历史、命运的关系,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空虚。互文性的使用不仅使小说本身颇具神秘感,同时让小说内容更加多元化,层次更加丰富,行文更加自由、开放。互文实现了跨越时空的交流,体现了作者无限的创造力。
参考文献:
[1]赵杰.戏仿和引用——对A.S.拜厄特的互文性解读,《长沙大学学报》2009年第l期。
[2]李玉平.互文性新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3]李玉平.巴塞尔姆小说《白雪公主》互文性解读.外国文学研究 2004年第6期。
[4]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5]王娜娜.文巴塞尔姆《白雪公主》中的后现代主义写作技法研究.学术位论2008。
(作者单位:1.沈阳大学外国语学院;2.中国刑警学院基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