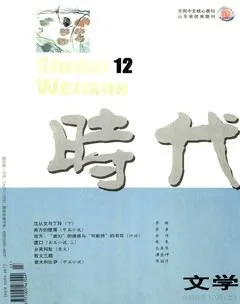大众文化时代下的中国文学
摘要:大众文化具有娱乐性、消费性、商业性、流行性等特性,人们对大众文化价值意义评价不同,当下中国文学活动全面市场化、文学期刊策划频繁、长篇小说独领风骚、审美理想世俗化四个方面体现了后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大众文化属性。
关键词:大众文化;文学;市场化;消费性;娱乐性
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文化,一般分为三类:即精英文化、主旋律文化和大众文化[1]。精英文化是由知识分子主导的有关精神、理想、价值标准、终极关怀等超越性的宏大话语。主旋律文化是由政府或统治集团倡导的旨在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文化。大众文化是指一种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民文化,是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集中满足人们的娱乐需要的文化形态。市民社会和电子信息技术是大众文化形成的两大基本条件。著名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家杰姆逊详细分析了大众文化的特点,认为大众文化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深度模式削平导向平面感。二是历史意识消失产生断裂感。三是主体性的消失意味着“零散化”。四是批量复制导致距离感消失,艺术缺乏个性和光环。[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众文化才在欧美流行。我国大众文化的兴起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也许是后发优势的原因,大众文化在我国发展十分迅猛,几乎是一夜之间便铺天盖地,流行歌曲、交谊舞、娱乐电影、电视剧、流行杂志、言情武侠小说、通俗文学、报纸的副刊周末版、卡拉OK、MTV、时装表演、选美活动、体育赛事、博彩、现代广告、产品包装、居室装潢、加之稍晚的上网聊天、网络游戏、手机短信等等,五花八门,五颜六色,将人们的生活填得满满的。大众文化似乎不费吹灰之力一下便击败其它文化,夺得文化主导话语权,成为一种强势文化。
最早提出“大众文化”概念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现在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电影、收音机和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出现了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之间虚假的一致性。这是因为文化工业的技术,只不过用于标准化和系列生产,而放弃了作品的逻辑与社会体系的区别 。”[3]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是深恶痛绝的。仔细分析对大众文化的批评发现,这些批评大多是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笔者认为应该辩证地看问题,既然大众文化是人类历史的某个时期必然会出现的文化现象,那么其肯定有存在的合理性,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且大众文化一经产生便显示出其旺盛的生机活力与强大的社会效能,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的传统格局,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国民的人格塑造。具体来说其积极的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一场空前的文化革命,在文化史上普通大众第一次成为社会精神文化价值建构的主导者,彻底打破了以往文化话语权由少数统治集团和精英阶层的成员垄断的局面。这一意义是巨大的,大众的凸现使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成为可能。二、大众文化因其普及性、广泛性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文化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和焦点,这是以往任何形式的文化都无法做到的。三、大众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普通民众的精神生活,使他们在现代快节奏的工作之余获得轻松愉快的精神享受,身心得到放松。四、大众文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共空间,能对大众提供精神抚慰,能有效缓解现代社会特有的各种各样的焦虑。五、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大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辅相成,大众文化的繁荣能极大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同时,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首先大众文化会导致人格的片面化。大众文化都是一些消解深度、拒绝意义的快餐式精神产品,这些产品长时间充斥心灵无疑会消解大众追问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意识,大家为了活着而活着,没有人思考理想、信仰、终极关怀等问题,人们变成平庸的存在。其次大众文化会强化人的私欲。大众文化不仅其自身以利润为目的,而且其内容也充斥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意识,人们浸淫在这种文化中会错误地认为追名逐利是人生唯一的目的,变成欲望的奴隶。第三、大众文化消解了人们的超越意识,使大众丧失批判现实的能力与欲望。大众文化的无风格使大众也变得没有个性,个性的泯灭意味着自由意识的丧失,而一旦没有自由意识,批判精神、否定精神也将不复存在。第四、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其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大众文化产品不得不粗制滥造,不讲审美情趣,风格雷同,格调低下,这样势必影响大众的审美趣味,使大众丧失审美能力或停留在低水平的审美层次上。
大众文化的兴起给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也不为过,它象飓风一样席卷了社会的角角落落。文学首当其冲受其冲击。众所周知,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般称为新时期),那时文学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心,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改革文学,人们争相阅读,纷纷议论。那时作家的地位也很高,是称为社会思潮的引导者。但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时代以后,大众文化的怪兽降临之后,传统的纯文学渐渐被冷落,很快由中心沦落至边缘。作家也变成了独语者,且现实的生存也出现了危机。一个文学的神话轰然破裂。“解构纯文学神话的首先不是理论,而是大众文化或者说媒体文化,……纯文学正是在大众文化的强大的攻势中陷入了困境。”[4] 面对大众文化强大的攻势,文学界及时作出了回应,进行了叙事策略的调整。 “进入20世纪后,西方现代文学面对大众文化的崛起有两种选择:或者走在大众文化的前面做引导者,真正起‘先锋’的作用;或者与大众文化决裂,坚持文学为社会精英服务的原则,创造新的形式以对抗大众文化的挑战。”[5] 即是说文学面对大众文化的挤压,或归顺或反抗,别无他途,20世纪西方文学选择了后者,产生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相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一般称为后新时期)中国文学选择了归顺,主动适应大众文化,文学被大众文化招安,成为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后新时期中国文学被大众文化招安,这并不是笔者的理论推导,这是文学现实。下面就来分析一下后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大众文化特点。
一、文学活动全面市场化。纵览后新时期的文学,犹如在迷宫中穿行,景观扑朔迷离。首先是性泛滥,挖空心思的性暗示、赤裸裸的性展示充斥各种文本;其次是作家触电,刘恒、刘震云、苏童、严歌苓等人的大量的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剧;再就是时尚写作、另类写作、用身体写作等各种写作;还有少儿写长篇、中学生著作等身;出版单位爆炒作家;人民大会堂搞首发式;作家行游各大中城市签名售书;文坛官司应接不暇,网络小说今天上传、明天出书、后天下架更成为普通现象……所有这些文学现象虽然离奇古怪,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有同一目的,那就是制造轰动效应,寻求卖点,这些充分表明文学全面市场化,文学已变成一种暖昧的消费品。作家也不是塑造灵魂的工程师,而是写手。文学写作不是一种追求美的精神创造活动,而是一门技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
二、文学期刊、出版社策划频繁,好戏连台。90年代的文学策划以期刊杂志为核心,集结了相当数量的作家和批评家,推出了一大批的文学口号和文学命名。《钟山》在1994年4月与理论刊物《文艺争鸣》合作,挂出了“新状态文学”招牌。同年《北京文学》在第一期祭起“新体验小说”的大旗,1997年又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以及20家大型文学期刊联合举办“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活动,1998年第十期刊登朱文、韩东的“断裂”宣言,著名的关于“断裂”的文学论争由此开始。上海文学也在1994年推出文化关怀小说,后又与《佛山文学》联手举办新市民小说联展,1996年又掀起“现实主义冲击波”。《青年文学》从1994年至1997年举办了“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1998年又列出“文学方阵”。1995年3月《作家》、《钟山》、《大家》、《山花》共同开设“联网四重奏”栏目,在同一个月份发表同一个作家的作品。1999年《时代文学》、《作家》、《青年文学》联袂推出后“先锋小说联展”。从1997年起,《小说选刊》编辑部与漓江出版社每年联合出版一套《中国年度最佳小说》,后又增加散文卷和诗歌卷。《大家》一创刊就与红河企业联手推出10万元的“大家红河文学奖”。
21世纪来以来,由于网络媒体的推动,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的市场包装或者炒作行为更是层出不穷,“80后作家”、“美女作家”、“少年天才作家”……各种命名更是漫天飞。文学策划是一种直接而明显的商业行为,它通过炒作制造轰动效应,达到抢占市场份额增加销售的目的,由知名青年作家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文学市场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后新时期文学风景里一道独特醒目的景观。
三、长篇小说独领风骚。新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式样是中短篇小说,而后新时期则是长篇小说,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并且逐年递增。2009年,中国图书市场出版的长篇小说已经超过了3000部[6]。与中短篇小说相比,长篇小说故事情节更能曲折奇怪,更具可读性,因此更具娱乐性,更具消费性,也就更具大众文化性。另外为扩大销量,在影视成为娱乐艺术绝对主流的今天,文学必然要借重视影视,显然长篇小说更利于改编成影视剧本,更容易投靠影视,事实上很多作家就是因为其长篇小说被拍成影视剧一炮打红而名声鹊起,这也间接反映长篇小说更具大众文化性。
四、审美理想趋于世俗。按照传统的分法,将文学作品分为内容与形式两部分,那么后新时期文学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呈现大众化、世俗化的特征。先看思想内容,后新时期文学的追求事故性、传奇性、趣味性、戏剧性和游戏性,缺秒对人生、对人类的生存现状、人类的未来巨大的痛苦与焦虚的反思与追问,没有终极关怀的沉重,只有游戏笔墨的轻松。形式探索的热情也消失殆尽,语言实验、文本实验鲜有人尝试,叙述圈套无人设置,叙事迷宫无人建造,娱乐性的后新时期文学完全没有现代主义那种复杂的技巧、丰富的想象、敲击灵魂的语言,而是一种简洁的线形叙事、通俗易懂的口语、明白晓畅的文风大行其道。
对于后新时期文学的种种巨大变化,评论界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走向读者才是文学的正途;也有人认为迎合读者是文学的堕落。不管作家和批评家的主观愿意如何,大众文化还是以其强大的话语优势对文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从此,文学不再是高不可攀的神圣事业,作家也不能在高高上下俯视众生,作家、批评家、读者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作家也被迫向市场和读者投降,这对于打破当前中国的文学体制,使更多的人获得文学消费的权利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参考文献:
[1]隋岩.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的划分和嬗变[J].《北京大学学报》.2002(4)
[2] 弗·杰姆逊著、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3] 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著,渠敬东、曹卫东 译.《启蒙辩证法》中译本[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 蒋原伦.大众文化与纯文学神话的破灭[J].文艺研究.2001(5)
[5]邓红风.大众文化的兴起与20世纪的西方文学[J].文史哲.1998(3)
[6]白烨.2009年度长篇小说概评[N ].光明日报.2010.1.18
(作者单位:西京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