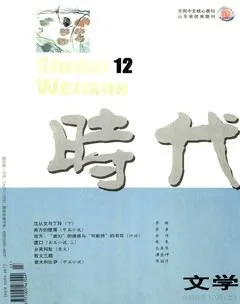镜像中的女性转变
摘要:以新时期女性小说作品为例,从历史、理论、现实等角度,简析女性话语权,特别是女性话语在文学作品中的表达。以此阐述了女性话语权在今天的解放阶段、重要性以及不足,肯定其发展的成果,寻求进一步自我觉醒的可能性,并对自我解放过程中所存在的现实误导,提出警醒和建议。
关键词:女性主义;话语权;社会角色;爱情信仰;主流陷阱
在对世纪之交青春文化现象评价中,何希凡先生曾提到“正视一个模糊身份的真实存在”①的观点。某种意义上,这种“正视”,同样适用于当今社会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虽然“女性”这个形象在女权主义时代之后,才被真正意义上确定,而至今仍无休止的文学探讨,似乎表明了其被主流承认而不被正视的地位。或说“女性”在文学领域中,仍是作为一个调剂的“玩偶”形象而存在着。
伊莱恩·萧瓦尔特②把女性文学视作一种“亚文化群”,并将女性作家的创作分为:女人气、女权主义和女性三个阶段③。从以上“女性主义创作”分段看,自1840至今漫长得足以改朝换代的时间里,女性的地位仅是从“无”发展到“模糊”,不禁令人喟叹。鲁迅对旧中国愚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语亦可用于此。为何?所谓悲剧,一方面不可或缺外界环境所带来的压迫和误导,而另一方面也不乏自身的默认和屈从。在波伏娃的《第二性》中对此就有着细腻、生动且精准的描写。
女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男孩被要求独立,而自己则拥有特权:“她的表情和撒娇让大人们感到快活——身体的接触和令人愉快的目光在保护着她,使她免受孤独之苦。”但在随后的成长中,却意识到所谓特权其实是一种轻视,一种弱势性别的定位,而男孩面对的苛求则是被寄予的厚望。社会不需女性能力的展现,而只要她讨人欢喜的努力。地位失衡,“不适,以急躁、发脾气和流泪的方式表现出来。她们之所以喜欢大哭,主要是因为她们喜欢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这不仅是对她们严酷命运的抗争,也是惹人爱怜的一种手段。”失落之后的不忿、潜移默化中对规矩的顺从和对特权的渴望,这些无形中怂恿着女孩们接近社会所铺就的性别期待:迷恋身体与容貌,沉溺物质,信仰爱情。
莎士比亚在悲剧《泰特斯·安德罗尼克斯》中,曾展现了男性期待的两种基本女性模板——天使与妖妇。这也是大多男性作家所期许的女性形象和创造共同点。天使,美丽纯真、善良顺从的拉维尼亚,作为男权社会的献祭品,永远逆来顺受。而如此懦弱沉默的存在,依然极具象征意义的让强暴者割去了她的舌头,致使其永远无法开口。
也许可以想象,丧失说话能力的女人更接近父权社会的理想女性。在古代中国,“娴静”“不参政”等赞誉和“牝鸡司晨”的谴责,则很好的证明了这点。西方哲学传统里,女性同样是“他者”,一个被阉割的不完整男人,带着二元对立的“反面”、“否定”、“缺乏”等烙印④。相对,男性却总是表达主体,如法语“人类”一词,甚至不是中性而是阳性即是明证。至于《周易》“阴阳说”中,男性为“阳”女性为“阴”的定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⑤同样也是父权社会为确立统治所寻求的理论依据,更是正大光明剥夺女性话语权、禁锢女性思想,从根本上完成对女性的奴役和驯服。
而就经历了几千年“菲勒斯中心主义”深层影响的女性群体而言,也很难真正体会和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毫无所觉的完美扮演着“第二性”的角色。贞妇烈女,以幸福和生命去捍卫“三纲五常”的不平等不合理规则,并以此为据,相互戕害。除少数叛逆者流火一般的抗争,女性群体的历史可谓是万马齐喑。如此背景下,今日争夺话语权和笃守自我的行为无可厚非,而因此矫枉过正更加迷恋自身容貌,放纵于物质享受和爱情体验,此种情况也很难判断是源于男权高压还是女性的自我生长。
无论如何,随着19世纪“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女性”这一形象,终于从牛羊、货物中脱离出来,成为“人”的一部分。而之后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的崛起,话语权的掌握,女性主义无论在政治还是文学上,都呈现出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据莱奇和萧瓦尔特已有的理论可得出:中国当代女性主义作品,尤其是80年代后,当处于发掘、笃守自我,脱离单纯“女人气”和具暴力革命性质的“女权”斗争阶段,开始运用话语权,跃上文坛。然而,一方面话语权不被主流“正视”,呈现出僵持的局面;另一方面,目标不明确性或方法的错误,也造成了女性作品中的一些糟粕。
梁启超说过:“一时代中含有过去时代之余波,与未来时代之余孽。”不敢说卫慧、绵绵“用皮肤对抗男性世界”的做法,就一定就是“余孽”之流,不过若说《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的马蒂达只是一个改善男性情感世界的傀儡天使,那卫慧、绵绵其无法忽视的男性消费群,是否也说明这些恣意抒写着“私人化立场”的女孩,依然无可避免被性征化,成为凭借“身体展示”取悦男性欲望的妖女呢?
在我们聚焦女性文学问题时,作为女性知识分子徐坤,无疑是一个极佳的阐述对象。结合上述分析和文坛现实可以看到,在90年代女性作家作品中,“性别立场”和“私人化立场”得到极大的发展,简直可称为泛滥成灾。若说男性话语权下的作品具有扭曲女性形象的效果,那女性主义作品,尤其是一些女权主义作品的尖锐崛起,显然也带着对现实的扭曲。
不否定女性作家的出现,在对女性独有心理体验的挖掘上,确有不小突破:如王安忆、铁凝等笔下敏感细腻的情感和游离多变的思绪;陈染、林白等对传统的背弃,竭力发掘有别于理性、暴力、控制欲等男性气质的女性形象;以及上文曾提到的卫慧、绵绵等对女性独特性欲体验和领会的描绘,表达了对脱离男性依附的迫切要求。而徐坤作为知识分子大于女性的身份,不仅在对女性历史文化、自我身份、语言解构等深刻的描摹上,让同期女性作家望尘莫及,而其坚守的仿若中立的“文化立场”,使其尽力除去女性自我怜惜或膨胀,少有狭隘性别意识,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带有公平意义、让人信服的诚恳。
根据马斯诺需求原理,人有欲望,并且层层递进着。那女性最大的欲望是什么?波伏娃说:“女人最大的需要是迷住一颗男性的心。”不过如此隐晦的描述,并未直接点出女性易耽于情感的特点。女人需要爱情,仿若信仰神明、渴求甘露、耽于罂粟。对此,徐坤的《厨房》《遭遇爱情》,以及张悦然的一篇《竖琴,白骨精》做出了叙述化评点,也描绘了女性主义分期的三种态度。
以股市作喻,《厨房》中枝子与画家“神女有心,襄王无梦”的故事,是一个资产雄厚的投资者,欲图将所有钱投入一支绩优股,却发现该公司不搞股份制了,有一种猛拳打棉花不着力的憋闷感。而《游行》里的林格献身诗人,是一个被突然的跌盘吓得割肉逃的胆小鬼,鲜血淋漓然而终是没陷落其中。至于《白骨精》里那个沉溺于丈夫甜言蜜语,被榨干价值遗忘自我的女人,是对熊市视而不见,盲信“股市将有起色”的宣传,最终输得倾家荡产的殉道者。
徐坤经历过愤青般为女性主义呐喊的阶段,也有以男性视角尖锐解构男性世界的过往,如今她逐渐走入无差别的旁观者视角,其小说的这种转变以及之后所体现出的生命力,似乎说明了一些问题:我们是否一定要竭力开发有别于男性气质的女性形象?一定要尖锐到“描写躯体”才是女性的书写?
所谓性别塑造虽然是男权社会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任何社会的产物。偏执的性别意识在面对仍以男性为主导的世界时,并无任何让人可认清现实或达成目的的积极意义。文化语言学中,刘长林先生曾提出“文化基因说”,指出相比西方语言,汉语为阴性,其根源是中国人的大脑结构偏阴性。且不论正误,就像汉语并未排斥西方语言一样,女性的独立也并非一定得消灭男性世界。这种偏激的消灭有若仇富心理,本身就是对男性强权的承认。
然而女性是“人”还是“玩偶”,这不过是棋子与下棋人,怎样评估自身位置的问题。对于社会掌权者的要求,其实无论男女,本质都是一样的,不同的仅仅是形式。那些叫嚣着突出“女性特点”的人,若非无知便是为虎作伥。这或许是一种比“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剥削”更加隐蔽的手段和潜移默化的过程。然而可以推想到,在某些极端的女性主义关注者和挖掘者不遗余力的努力下,逐渐构建出的“女性形象”,是真正脱离男性主导掌控的角色,还是主流文化冷笑着设下的陷阱?那么到底是谁,确定的既有的女性形象?
在《俄狄浦斯王》中,父权彰显,母性被贬低到只剩生育功能的程度,语言和法制都划归到父权的名下。而其中创造力、语言和法制,并非就完全是父权社会的独有产物,而可以说是每一种社会的必然产物。也许我们可以猜测,一味拔出男性在我们田地里栽种的植物,并非必要,抑或其中的一些是我们本来就会栽种的呢?
女性被构建,男性同样被构建。如徐坤笔下的顾跃进,在驰骋商场之后“回归”一样,似枝子同样期望着家庭。难道说“顾跃进”只是一种女性对男性形象的扭曲?从现实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南希·史密斯的《只要有一个女人》诗中说道:“只要有一个女人,觉得自己坚强,因为讨厌柔弱的伪装,定有一个男人,意识到自己也有脆弱的地方,因为不愿再伪装坚强。”⑥所以,细腻、妩媚不是女人专长,理性、豪放也非男性特点,不过都是被构建的规则罢了。
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也只是想要破除仍在运行的男权中心规则,而创造出另一个新的规则体系。然而男性话语体系的解构和探寻、构建女性话语体系的过程,或许只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样,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无力撼动社会基石的今天,或许现实更偏向于美国女性主义立足于现实的观点,探索女性语言与女性框架只作为辅助。毕竟所谓话语权,落脚点野在“权”字是。当下的女性主义文学任务,或许应该是告诉我们现在的真实处境,构造一个可以实现的现实目标,而非是一味的想自觉跳进“主流”所挖的文字陷阱。不过“文以载道”这种想法,对于充满激情的文学创作者和阅读者来说,或许过于无趣了。
参考文献:
[1] 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 阮元.十三经注疏[M].中华书局.2008
[3] 徐坤.爱你两周半[M].作家出版社.2000
[4] 徐坤.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M].作家出版社.2010
[5] 张悦然.竖琴,白骨精[M].作家出版社.2004
[6] 主编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 主编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注释:
① 王涛.代际定位与文学越位——80后写作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1
②伊莱恩·萧瓦尔特,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文艺批评家。力图恢复女性文学和文化历史,追溯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呼吁从女性的角度进行课程和教学改革。
③ 伊莱恩·萧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M].2004:女人气(1840-1880,模仿)、女权主义(1880-1920,反抗主流传统的价值、标准,争取独立价值与权力)和女性(1920-,摆脱依赖对立面而转向内心、自我发现)
④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主编朱刚[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7:349
⑤ 阮元.十三经注疏[M].中华书局.2008:75
⑥ http://www.xbwhyj.cn/html/suibizatan/200810/05-414.html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