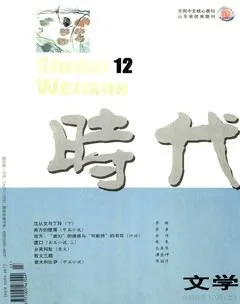南方:“虚幻”的诱惑与“可能性”的书写
《南方的堕落》,发表于《时代文学》1989年5期,是苏童的一篇重要的先锋作品,也是先锋文学的衍生概念中,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存在。对于苏童及其作品的评价,一直和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欲望写作等概念扭结在一起,苏童的小说,总是以细致绵密的抒情性想象见长。他以对人类隐秘欲望的发掘,对复杂人性悲悯的洞彻,以华美奇幻、典雅流畅,又略带忧伤的现代汉语,颠覆了经典现实主义对小说的叙事枷锁,在复活并追溯汉语小说诗性抒情的婉约风致的同时,为“现代中国表意”开创了新的小说风貌。然而,时间过去了二十年,我们如何重新看待这部小说呢?重读这部小说的意义又何在呢?在那些原有的阐释角度之后,我们在远距离地考察苏童那些氤氲而神秘的文字,不禁要问,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出现了那样一种叙事的地域文化想象呢?我想,这也许就是时间距离赋予我们重新解读该小说的一个灵感的源泉。
苏童小说的题材十分开阔,既有对日常生活隐私的考察,也有对宏大话语的理性怀疑;既有对启蒙精神的先锋探索,也有对历史的虚构热情。作为当代文坛活跃的追踪者,苏童的步伐是非常轻灵的,甚至是奇幻的。他总是在各种主义、思潮之间轻盈地游走,以狐步舞的华丽身姿,给批评家们留下种种阐释的空间。然而,他又是拒绝阐释的。他的小说,绝非“新历史主义”、“先锋小说”、“新文人小说”等标签可以简单厘定的。很多作家,都将苏童的转型,作为90年代以来先锋死亡的例证,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上朔,就会发现,所谓“先锋”概念本身,其80年代末期的定义,就充满了太多中国独特的体验性质素和表述特点,也并非先锋就可以概括。其中,先锋小说家如何“面对历史”的问题,一直是批评界关注的焦点。对于先锋小说家的指责之一,就是对历史的“解构”和“回避”。其实,在苏童的先锋创作阶段,也不能仅仅用这类话语来限定他的历史写作态度。例如,我们很容易用“南方主义”等带有东方学意味的话语方式,来解读《南方的堕落》这部小说。然而,这样的分析,似乎又过于简单,容易落入“后殖民”的简单阐释公式之中。因为中国80年代末期之后的南方书写,远远要更为复杂。苏童笔下的南方世界,不仅是对中心的一种边缘化的欲望想象,更是中国在80年代中后期面对旧的宏大叙事分化,消费时代崛起,所产生的文学现代性的叙事策略。在中国的传统地域想象中,中国北方,一般都与仁义、勇武、刚强、豪迈等概念相联系,而我们对南方的正面想象,则与温柔、多情、精致、文化相联系。南方文化,本来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就较北方来的更“边缘”一些,自由一些,也更多了一些浪漫和想象。北方文化正统庄严,雄浑严肃,却也出强盗和亡命徒。苏童选择了“南方”,正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时代选择了南方,来完成“诱惑”的符号仪式。而这个南方,却恰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而对北方的负面想象,应与暴力、残忍、血腥与粗鲁、专制等概念相联系。
由此,我也想到了在贾平凹、高建群、陈忠实、京夫等陕军众作家笔下的“北方世界”,同样是一个由“历史负面”组成的北方,那些土匪、妓女和流民、暴乱者,共同构建了一个狂暴而浪漫的神秘世界。即使在《白鹿原》中出现了大儒形象,却也怪异地联结着那古怪而蓬勃的性欲。那些黄土遮天的反叛者的北方世界,如同苏童邪恶而潮湿的南方,同样构筑了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小说叙事地理的两座“幻城”。而有所不同的是,北方的世界,长满了金戈铁马的喧嚣与道德批判的野心,似乎更为擅长树立“主体性”的幻觉,更具有国家民族叙事的某种宏大性;而那感伤而淫荡的南方,则似乎更为贴近古典小说中的某一部分,更适合表现所谓“个人化”的情感想象。
同样,二者的不同还在于,南方总是在“诱惑”中堕落着,而北方却总是在“拒绝”中飘荡着。然而,二者的根,同样无处找寻,无处安放。那些北方作家笔下的北方世界,已不是张承志《北方的河》中那些现代英雄般的国家民族寓言。宏大而庄严的现代世界已坍塌而陷落,所有主体的承诺均以落空,有的只是力不从心的缝补和再次整合的奢望,只是欲盖弥彰的慌乱与煞有其事的嫁接。那些出现在陈忠实、莫言、张炜等作家笔下的80年代末期之后的北方世界,只能以拒绝的姿态,将主体的幻城,飘荡在一片历史的尘埃之中。而与此不同,南方在苏童的笔下,则总是以诱惑的方式完成自己的肖像的。“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魁力的存在”。王德威在对苏童的评论中,对“诱惑”一词做了细致解释,而他对虚构的民族地理学的理解,也让我们在解读苏童地域想象时,有了很好的切入角度。他从鲍德里亚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理论指出,符号的魅力,来自它与指涉物的脱节,并自行衍生繁殖出无限新意:“苏童的南方如果已成为他的正字标志,正是因为他的南方早已被抽空了需要指涉的实体,悬浮飘荡,却又摇曳多姿……南方的堕落与死亡,本身就可能是一个不断被炒作的迷思,因为南方可能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如果南方的存在是虚幻的,南方的死亡也只是一种虚拟,一种诱惑。”其实,诱惑的本质在于,事物显现出大于它本来面貌的魅力,而这种魅力却是在若即若离的距离感的变化中,挑动接受者的欲望想象。诱惑起自魅力,而终结于想象。诱惑的特征也即在于它的这种在“真实”和“想象”之间的中间状态。这不仅是消费时代的艺术符号的共通性之一,也是弱势文化的天然策略,也反映了苏童的作品所透露出的80年代末期特殊的时代信息和转型期的民族文化心理。因此,苏童的小说,也具有着不可抹杀的民族志学的影子,成为我们解读那个时代的证词,进而从微观处考察我们当下时代的文化症候的恰当的窥入口。
由于“诱惑”的品质,苏童的小说,可以轻易地与影视文化接轨,并成为1990年代消费文化与纯文学嫁接的既得利益者——这也反映了苏童小说本身的通俗性和灵活适应性。那些南方的神秘故事,不仅适合于文学想象,而且适合消费文化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允许下,进行符号增值性活动。而与此相对应的,《白鹿原》、《古船》等北方作品却因其明显的意识形态批判性,而很难得到影视文化的青睐。同时,也是由于“诱惑”的品质,苏童的南方世界,恰恰隐喻了中国文化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弱者地位和边缘身份,也指涉了中国先锋文学突破社会主义宏大叙事文学所不可避免采取的叙事策略。南方,是弱势的,但南方又是美丽的,充满了诱惑的。由此,苏童就以那些欲望泛滥的南方流言,那些精美怀旧的历史想象,实现了对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性,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双重否定和超越。苏童试图通过那些新颖的叙事感觉、主题、人物、故事,以及对语言技法的迷恋,从而对历史庞大的意识形态权威,进行感性“溶解”,从而恢复我们面对历史时更为个人化的复杂体验。苏童解放了我们的文字触觉和感观经验,为我们描绘了一副副“欲望涌动”的另类历史。《南方的堕落》、《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飞越枫杨树的故乡》、《罂粟之家》、《祖先》等一系列先锋历史小说,苏童带有“灵龟预言”般魔力的语言,用一个个神秘莫测的历史文化意象(如罂粟),剥落了历史庄严却冷酷的外衣。然而,这种否定,同样也是巧妙而温和的,以不触碰现实逻辑为基础的。在这一点上,同样是先锋文学家,苏童和余华、莫言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性。南方的欲望和美丽,寄托着有关主体性的想象;而南方的颓废与邪恶,又在彰显着弱势者的驯服。苏童的南方世界,似乎离我们很近,又似乎离我们很远,抑或说,这个世界总是在远与近之间幽灵般的游荡着,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秘史和符号化的悲剧性寓言。
具体考察《南方的堕落》,我们则发现,在这部小说中,有一个边缘化的叙事者“我”。我既是香椿树街的流言秘事的见证者和旁观者,也是这些事件的亲历者。而“我”对南方的氛围和故事,则有着迷恋与厌恶的双重意味。我见证了有关梅氏茶馆的兴衰,而正是迷恋与厌恶的双重情绪,使得南方成为一种被过量被关注的“风景”:“我从来没有如此深情地描摹我出生的香椿树街,歌颂一条苍白的缺乏人情味的石硌路面,歌颂两排无始无终的破旧丑陋的旧式民房,歌颂街上苍蝇飞来飞去带有霉菌味的空气,歌颂出没在黑洞洞的窗口里的那些体形矮小面容委琐的街坊邻居,我生长在南方,这就像一颗被飞雁衔着的草籽一样,不由自己把握,但我厌恶南方的生活由来已久,这是香椿树街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记。”这种写作策略的出现,无疑与“诱惑”的品质有关。正是在那忽远忽近、亲近而又排斥的悖论性情感中,“南方”才得以成为一个时期国家民族的另类寓言。苏童试图颠覆那些宏大的历史,甚至不惜在梅氏茶馆挂上一个无字的匾额。然而,苏童绝不是一个叛逆者,顶多算的上一个颓废的另类者。所以,有关个人化书写的欲望,也就不可避免地沦为了一次有惊无险的文字演习。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定义为“风景”的呈现。这里的风景,不是指一种自然风景,而是现代性赋予现代文学时,所呈现出的特定能指。 而“南方”无疑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延展的一个重要且标志性的“风景”。姚碧珍与李昌的奸情,红菱的不伦之欲,也因和尚桥的存在,成为南方秘史的一种印证。 作家执意挖掘正史背后野史的细节,见证了那些淫荡的人生和无数隐秘诡异的死亡。而死亡,成为“南方诱惑”的高潮部分。它开始于欲望,而结束于各式各样的死亡,如金文恺痛苦的瘫痪之死,红菱的被谋杀,李昌被枪决。死亡,以我们最熟悉而又最陌生的气息,将诱惑的本质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小说结尾写道:“于是我真的跑起来了,我听见整个南方发出熟悉的喧哗紧紧地追着我,犹如一个冤屈的灵魂,紧紧追着我,向我倾诉它的眼泪和不幸。”“南方”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所有对于“南方”的想象,都会变成“压抑真实”的历史的阴影而存在。那么,真相在哪里呢?那些鬼魂一般飘荡的南方灵魂,继续以诱惑的方式纠缠着所有历史的好奇者。
其实,《南方的堕落》这篇小说,算不上苏童“南方系列”小说的巅峰之作,而应该是一个开端。真正很好地体现苏童的写作意图,并形成比较成熟的美学风格,还在于长篇小说《我的帝王生涯》之后精致亮丽、又哀怨缠绵的小说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历史窥视者和历史批判者的目光合二为一,历史的想象与历史的疏离也合二为一,其价值感和审美感距离,更为冷静而稳定,也更为强烈、鲜明,其语言魅力也更为充足而丰沛。苏童的历史小说,其叙事主题、技法、态度,也经历了“解构历史”——“想象历史”的转变。不可否认,先锋时期的苏童,面对历史的写作,仍有很多无法言说的苦恼。历史被消解后,是否还应存在意义?如果有意义,那么它的价值形态又如何?历史的颠覆如何与个人化复杂历史体验更好地结合?对此,很多批评家从日常经验与抽象概念的紧张关系、先锋小说家的美学突围、消费时代文学先锋性的消失、后现代主义对高雅与通俗的混淆等方面进行了细致阐释。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先锋小说,既是启蒙精神呼唤“人”的主体性产物,又是80年代启蒙文学“弑父”的“逆子”。它对启蒙的颠覆与语言学拯救,最终以极端化的逼仄而告终。正如苏童所言:“当时我感到,再个性,再自我,写到一定的份上,空间也会越来越小,慢慢耗尽,有了这样的意识之后,脚步就会向后退,在形式的要求上出现摇摆性。”当抽象“先锋个性”,将目光投向那些现代性的未完成状态,必然会对启蒙本义,诸如个体的人、人性的丰富性、现实批判性,进行某种程度“复归”。在启蒙反思框架内,先锋小说的集体与个体的抽象化紧张关系,则再次以“经验化”历史,进入作家的描述范畴,而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关系,则变得更舒缓,呈现出“有机融合”的契机。可以说,《南方的堕落》对于苏童的写作,以至于对于先锋写作而言,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在继《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等小说后,第一次将有关“南方”的地域性想象,以概念的方式加以确立,同时,这也标志着先锋文学在颠覆正史的同时,将那些旧时代的亡灵,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重新复活于我们的文化视域之内,并赋予了他们新的解码口——这其间,既有着个人化书写隐秘曲折的抗争,也有着新消费时代到时妥协的呻吟。“南方的诱惑”,确立了先锋小说的美学风范,也为先锋的迅速衰败与转型,埋下了沉重的伏笔。因此,重读这篇《南方的堕落》,我想,对于当代文学史而言,将会是一次非常有益的回顾与反思。
参考文献:
[1]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123页。
[2]林舟.《生命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78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