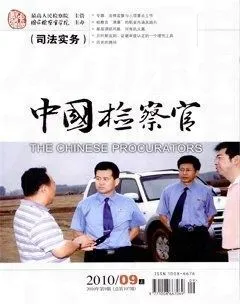好人还是坏人
2007年末,我所在的公诉二处承办了这样一个案件:原广东省法院保安人员许霆使用其银行借记卡在柜员机上取款时,发现柜员机出现故障,其在明知自己的银行账户只有170余元的情况下,取走了17万余元。我院以盗窃罪对许霆提起公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许霆无期徒刑。这一判决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关注。许霆上诉后。广东省高院将该案发回重审。在纷纷扰扰的争论中,好奇心驱使着我很想去旁听重审开庭。没想到过几天,我接到领导的电话:“许霆案重审,院里决定增加一名公诉人,派你去。”按照分工,我负责庭审时的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我的搭档负责法庭讯问。重审开庭那天,许霆一改原一审开庭时的寡言少语,面对法庭上记者的“长枪短炮”,神态自若,妙语连珠。“距离产生美”、“取款是为了保护银行财产”等言论成了当天报纸上的重磅花絮。在法庭辩论阶段,辩护律师发表了“许霆的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秘密性的要求”、“是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许霆的行为具有偶然性,不可复制。不必动用刑罚追究其刑事责任”等无罪辩护观点。针对辩护人的意见,我从许霆行为的时空特征上论证了其行为符合秘密性的要求:从许霆的获利行为是主动、故意实施等方面否定了其行为仅仅是民法上的不当得利:从刑罚的一般预防是指防止出现一般类似行为,而不是防止出现一模一样的行为,论证了其行为的应受刑罚处罚性。我的答辩意见获得了法庭的认可和业内人士的认同。
庭审之后,主流媒体的舆论倾向从同情许霆到质疑其行为的可宽恕性;很多网友也倒戈,由“挺许”到“倒许”。公众和学者们对这个案件的讨论和思考已不仅仅涉及法律层面,我也在思考其中的人性问题,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提审许霆时的情景——我们去提审那天已是2008年春节前夕,从许霆的一举一动上,看得出他已熟悉了看守所内的生活,在从提押室去讯问室的路上,他不时提醒不常来这个看守所提审的我们,哪里转弯,哪里上楼,懂事而又周到。在一脸平静地陈述完事情的经过后,他忽而提到自己的为人。他说,在邻居眼里,在熟悉他的人当中,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好孩子。是一个好人,没有人会把他跟“偷”联系在一起。他说:“本来,我们单位附近就有柜员机,可是为了省两块钱的跨行手续费,我就专门过天桥走到单位对面,找到这台商业银行的柜员机,谁知道……”他眼圈红红、一脸茫然地望着窗外:“唉。也不知道我的案子到底会怎么样?我还要在这里待多久?”面对这样一个邻居眼中的“好孩子”,我并不觉得他在撒谎。提审之后,我在公诉意见的原稿上加上了下面这段话:“不可否认,许霆的行为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碰巧那个时候,那台柜员机出错了,碰巧那个时候许霆需要取100元,碰巧许霆按“100”却多按了一个“0”,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巧合,也许许霆还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着。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巧合、诱惑和选择,以不变应万变的,只能是我们内心的善和对法律的敬畏,别人的东西即便无人看管也不能拿,不义之财不可取,如果许霆在发现柜员机出错的那一瞬间,内心能够恪守这样通俗而又简明的行为准则,他就不会面临生活可能发生巨大变化的这样一个境地。
2008年8月,随着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对许霆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许霆案在纷纷扬扬中落下帷幕。但是这个案件前前后后带给社会的法律层面的和法律之外的思考,也许并未随之湮灭。面对社会上一度出现的“柜员机坏了,不拿白不拿,为什么不拿?”这样的言论,我曾深感痛心。信教的人相信上帝和神灵无所不在地俯瞰着众生,俗世中的我们是否也应当将“去恶向善”这盏明灯时刻点亮在心
- 中国检察官·司法务实的其它文章
- 冬日暖阳
- 历史的拷问
- 忠诚是一种义务
- 控方卷宗笔录运行之审思
- 检察和解的若干思考
- 简论宗教与法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