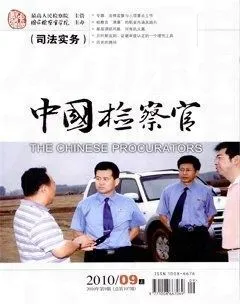历史的拷问
本案有着缺席审判的“硬伤”,久告不休的缠访经历,刑罚执行完毕之后启动再审、二审程序的罕见“履历”。为了求得并给予一个正义,笔者对历史进行了追寻,在惊叹昔日执法简陋之余,反思今天的我们围绕案件所做的点滴注定也会成为历史,被后人拷问。透过本案,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程序对于案件的意义、对于当事人的意义,责任除神圣之外还有厚重……
——作者
2010年4月28日,又是我职业生涯中印象深刻的一天。这一天。我与我的同事从广东东莞远涉千里到湖南平江去为一个缠访十五年之久的案件二审开庭。
从岳阳到平江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此时正是阳春时节。一路之上阳光和煦、泥土芬芳、树枝吐翠,百花怒放,池塘清澈、山峦如妆,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充盈着活力与希望。然而,我的思绪却游离于这美丽的平江春色之外,去将那些早已飘散在辽阔空间和漫长时间里的信号一点一滴地拾起、串起、回想……
1994年9月23日,刘某等人在东莞盗窃了一辆自卸翻斗车(价值95000元)到深圳福田销赃,事前通谋联系买主并销赃的袁某、晏某,协助盗窃并销赃的陈某被当场抓获。主犯刘某和实施盗车的邓某、吴某逃脱。事后,袁某、晏某、陈某均因犯盗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八年、七年。一审判决生效后,陈某于1995年3月20日被保外就医,回到原籍平江。袁、晏二人被送往服刑,1998年、2000年相继被假释。表面上看,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定罪量刑并无不当。可为什以陈某为此久告不休,这背后又有怎样的隐情?从本案扑朔迷离的经历中,我们又能感悟到些什么?
堵不如疏,救济渠道通畅才有和谐。1996年7月5日,陈某第一次以定性错误、被刑讯致残为由开始申诉,他先后到过省公安、检察机关和市公、检、法、人大等多家单位,不厌其烦地写申诉材料,1997年、1998年间得到的回复要么是申诉被驳回,要么是定罪量刑均无不当、没有刑讯、望息诉服判等等。至此。此事告一段落。2008年,陈某重新踏上申诉之路。这次他比十年前幸运,经检察机关协调,2009年6月4日,本案得以启动一审程序的再审。这对于陈某来说意义重大,他找回了参与庭审和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获得了一次在法庭上诉说的机会,尽管这一切已是时过境迁十四年之后,刑讯致陈某眼睛、左腿等部位伤残成为庭辩的重点。法庭上的陈某显得异常激动。历数其痛苦遭遇,仿佛要将积攒了十多年的辛酸与委屈全部倾诉,情急之下甚至要脱衣验伤。辩护人更是务求详尽地阐述了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内容。再审裁定维持原判,陈某提出上诉,于是便有了刑罚执行完毕之后的二审开庭。从本案艰难曲折的申诉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到目前我国社会运行机制的某些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衙门难进,事情难办,本位思想等等。很多情况下弱势者蒙冤受屈时。救济手段十分有限,有人因为申诉前途渺茫,干脆选择放弃,部分人虽然能坚持下去,但终因法律缺位、举证不能等种种原因劳而无功。无奈之下要么隐忍求生,要么铤而走险以求得社会的有效回应,这就是一些极端事件往往由小事引发的原因。有鉴于此,强大的政权力量与其选择迟缓或阻隔申诉上访的进程,不如完善救助立法,疏通救济渠道,唯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极端心态生成的土壤,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刑讯逼供,终将从沉重话题中走出。陈某伤到何种程度,如何形成的,何时形成的?既然遭受刑讯,为何当时不提出?即使公安阶段不提,案件到了检察院、法院为何也不提出?带着这些疑问,我向陈某作了详细询问。按常理。伤残者对致伤原因应该能终生记忆,但令人大感意外的是陈只能空泛讲述遭受殴打的情形,对于眼睛如何致盲,左腿如何致残等关键细节记不清、讲不出。这不能不使人考虑刑讯之外的其他可能性:牢头所为、自身疾病、出于意外。我又查阅了陈某当年的病历及诊断资料,仅能反映陈某当时有重感冒、肺部感染、视神经炎等症状。至于这些症状如何形成,诊断资料无从证明。陈某本人也讲不出所以然。而今,陈某就医十余年,伤情一定程度上治愈或好转,双眼早已复明,拄拐能行走,原始伤残状态已不复存在。再者,历经十余年人事变迁,很难就此事与当年的办案人员建立交流,更何谈取证。总之,无论从证据衡量,还是从时空考虑,认定刑讯的可能性很小。本案中陈某有无被刑讯从个案的角度虽已无从考证,但刑讯所带来的危害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长期以来,刑讯屡禁难止,不仅侵犯嫌疑人合法权益,容易酿成冤假错案,而且严重损害了我国司法机关形象,人们纷纷探求解决之道,如赋予嫌疑人沉默权,实行全程同步录相,向看守所派驻值班律师,非法证据排除等,这些想法都相当具有前瞻性、可行性。尽管刑事诉讼立法修改需要时间,相关证据规则也需要试行和论证,杜绝刑讯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但毕竟我们正在从教训中走出,刑讯终将成为历史。
理性回归。实体与程序不可偏废。翻开那早已发黄的卷宗,映入脑海的是超期羁押、单人审讯、代嫌疑人签名、人犯在押期间伤残、缺席审判、对被告人口头上诉置若罔闻……这些程序“硬伤”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白纸黑字,将这一切定格为历史,确凿无疑。我们无法将这些轻易开罪给那个特定的年代,如果办案人员的证据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再强一些,他断然不会愚蠢到单人审讯、代嫌疑人签名:如果监管与制约机制足够健全,刑讯会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如果法院坚持让陈某治愈后参与庭审,就不会铸成缺席审判之错:如果检察院能进行有效监督,也不会因失职失察而蒙羞:如果充分尊重被告人权利,定会对口头上诉及时受理……从历史碎片的纠缠中回归理性,前述教训早已或正在化作今日立法之完善,值得欣慰。毋庸讳言,我们对案件质量的评审或多或少有重实体、轻程序的偏见与惯性:对于程序的价值总有些不以为然。如非亲历本案的办理,我对程序的认识恐怕仍将狭隘而浅薄。本案让我深刻体会到,追求案件实体真实的过程好比流淌的河,程序好比堤坝。有了它河水才不会肆意泛滥,对于嫌疑人而言,严格的程序规定又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宪章。陈某的不幸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当年立法粗糙,执法水准不高,但究其根源仍在于片面追求案件实体真实。而对于程序正义漠然置之。在惊叹昔日执法简陋之余,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程序对于案件的意义,对于当事人的意义,它决不是哗众取宠的装饰,而是不可或缺而又无法替代的,实体与程序的价值应当受到同等尊重。
责任皈依,拷问历史的深切感悟。从事刑事司法无疑是神圣的,罪责权衡、轻重取舍、生杀予夺,一言一行,彰显威严。同时,神圣背后也承载着一份厚重的责任。本案的意义还在于它能告诫和警醒今天的我们如何对待责任。珠三角地区发案率高,案多人少的矛盾由来已久,于是催生了许多追求效率的办法,在庞大的人均办案数字背后。有谁敢肯定责任没有打折扣?又有谁敢保证不存在实体或程序的隐忧!还有。办案人员长期超负荷运转,多少激情被岁月剪裁,多少执着被时光掩埋,按部就班中精心钻研的锐气渐渐消磨,重复劳动中敬畏的法律不再充满神秘,曾经倍感神圣的责任变得虚无飘渺。如此一来,失误将不期而至,也许就因为一个细节的忽视,或者在关键问题上少一份坚持,你就有可能重蹈覆辙,续写佘祥林、赵作海的悲剧。这真是一种可怕的“适应”、恐怖的“定律”!历史无法重来,教训必须吸取。检讨前人过失的同时,我们也正在书写历史。今天我们拷问历史,明天我们也将被历史拷问。试问,若干年以后,我们有没有接受拷问的底气,而底气又来自哪里?我想它就蕴藏在今日之尽职尽责当中,编织于决定成败的细节之中。法施于人,虽小必慎。所谓责任,外部制约自不殆言,但它更源于内在。贵在自发,它是追求至善的理念,它是执法必严的使命,它是违法必究的担当,它还是历久不怠的坚持。责任没有保质期,如果有,我想应该是一万
- 中国检察官·司法务实的其它文章
- 冬日暖阳
- 好人还是坏人
- 忠诚是一种义务
- 控方卷宗笔录运行之审思
- 检察和解的若干思考
- 简论宗教与法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