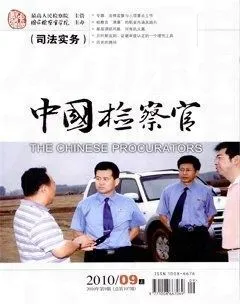论刑事起诉犹豫制度
宽严相济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刑事司法政策,尤其是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如何建立具有中国司法特色的起诉犹豫制度。我愿谈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供大家商榷。
一、中外不起诉制度的表现及比较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作了一系列规定,构成了我国刑诉法上的不起诉制度。共分为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三种,
我国刑法在规定不起诉条件的同时,也规定了不起诉排除条件及相关条款,也即:1.犯罪嫌疑人一人犯有数罪的:2.共同犯罪案件中的主犯,对从犯提起公诉的;3.犯罪嫌疑人不承认有犯罪事实的:4.有附带民事诉讼的。在这些情况下,人民检察院一般不得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不起诉制度不仅在我国存在,在国外许多国家也都纳入司法体系,但对于检察院或检察官的不起诉决定权,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看却不尽相同。尤其表现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在英国、美国,检察官决定不起诉的案件主要是证据不足和起诉违反公共利益的案件,如对未成年初犯,因家庭纠纷引发的案件是否起诉,检察官可以不符合公共利益为由,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德国刑诉法典153条规定有五种情形,可以决定不起诉:(1)轻微案件不必追究;(2)暂时不予起诉,经法院和指控人同意,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不提起公诉。但要求其履行一定的义务:(3)在免予处罚的前提下,经法院同意,检察院可以不诉:(4)以行为自责时不予起诉,但对广一些的轻微的犯罪行为,检察官不起诉时可判一定数额的罚金:(5)不重要的罚金刑案不起诉。在日本,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48条规定“根据犯罪人的性格,犯罪的轻重、情节以及犯罪后的状况,认为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之必要时,可以不提起公诉。日本刑诉法规定了不起诉权,但未规定有关不起诉的具体内容。日本检察官决定不诉的主要依据是检察厅根据先例概括出的指导准则,
以上中外具有的不起诉制度,笔者对其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归纳如下:
中外制度的相同点是。不起诉的对象都是轻微案件,中外法律都给了检察院(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检察官不诉的自由裁量权,都规定了某种限制。
中外不诉制度的不同点是,外国有起诉犹豫的规定,即暂缓不诉,中国没有起诉犹豫的制度。外国检察官对于不起诉的案件可判处一定数额的罚金或要求履行一定义务,我国却没有这样的规定。
我认为,我们应当充分汲取外国的经验,弥补我国不起诉制度的不足,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研究起诉犹豫制度及其具体操作程序。
二、起诉犹豫制度的理论渊源和现实意义
起诉犹豫制度是在具备不起诉的基本条件之后,暂不起诉,以观后效。这种制度,一可以节省诉讼资源:二可以提高司法机关的效率:三可以有效的通过教育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四可以延长检察机关工作的纵深度,由起诉或不起诉延伸到对人的教育改造,有利于社会稳定;五可以避免短期自由刑过程中的交叉感染。起诉犹豫制度,在实践中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但要想在我国建立起诉犹豫(即暂缓不起诉)制度。必须深入思考,破除一切不切实际的观念。
起诉犹豫制度的建立,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分析,在实务部门及各级检察机关具体操作中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阻力,但在理论界则多有人杞人忧天。为了实现观念上的转变,我们必须对起诉犹豫制度得以产生的背景及其演变过程作一个历史的回顾,
起诉犹豫制度是检察制度的一项内容,它缘起于效率优先和便宜主义的政策思想,而不是来自检察机关的职权主义。回顾世界上不起诉制度产生的背景,各个国家都是在犯罪率大幅度上升,案件堆积如山的情况下出现了这样的制度,当社会上犯罪行为风起云涌,积案成山的情况下,全国人民的目光就会聚焦在效率优先这样一个视点之上。在起诉职权主义者看来,不起诉、起诉犹豫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法院的审判权,因此,起诉犹豫制度,尤其是在犹豫之前由检察官判处一定数额的罚金制度或履行某种义务为内容的起诉犹豫制度就是在侵犯审判者的权限,因此断不可取。笔者认为,公检法三机关的设置无疑是依据现代刑事法制观念中的职权主义设置的,三个机关也依法各自履行各自的职权。但是在刑事法制的立法中,从来不排除在一般规定之外,作某些特殊的规定,这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产物。在刑事法制中我们在坚持职权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又会做一些例外的规定。我们的刑事法正是职权主义和便宜主义的恰当结合。如在刑法中规定单位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同时又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如在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有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权利,同时又列举出九种不准不起诉情形的规定。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职权主义不应当成为在我国刑诉法上规定起诉犹豫制度的障碍。
便宜主义会导致不诉权的滥用。因此,既然不能同意起诉犹豫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确立。我们认为为了提高效率,就必须给检察官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这种权利并非不受制约。如在美国有前置程序予以控制,在美国重罪案件起诉与否,要由大陪审团批准,只有轻罪,检察官对于不起诉才有充分的自由裁量的权利:在日本设置了后置程序,检察官对于公务人员决定不起诉的,被害人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予以审理,除此之外,还从民众中选出检查员。对不起诉的案件实行监督检查。任何制度都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有开必有关,才能成规矩就方圆,起诉犹豫制度同样如此。
我们跨越了职权主义的障碍,去掉了检察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担心,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呼吁,应当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起诉犹豫制度。
三、我国建立起诉犹豫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建立起诉犹豫制度必须根植于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中国本土文化一向不相信缘起于西方的绝对的职权主义。如古人在《周礼》中写道“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制之。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遇到灾荒暂缓使用刑杀的方法来处罚犯罪问题。所谓暂缓使用刑杀的处罚,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对于已经发生的犯罪暂时不予追查,二是对于已经判决的犯罪暂时不予执行,留在灾荒过后再去处理。汉代有秋审制度,具有暂缓追究刑事责任之意。宋代有“录其后效,听其自新”的制度,这些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起诉犹豫制度,但他已经可以被认为是现代起诉便宜主义的萌芽。
我国现代刑法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确立了不起诉制度,在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曾颁布《关于县市公安机关与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权责的规定》就规定了存疑不起诉、不构成犯罪不起诉、酌情不起诉三种,但这时把不起诉权交给了公安机关。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了6种不起诉的情形。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又作了修改。内容前面已述不再重复。这证明我国对于不起诉的制度,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应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不诉犹豫制度。
中国检察机关可以与法院为中心的现代职权主义有所不同,我们公诉人莅临法庭,不仅以公诉人身份出现,还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履行职责。因此,我们检察机关名义上的地位比任何西方国家的检察官、检察机关都高,属于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我们检察机关也应当拥有。
我们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检察机关适用不起诉权已经作了种种限制。即规定了前置条款,又规定了后置条款。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认为证据不足的,可以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补充侦查,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这是限制检察官不起诉权的前置条款。对于1979年《刑事诉讼法》法典所规定的不起诉的内容增加了共同制约的条件“犯罪情节轻微”,否则不准不起诉,还规定了后置条款,规定不起诉的案件,被害人不服,可以请求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此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起诉制度有别于外国,他既有前置条款又有后置条款,还有不起诉条件的共同制约条款。可以充分保证我国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不被滥用。
基于以上分析和探索,笔者建议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3款进行修改,第142条第3款是这样写的“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应增加“也可以做出暂不起诉,而要求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刑法所规定的非刑罚方法所确定的义务。”
综上所述,扩大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规定具有中国特色的起诉犹豫制度在实务上有需要,在理论上行得通,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