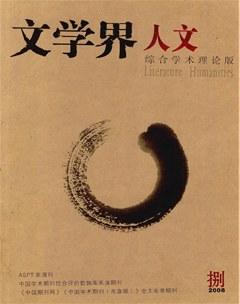传统与转化:李泽厚对传统儒学的反思及其局限
郭景华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泽厚对传统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并探讨其现代转化的路径。通过解析其哲学基础,结合李泽厚所处的时代、思想背景,李泽厚对传统对传统儒学的反思的意义及其局限才能得到同情地理解。
关键词:李泽厚;传统儒学;现代转化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8-130-04
如所周知,李泽厚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国思想史、美学和哲学领域。综观李泽厚的学术活动轨迹,由中国思想史开端,进而是西方哲学(主要是康德哲学)和马克思哲学,最后回归到中国儒学,其演进轨迹耐人寻味。
经过自近代百余年以来古今中西文化的碰撞、撕裂的中国人,尤其是经过“文革”思想浩劫的学者,十分明显地感觉到了精神、信仰的无家可归。海外现代新儒家自身也认为,由于失去制度化个根基,儒学业已“花果飘零”(唐君毅语),变成所谓的“游魂”(余英时语)。在李泽厚看来,中国当代思想的建立不可能西化,即不可能奠基在古希腊文明和中世纪基督教精神基础上,但也不能回到新儒家宣扬的孔孟陆王的“心性之学”。职是之故,当人们在他的启发下大谈主体性时,言必称康德或萨特时,李泽厚自己却又告别康德,走向了反省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历程。“应该站在广阔辽远的历史视野上,站在中国民族真正跨入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文明与全世界文明交溶会合的前景上,来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仁学结构进行新的研究和探讨。这样,对孔子的再评价,才有其真正巨大的意义。”Ⅲ事实上,写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孔子再评价》没有辜负李泽厚的期望,它在李氏整个传统文化研究中应该可以算是一篇非常有分量的文章。此文中提了许多新颖的概念,如“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文化心理结构”等,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其独特的学术视野。李泽厚抛弃了当时学界纠缠不清的关于孔子生活时代的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而是将孔子放在中华传统铸型之初以及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背景下评价孔子及其学说。其中,“汉民族文化一心理结构”、“道德主体性”等概念,对儒家礼仪制度的人类学探究,孔子思想中的忽“礼”而推“仁”,对孔子“仁”的结构主义分析,凡此种种,都显示了李泽厚孔子研究的与其建构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精神联系。李泽厚通过对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的考察中,认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自孔子“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内在自觉”形成“心理本体”始,其间经由孟子、汉儒,直至宋明理学,无不指向其主体性哲学之核心一心理本体建构。尤其对于宋明理学,李泽厚给予很高评价,“由于宋明理学细密地分析、实践地讲求‘立志、‘修身,以求最终达到‘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志结构,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空前地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在世界思想史上,大概只有康德的伦理学能与之匹敌或相仿。康德著名的墓碑:‘位我上者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与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表现人类主体伦理性本体的崇高上,是同样伟大的。人的本质,一切人性,并非天生或自然获得,它们都是人类自我建立起来的。对人类整体说是这样,对个体也如此。……与康德不同的是,康德的道德律令具有更多的可敬畏的外在性,宋明理学在理论上却保留了更多的人情昧。在康德,是本体与现象界、伦理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分裂;在理学,是赞化育,与天地参的情理谐和、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以建立区别于动物的人类本体,在精神空虚、价值崩溃、动物性个体性狂暴泛滥,真可说‘人欲横流的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有没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宋明理学的理论成果和世界意义,是一个尚待深究的题目。”Ⅻ
李泽厚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系列研究论文的发表,学术界,特别是青年一代学人便非常敏感,认为他的学术立场已经背离了写作《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时的批判向度,思想业已趋于保守。1986年,李泽厚专门撰文澄清,不乐此誉。但是90年代中期后,对于有人目之为大陆当代新儒家,他欣然接受。但是他同时多次强调,他和现代新儒家是有很大差别的。
这种差别就表现在关于传统儒学的认识和现代性的转化上。在80年代,李泽厚不仅反对现代新儒家对传统儒家的理解,“如果仅以孔孟程朱或孔孟陆王作为儒学的主流和‘正统是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程朱陆王所发展或代表的只是儒学的一个方面。儒学生命力远不仅在它有高度自觉的道德理性,而且还在于它有能面向现实改造环境的外在性格。这就是以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命题为代表的方面。”“如果说,孟子、《中庸》和宋明理学在‘内圣人格的塑造上作了贡献的化;那么荀、易、董和经世致用之学则在培养人格的‘外王方面作出了贡献。所谓‘现代新儒家轻视和抹杀后一方面,并不符合思想史和民族性格史的历史真实。”而且对现代新儒家自身的理论建构的缺陷作如下判断:“现代新儒学不管是熊、梁冯、牟,不管是刚健、冲力、直觉、情感、理知逻辑或道德本体,由于都没有真正探究到人类超生物性能、力量和存在的本源所在,便不能找到存有与活动、必然与自然、道德与本体的真正关系。”
90年代,针对现代新儒家的“儒学三期说”,李泽厚提倡“儒学四期说”。他认为,“儒家三期说?芷理论上有表层和深层的四大偏误,在实践上也有两大困难,所以不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构不成一个新的时期,恐怕难得再有后来者能在这块基地上开拓出多少真正哲学的新东西来了,现代新儒家只是现代宋明理学的回光返照,它是过去的暮影,不是未来的曙光。于是李泽厚提出“儒学四期说”,“我所谓‘四期,是以孔、孟、荀为第一期,汉儒为第二期,宋明理学为第三期,现在或未来如要发展,则应为虽继承前三期,却又颇有不同特色的第四期。”
那么,中国传统儒学如何实现现代转化呢?主张“儒学三期说”杜维明认为:“儒学要有发展,必须接受西化的考验,但我们既然想以不亢不卑的气度走向世界,并且以兼容并包的心胸让世界走向我们,就不得不作番掘井及泉的功夫,让儒家传统(当然不排斥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其他传统、特别是道家和佛家)的源头活水涌到自觉的层面。只有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儒学才有创新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杜维明把知识分子的群体批判意识作为儒学向现代转化的关键,而李泽厚李泽厚认为,必须面对当代现实问题的挑战,这才是儒学发展的真正动力。儒学及其传统所面临的当代挑战来自内外两个方面,而都与现代化有关。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是反传统、反儒学。这是因为现代化带来了“个人主义”的问题。现代化使个人主义(个人的权力、利益、特性,个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与传统儒学(人道存在及本质在五伦关系之中)成了两套非常矛
盾与冲突的话语。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的体制、观念和方式,如社会契约、人权宣言等等,与传统儒学扦格难通,凿枘不入。因此,儒学如果要在现代社会有所作为,必须另辟蹊径,另起炉灶。80年代,在《略论现代新儒家》一文中,对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内圣”和“外王”内涵如何向现代转化做了初步的思考。李泽厚认为,“第一,“内圣”和“外王”的关系。“外王”,在今天看来,当然不仅是政治,而是整个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现实生存,它首先有科技、生产、经济方面的问题;“内圣”也不仅是道德,他包括整个文化心理结构,包括艺术、审美等等。因之,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由“内圣”决定“外王”的格局便应打破,而另起炉灶。第二,现代新儒家是站在儒学传统的立场上吸收外来的东西以新面貌,是否反过来以外来的现代化的东西为动力和躯体,来创造性地转换传统以一新耳目呢?”具体的阐发在《漫说‘西体中用》、《再说“西体中用”》等文得到体现。
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遭受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质疑和批评,他们或从政治着眼,认为他是改头换面的“西化派”,或从文化着眼,以为他是自由主义文化派在大陆的代表。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没有和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相联系,因此在批判其观点谬误的同时,并没有多大学理上的说服力。事实上,在现阶段,李泽厚过份地强调他的工艺一社会层面这个实践哲学的基础,对西方现代科技的崇拜,连同他被人称为粗俗的“吃饭哲学”,都是面向中国目前存在的具体客观现实而阐发的,故而他在经济上主张可以大胆探索新形式,促进经济发展;政治上主张在维护党和政府权威下,加强党内民主,开放社会舆论;文化上要改变“三教(宗教、政治、伦理)合一”的状况,逐步实现三教分离,尤其在道德层面,要区分“宗教性道德”(个体的安身立命,终极关怀)和“社会性道德”(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生活的共同规范)。“总之,我认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必将逐步产生社会关系的改变和‘公众社会“公众空间的扩展和言论控制的失效,尽管这进程是缓慢的,逐渐的,有时甚至有反复,没有戏剧性的急剧变化,但倒可能会更坚实和稳固。”由此可见,尽管他的主体论理论包含着工具本体和情感(心理)本体两极,但是他目前对工具本体强调胜过情感(心理)本体也是事实,他希望通过一个强有力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性的变动,来促使文化心理结构的根本改变。这也就是由“外王开出内圣”的途径,这也就是儒家传统的现代转换。正因为李泽厚一再强调社会存在,所以有人批评他是“经济决定论者”,也职是之故,李泽厚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告别革命”说、“辛亥革命搞糟论”都是由于强调经济因素,所以出现了非历史主义的倾向,这都是李泽厚一相情愿观念演绎的结果。90年代以来,李泽厚的学术思想开始趋于式微。尽管他的一些观点、话题还在有些争论,尽管李泽厚表示:“我那些书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人认真注意。也许过几十年后才能被人真正认识,我常常只点到一下,就带过去了。”“我认为我的许多东西也许要等到三十年后才会被充分理解。”但这些都已经不能阻挡中国大陆学界告别李泽厚的脚步了。
李泽厚学术思想建基的主体论实践哲学,在80年代引起学术思想解放(如由主体论带来的人道主义争论)的同时,却由于主体性理论自身的理论的建构设计,就一直遭受不少争议甚至批判。如所周知,李泽厚的主体性理论资源来源于三个方面:康德哲学、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皮亚杰的结构主义理论。在他的主体性理论的两个双重内容和含义中,他一再言说他虽然把每个双重含义的第一个方面,也就是把群体的工艺一社会层面视为基础,带有决定性的要素,可他的主体性理论探讨的主题却是对人类本体的第二个方面,即提出作为主体性的主观方面的文化一心理结构问题,由此形成他的著名的“积淀”理论。李泽厚对主体性的主观方面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探究,取得了累累硕果(他的美学著作是这方面的最好展示)。但是身为美学家、思想史家、哲学家的李泽厚,绝对不会只满足于学术思想史的理论探讨,他更希望他的哲学理论能够在改革开放的现实中大显身手。因此,李泽厚不得不偏离他学术理论设计的初衷,特别强调人类群体实践的重要,强调人类群体由实践而积淀形成的群体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面,在无形中却消泯了人类个体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感性、偶然、生动的一面。由此我们可以看得出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影响的因子存在。康德在认识论中对人类先验赋予认识形式的强调,黑格尔对于人类精神现象自身流动的描述,都是某种理论抽象的演示,它们都是以牺牲人类个体大量的生动性(感性)作为代价的。无疑这种由近代启蒙发端而来的现代理论,由于过分强调理性对感性的支配,所以遭受后现代理论质疑和批判,也就是在情理之中。可是李泽厚却认为存在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只不过一种浪漫主义批评,对于现实改造没有多大作用。同时,李泽厚的主体性理论也负载了太多的内容,什么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感性的、历史的、心理的、群体的、个体的等等,他都想一网打尽。由此也就决定他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提出的概念诸多包容性的同时,也就失去了自身的边界而游移不定。“实用理性”是如此,“西体中用”也是如此。所以曾一度造成理论混乱。譬如,在“西体中用”,他在拓展“体”的含义时候,由于过份迷信“工艺一社会层面”这个社会存在的工具本体,对由此而积淀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能动性、反思性估计不足,对于传统文化中所拥有的精神价值认识也是不够的。因此,实际上在他的主体性理论中,逐步消解了人类主体性尤其是个体主体性的独立作用。因此,他对传统文化的“转化性创造”目标是犹疑的,因此并没有把它作为“体”来看待,他所继承的也只是传统的形式,所谓“旧瓶装新酒”。相反的,由于对西方现代化和科技的崇拜,他把它们都作为“体”,因此也就和所谓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也是殊途同归,只是一个缓和,一个激进而已。从这个意义上看,李泽厚这个“大陆新儒家”对传统文化的转化是有限度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李泽厚选择这种理论作为自己学术思想建构的基石,有他学术情境,我们在给予“同情之了解”的同时,也对他一直顽强固守自己的学术逻辑表示遗憾。其实,关于科技理性的危害,西方批判的声音就一直不绝于耳。史华慈教授说:“19世纪的物质主义进步观,……当时有整套的意识形态,诸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等,都持续地对于科技进步的非‘物质主义的、伦理的后果感到深切的不安与忧虑。科技经济的进步毕竟没能阻止屠杀犹太人的浩劫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惨剧。恰恰相反,它把古已有之的恶推向恶毒的新极致。……然而,事实仍旧是:大部分贮存在人类经验中的“信息”,并非建立在对于人类成就所作的“物质主义”的说明之上,而是建立在远远更为复杂的、对于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的”说明之上;在人类的命运中,追求幸
福与此种追求中所包含的吊诡(悖论),两者是分不开的。……就物质力量在一定限度内确实能够在不予限定的未来,减轻人类受磨难的苦楚而言,这种力量当然受到欢迎。不过,物质力量绝对不能替代人类长久以来在依据人文主义的观点去理解其自身的幸福所作的努力。因此,李泽厚对于包括现代新儒家在内的文化批判理论的作用和意义的低估,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一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中西方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都进行着仔细的清理。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方面,传统文化的研究路向业已走出原先的“挑战一反应”模式,一种注重从“内在理路”思考的传统文化研究取向开始时兴起来,这方面可以以余英时先生为代表,余先生指出:“现在深受西方论著影响的知识分子往往接受西方人的偏见,即以西方现代的价值是普遍性的(universalistic),中国传统的价值是特殊性的(parliticularistic)。其实,这是根本站不住的观点。其实,每一个文化系统中的价值都可以分为普遍与特殊两类。把西化与现代化视为异名同实便正是这一偏见的产物。”同时,余先生认为,文化变迁可以分成很多层:首先是物质层次,其次是制度层次,再就是风俗习惯层次,最后是思想价值层次。大体而言,物质的有形的变迁较易,无形的、精神的变迁则甚难。中国现代化的困难之一即源于价值观念的混乱,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看成的绝对对立的。从整体来看,中国的价值系统是禁得起现代化以至“现代以后”的挑战而不至于失去它的存在根据的。当前,我们应该把科学和技术严格加以区分,我们中国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认识西方“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我们所追求的仍是用“科技”达到“富强”的目的。无独有偶,在西方,譬如美国年轻一代的汉学家们,也大多抛弃了完全用西方冲击论来处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路径,他们强调,在“传统中国”的晚期,中国社会的每个层面内部都发生了内在变化的趋势。史华慈教授也认为,在古代中国文明框架下,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出现过像现代西方与“传统”过去之间发生过的那样全盘的质变性的决裂,所以他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时,提出了“通见”(vision)和“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两个研究视角。在国内,汪晖教授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皇皇巨著也可以视为从“内在理路”来探讨中国现代思想发生、发展脉络的产物。相对于李泽厚单一直线式的学术思维理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学术研究的路径越来越宽广,思维模式也日趋多元。
不过,即是如此,李泽厚的学术进路的意义仍是巨大的。它是一个直面现实、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的焦灼思考标记。李泽厚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站在中西汇通、传统向现代转化这个交接点上,对所有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李泽厚身上集中的各种矛盾,他学术思想建构中显现出来调和、折中的思维模式,其间引起的理论争执、教训,除了跟其主体性思维自身阐释的“前结构”先天不足紧密相联以外,还和这个时代症候也息息相关。在当今文化多元、思潮迭起社会,李泽厚固守主体性思维,宣扬“吃饭哲学”,理所当然被视为“过气”的表现。然而,李泽厚思想的意义不只是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他学术运思的进路,包括他思想的复杂性、含混性,对于处于相似学术处境中的我们,应该也有很大的现实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