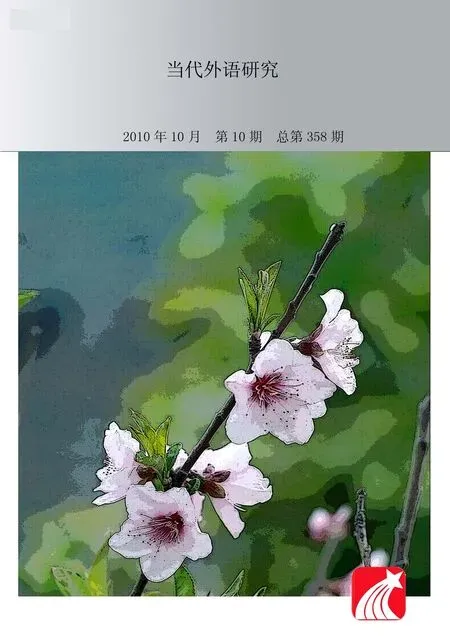语篇中的意识形态与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
——论马丁的相关理论及其应用
朱永生
(复旦大学,上海,200433)
马丁(James R. Martin)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自上世纪70年代末始,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在“话语语义学”(discourse semantics)领域(王振华2010),他从多个方面和角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拓宽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例如,他(Martin 1997a,1997b,1999,2000,2001,2010)提出的“语类结构理论”(generic structure theory)说明了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对图式结构(schematic structure)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丰富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观;他(Martin & White 2005)的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为人们从词汇层分析语篇的评价意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具体的操作方法,从而把人际意义的研究从Halliday(1985/1994)注重的语法层扩展到整个词汇语法层;他(Martin 2004a)的“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方法打破了已有30多年历史的“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消极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传统做法,希望语言学家们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建设性的态度消除不良的社会现象,为创建一个比现实美好的社会作出语言学家应有的贡献;他(Cranny-Francis & Martin 1991)提出的“语篇对抗性”(contratextuality)理论有助于分析不同的语篇对同一个事件或同一类事件是否持有对抗性的态度,从而看到语篇类型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Martin 2008,2009)的“个性化”(individuation)理论,侧重研究个人或话语社团(speech community)的语言特点,从而帮助人们看清支配这些语言使用特点的意识形态;他(Martin 2010;Martin in press;Zappavigna,Cleirigh,Dwyer & Martin 2009)积极倡导的“多模态话语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改变了单模态话语分析即只分析文本本身的传统做法,对其他模态的表义方式也予以高度的重视,从而使人们对人类如何使用不同的模态或符号系统表达意义有了更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本文将对马丁有关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学家应尽的社会责任的相关理论及其实际应用进行评述,以帮助读者厘清他有哪些不同于其他语言学家的观点及这些观点的应用价值。
1. 马丁有关语言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述
功能语言学始终把语言意义的产生、传递与理解看作是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但语言意义在哪里?同一类语篇能否表达不同的意识形态?如何分析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语言学家是否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对这些问题,马丁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1.1 意义在哪里
马丁继承了J.R. Firth,L. Hjelmslev和M.A.K. Halliday等人创建的功能主义语言学理论,以一种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的观点看待语言,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切入,研究社会文化与语言结构和意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在语言意义存在于哪里这个问题上,马丁与语言学界的大多数人有着不同的见解。
语言学界普遍认为,语言本身是由“音系学”(phonology)、“词汇语法学”(lexico-grammar)和“语义学”(semantics)三个层次构成的符号系统,意义存在于语义层。而马丁(1992)认为,虽然这三个层次之间确如Halliday(1978,1985/1994)所说的那样存在着“体现”(realization)关系,即语义层由词汇语法层来体现,词汇语法层由音系层来体现,但并不等于说只有语义层才有意义,意义存在于语言的所有三个层次:音系层、语法词汇层和他所说的“语篇层”(discourse),或者说在音节(syllable)、小句/单词(clause/word)和语篇(text)所有三个层次中。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研究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就不能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语义学,而应该对音系、语法词汇和语篇三个层次予以全面的关照。
1.2 同一类语篇能否表达不同的意识形态
1991年,马丁发表了一篇题为“语篇对抗性:颠覆的诗学”(“Contratextuality:the poetics of subversion”)的文章,首次提出了“语篇对抗性”这个术语。他分析了“生在美国”(“Born in USA”)和“星期天,血腥的星期天”(“Sunday,Bloody Sunday”)这两首著名的摇滚歌曲。他首先从语类结构(generic structure)、音乐结构(musical structure)、话语范围(field of discourse)、及物性(transitivity)和语气(mood)等方面对它们的异同进行分析,然后从语言和表演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对比,最后又从对话性的角度论述了这两首歌曲所包含的主流意义以及与颠覆相关的非主流意义,从而揭示了说明性语篇(expository text)彼此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可能存在某种对抗性的关系。
这项研究告诉我们,虽然有些语篇属于同一语类,但每个语篇的内部以及不同语篇之间可以有不同的、甚至彼此对抗的意识形态。这对我们研究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无疑有着一定的启发作用。
1.3 如何分析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们在分析话语意义时,已习惯于把研究重点放在与语篇类型这个概念紧密相关的“语域”(register)和“语类”(genre)上。马丁(1986)则认为,这样的分析难以解释语篇中的所有变化,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变化。人类不是喜欢独居的物种,而是喜欢群居的“政治动物”(political animal),因此在使用语言时,不仅要注意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制约,而且要考虑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话或任何一个词在意识形态上都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
马丁(1986)在“使生态学语法化:小海豹与袋鼠的政治”(“Grammaticalising Ecology:The Politics of Baby Seals and Kangaroos”)一文中指出,意识形态与语篇类型(discourse type)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虽然每个语篇都有意识形态,但相对而言,意识形态在具有争议的事件中表现得最明显,其原因是与这些事件有关的人通常都会以某种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文章中,马丁还告诉我们,人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对意识形态的界定也就不同。他认为,既可以对意识形态作“概要式的”(synoptic)解释,把它看作是一种与一群特定的语言使用者(language user)有关的“语言品种”(lect),也可以作“动态的”(dynamic)解释,把它看作是一种依赖于语言使用(language use)的语言变体。这就是说,意识形态不仅存在于各种地理变体即方言(dialect)中,而且也存在于各种功能变体即语域之中。忽视任何一种变体中的意识形态都是不可取的。
1.4 语言学家是否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
既然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每个语篇中都包含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那么,语言学家就面临三个选择:一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对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作静态的描写和客观的分析;二是像批评语言学家那样,以消极的态度分析语篇中的意识形态,揭露和批评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弊病;三是采取积极的姿态,在通过话语分析揭露社会问题的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措施。
在这三者之间,马丁(2002)选择的是第三个。他把热衷于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批评语言学叫做“水门语言学”(Watergate Linguistics),竭力主张语言学家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放弃“解构”(deconstructive)的做法,建立“和平语言学”(Peace Linguistics),以建设性的(constructive)态度对待各种社会问题,通过对话与和解,设计并建构一个美好的未来。
2. 理论的实际应用
马丁不仅在理论层面上对语篇中的意识形态与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身体力行,把这些观点应用到具体的语篇分析之中。在这里,我们将对马丁围绕政治语篇和学校教育中的意识形态所作的分析进行评述。
2.1 政治语篇中的意识形态分析
在所有语篇类型中,政治语篇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最为密切。在分析此类语篇时,马丁做了三件事。一是分析这些语篇中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各种语言手段得到体现的;二是分析这些语篇中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语言以外的手段得到体现的;三是主张语言学家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以积极的姿态对待这些语篇涉及到的敏感事件,不仅揭露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不公,更要努力寻求消除矛盾和解决分歧以达到和解的途径。
在第一个方面,我们以马丁(2006)的“对方言的解构:破坏性的旋转”(“Vernacular Deconstruction:Undermining Spin”)一文为例。Martin应用Halliday的功能思想和他自己提出的评价理论,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情感投入等方面对三个各有不同、但都与战争有关的语篇进行了分析。
第一个语篇是英国U2乐队的主打歌曲“星期天,血腥的星期天”(“Sunday,Bloody Sunday”),由Bono主唱,讲的是1972年1月30日发生在爱尔兰的一次由北爱尔兰民权协会组织的抗议游行,这次游行遭到了政府的残酷镇压。马丁从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的角度分析了这首歌曲对政府残酷镇压此次游行的强烈不满。
第二个语篇是Mark Twain去世后才公开发表的“战争祷告者”(“The War Prayer”)。这篇短文假借教堂布道的形式,谴责美国政府如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诉诸武力,打败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奋勇战斗了数十年的菲律宾军队,并推翻了新生的菲律宾共和国。Martin在分析该语篇时,再次把积极话语分析和名词化了的“spin”(“旋转”)即动作的名词化分析结合起来。Martin发现,该语篇和前一个语篇一样,都是先讲抽象的概念,然后逐步转向现实。
第三个语篇是Raymond Briggs撰写的儿童故事“外国的锡壶将军与年迈的铁女人”(“Tin-Pot Foreign General and the Old Iron Woman”),以隐喻的方式影射了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因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归属而爆发的那场战争。马丁告诉我们,这个语篇与上两个语篇有所不同,它不是从抽象走向现实,而是从虚幻突然走向现实。
在第二个方面,我们以马丁和Stenglin(2007)为例。在题为“实现和解:一次后殖民时期展览中的分歧协商”(“Materialising Reconciliation:Negotiating Difference in a Post-colonial Exhibition”)一文中,马丁应用了Halliday的功能思想,对位于惠灵顿的新西兰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一次跨殖民时代的展览会的空间安排进行了多模态分析。在概念意义层面上,他把展览的组成部分分成两大类:轨道式的(orbital)和顺序排列式的(serial),前者表达的是核心意义及其附属意义,后者表达的则是不分主次的若干组成部分如何组合成一个意义链。在人际意义层面上,马丁区分了两种类型:约束(binding)和结合(bonding),前者关心的是展厅的开放程度及其产生的舒适程度,后者关心的则是参观者对展览品的态度,影响参观者态度的有旗帜、会标、颜色等具有象征意义的会场布置。在语篇意义层面上,马丁借鉴了Kress和Leeuwen(2006)的观点,从展厅和展品所处的位置来判断整个展览会的“主位”(theme)和“述位”(rheme),从上下、左右等视角判断信息的新(new)与旧(given)。在这篇文章中,马丁向我们说明了一个道理:能表达意义的不只是语言,平面空间和立体空间也有意义,也有“语法”,关键是我们要学会如何在貌似随意、甚至杂乱的空间意义中寻找规律和特点。
在第三个方面,我们分别以马丁(2004a)和马丁(2004b)为例。
第一篇是“通过协商解决分歧:意识形态与和解”(“Negotiating Difference:Ideology and Reconciliation”)。在这篇文章中,马丁首先谈到20世纪70年代在澳大利亚发生的一次土著工人罢工以及由此引起的土地收复运动,希望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事件引发的不同声音和态度,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通过批评话语分析对白人霸权进行解构,还是在白人和土著人之间寻求和解。然后,马丁应用Halliday(1985/1994)有关“投射”(projection)的理论,从“引用”(quoting)和“转述”(reporting)两个角度,向我们展示如何在话语中传达土著人的声音。马丁要表明的是: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交际,白人依然掌握着话语的主动权,他们的声音始终是社会态度的主流,话语分析家们有责任让人们听到没有权势的土著人发出的各种声音,替他们说话,为他们写作,歌颂他们,从而帮助人们看到历史的真相。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已经有白人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但还远远不够,此外,土著人也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因而,目前这种话语交际还处于单向状态,不利于民族和解的实现。
第二篇是马丁1999年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宣读、2004年发表的“积极话语分析:团结与改革”(“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Solidarity and Change”)。马丁首先对批评话语分析过于关注语言与权力因素的关系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话语分析基本上是以解构的方式对待各种社会问题,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主张,语言学家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以建构的(constructive)方式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以便设计、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人类社会。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马丁第一次正式提出“积极话语分析”这个口号,并通过分析具体的语篇,如澳大利亚前总理Paul Keating和John Howard就澳大利亚历届政府强迫土著居民的子女脱离父母去遥远而陌生的白人家庭接受所谓良好教育一事发表的演讲,向我们展示了积极话语分析的含义和动机,以及积极话语分析的语料选择和分析方法。
2.2 学校教育中的意识形态分析
多年来,马丁对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所给予的关注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他身体力行,把他的思想贯彻到实际的学校教育事业中。这里仅以他对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关注为例。
2003年,马丁发表了题为“为‘他人’代言:阅读与描写澳大利亚土著人”(“Voicing the ‘other’:Reading and Writing Indigenous Australians”)。马丁告诉我们,如何倾听“他人”即以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为代表的非白人社团所发出的声音,以及这些人用土语或英语的口头或书面形式讲述过去和发表观点的方式和特点,从而看清历史真相,理解“他人”不幸的经历和心中的怨恨,最终实现不同民族之间的和解。
在“接触语类:对文化边界的理解”(“Encounters with Genre:Apprehending Cultural Frontiers”)(Martin & Rose in press)一文中,他向读者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澳大利亚这个多民族的国度里,土著人和非土著人之间在写作方面所接受的教育和训练不同,这是彼此之间缺少相互理解的重要原因之一。马丁分析了两类故事在语类结构上的差异,认为“假设类故事”(just-so stories)只适用于低年级小学生,而“梦想类故事”(dreaming stories)则应由土著人自己来讲述,并用作土著文化教学计划的组成部分。他还认为,应该把那些由土著人撰写的土著人传记和历史故事引入到写作课的教学中去,因为这样的语类涉及的话题不仅为土著儿童所熟悉,而且会引发所有儿童的兴趣。此外,马丁还建议把报道(reports)、解释(explanations)和议论(arguments)在内的书面语类也纳入教学计划,以帮助学生更多地从土著人的角度来了解土著文化以及全国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土著人社区的成员应该结合自己的文化背景给儿童开设土著语言课程,从而维护土著人的语言地位。
马丁不仅关心澳大利亚土著人在学校受教育的内容,而且关心教师授课所使用的语言。他(1990)在“语言与控制:用词语战斗”(“Language and Control:Fighting with Words”)一文中,对澳大利亚土著人双语学校中的写作课应该使用什么语言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发现,现在采用的转写法(transcription)只是把土著人口传的个人经历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字,因而失去了以平等的方式与白人交流的权利。他认为,土著人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方言写作,以保护已经受到严重威胁的土著文化;但他们也必须学会用英文写作,以达到与白人进行交流和协商的机会。这就是说,在双语社会中,不同的语言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如果土著人只会使用自己的母语,他们就会处于被他人控制的地位。双语学校有责任为土著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教育,帮助土著人掌握用不同语言实现不同社会功能的基本技能。
3. 结语
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学家如何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对系统功能语言学来说,是两个重要的课题。马丁所做的理论研究和具体的语篇分析起码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科学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这是科学发展的关键,但偏偏是我们的“短板”所在;二是语言学家需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问题,担负起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Cranny-Francis, A. & J. R. Martin. 1991. Contratextuality: the poetics of subversion [A]. In F. Christie (ed.).LiteracyinSocialProcesses:papersfromtheinauguralAustralianSystemicLinguisticsConference,heldatDeakinUniversity,January1990 [C]. Darwin: Centre for Studies in Language in Education, Northern Territory University: 286-344.
Halliday, M.A.K. 1978.LanguageasaSocialSemiotic[M]. London: Edward Arnold.
Halliday, M.A.K. 1985/1994.An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M]. London: Edward Arnold.
Kress, G. & Leeuwen, Theo van (2ndEdition). 2006.ReadingImages:TheGrammarofVisualDesign[M]. London: Routledge.
Martin, J.R. 1986. Grammaticalising ecology: the politics of baby seals and kangaroos [A]. In T Threadgold, E.A. Grosz, G. Kress & M.A.K. Halliday (eds.).Semiotics,Ideology,Language. Sydney: Sydney Association for Studies in Society and Culture (Sydney Studies in Society and Culture 3): 225-268.
Martin, J.R. 1990. Language and control: fighting with words [A]. In C. Walton & W. Eggington (eds.).Language:maintenance,powerandeducationinAustralianAboriginalcontexts[C]. Darwin, N.T.: Northern Territory University Press: 12-43.
Martin, J.R. 1992.EnglishText:SystemandStructure[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Martin, J.R. 1997a. Analysing genre: functional parameters [A]. In F. Christie & J.R. Martin (eds.).GenreandInstitutions:socialprocessesintheworkplaceandschool[C]. London: Cassell: 3-39.
Martin, J.R. 1997b. Register and genre: modelling social context in functional linguistics-narrative genres [A]. In E.R. Pedro (ed.).DiscourseAnalysis:ProceedingsofFirst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DiscourseAnalysis[C]. Lisbon: Colibri/Portuguese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305-344.
Martin, J.R. 1999. Modelling context: a crooked path of progress in contextual linguistics [A]. In M. Ghadessy (ed).TextandContextinFunctionalLinguistics[C]. Amsterdan/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Martin, J.R. 2000. Grammar meets genre—reflections on the ‘Sydney School’ [J]. InArts:thejournaloftheSydneyUniversityArtsAssociation(22): 47-95.
Martin, J.R. 2001. A context for genre: modelling social processes i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 In J. Devilliers & R. Stainton (eds.).CommunicationinLinguistics:papersinhonourofMichaelGregory[C]. Toronto: GREF (Theoria Series 10): 287-328.
Martin, J.R. 2002.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reconciliation and evaluation [A]. In C. Candlin (ed.).ResearchandPracticeinProfessionalDiscourse[C].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87-227.
Martin, J.R. 2003. Voicing the ‘other’: reading and writing Indigenous Australians [A]. In G. Weiss & R. Wodak (eds.).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theoryandinterdisciplinarity[C]. London: Palgrave: 199-219.
Martin, J.R. 2004a.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solidarity and change [J]. InRevistaCanariadeEstudiosIngleses. 49 (Special Issue on Discourse Analysis at Work: Recent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ractice): 179-200.
Martin, J.R. 2004b. Negotiating difference: ideology and reconciliation [A]. In M. Pütz, J.N. van Aertselaer & T.A. van Dijk (eds.).CommunicatingIdeologies:Language,DiscourseandSocialPractice[C]. Frankfurt: Peter Lang (Duisburg Papers on Research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85-177.

Martin, J.R. 2008. Innocence: realisation, instantiation and individuation in a Botswanan town [A]. In N. Knight & A. Mahboob (eds.).QuestioningLinguistics[C].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7-54.

Martin, J.R. 2010. Semantic variation: modelling system, text and affiliation in social semiosis [A]. In M. Bednarek & J.R. Martin (eds.).NewDiscourseonLanguage:functionalperspectivesonmultimodality,identityandaffiliation[C]. London: Continuum: 1-34.
Martin, J.R. (in press) Multimodal semiotics: theoretical challenges [A]. In S. Dreyfus, S. Hood & M. Stenglin (eds.).SemioticMargins:reclaimingmeaning. London: Continuum.
Martin, J.R. & P. White. 2005.TheLanguageofEvaluation:AppraisalinEnglish[M]. London: Palgrave.
Martin, J.R. & M. Stenglin 2007. Materialising reconciliation: negotiating difference in a post-colonial exhibition [A]. In T. Royce & W. Bowcher (eds.).NewDirectionsintheAnalysisofMultimodalDiscourse[C].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15-238.
Martin, J.R. & D. Rose. (in press). Encounters with genre: apprehending cultural frontiers [A]. In B. Baker, R. Gardner & I. Mushin (eds.).LanguageandIdentityinTraditionalCommunities(Festschrift for Michael Walsh) [C].
Zappavigna, M., Cleirigh, C., Dwyer, P. & J.R. Martin. 2009. Multimodal Coupling in Youth Justice Conferencing [A]. In M. Bednarek, & J. Martin (eds.).NewDiscourseonLanguage:functionalperspectivesonmultimodality,identityandaffiliation[C]. London: Continuum: 219-236.
王振华(主编).2010.马丁文集(2):语篇语义学[C].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