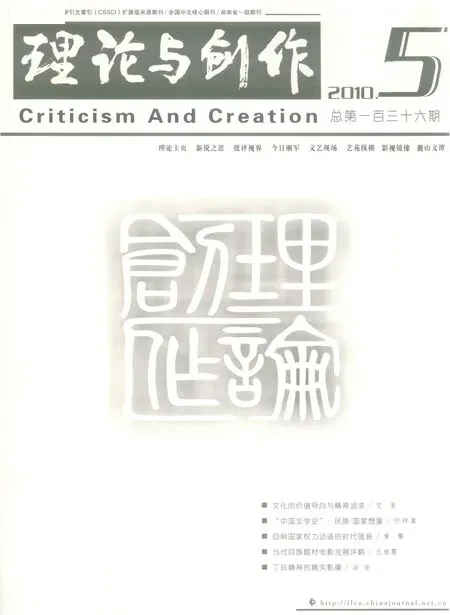文化的价值导向与精神追求
■艾斐
流变性和多样性是文化的天性,但正确的、积极的、先进的,具有时代精神、民族特点和社会担当的价值导向与精神追求,则是文化的生命线。只有当文化的天性服膺并融汇于文化的生命线之中的时候,文化才会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否则,流变性和多样性就会在内蕴上和效能上成为文化的悖论。
一
尽管文化的形态和作用是极其广泛的,但最高旨归和最深层次上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理念,则永远都是一种以思想、精神、道德、情操、信仰和追求为质点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并由此而外化为人们美好的社会愿景和高度的行为自觉。这也就是说,只有先进的文化,才能赋予人们以正确的思想、崇高的道德、远大的理想和丰赡的精神;而又只有在正确思想、崇高道德、远大理想和丰赡精神的支配和驭动下,才会使人们形成良好的社会期待和产生高度的文化自觉。这是一个链式的因果递进关系,其得以正常运转与不断前进的芯片和动力,始终都是正确的、积极的,具有时代风采、科学内涵和先进思想意蕴的价值导向与精神追求。
文化的价值导向,主要是指:文化以其科学的价值判断和先进的价值指向,在人和社会实现提升与发展中所具有和所发挥的正确而积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而文化的精神追求,则主要是指文化对先进思想、崇高道德、纯尚情操与懿美心愫的汲取和涵寓及其所产生的巨大而良好的社会效能。一切文化创造、文化形态、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不论其表现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方式、具有什么特点、追求什么目标,其在终极效能上都应当和必须具有这样的价值和作用。古往今来,凡是被历史钤印、社会肯定、大众认同、民族汲纳的文化产品与文艺作品,其在本质上就都是具有这个特点并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所以,《礼记·效特性》上说:“礼之所尊,尊其义也。”《韩非子·解老》中亦说:“事有礼而礼有文;礼者,义之文也。”这里所说的“义”,也就是对文章价值导向的强调与凸显。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才明确提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否则,只“陈其数”而“失其义”,那就写得再多,也不会有什么价值了。显然,“义”对于文化创造来说,既是价值导向,又是精神追求。这一为文的原则与圭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以极为强势的力量构建了中国的人文精神,塑造了中国的文明形象,并使从屈原到鲁迅的几千年中国文化始终都强烈地秉赋着以“义”为核心的精神魂魄与价值追求。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文化创造者们必须具有深刻挖掘和真切表现人与生活之本质,并能给予其以正确引导和有力驱动的使命感与责任心。无独有偶,遥处于地球对面的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在1950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感言中,也说出了与此极为相似的话。他指出:“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诗人不应该单纯地撰写人的生命的编年史,他的作品应该成为支持人、帮助他巍然挺立并取得胜利的基石和支柱。”①
这种对于文化之特点、本质、效能及其与社会和人生之关系的见解,虽然跨越了旷远的时空,但却仍能取得高度的吻合,以至完全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与睽隔。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文化的价值内涵和价值标准既然是人类社会所共同勘定和一致尊崇的,那么,它就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文化创造者们的共有原则、共同理想和共性追求,成为一切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的准则、任务和使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尤应如此。
这既是文化的前置性动力,又是文化的结论性标识。任何有价值的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都应当、必然和必须在这个前置与结论之间进行个性化的创造性活动。从前置到结论,这不但是一个极其广阔的社会和文化空间,而且更是一个充满生力与魅力的思想空间和美学空间。所以,它完全可以给大容量和高品位的文化创造与文艺创作提供最为丰富的养料和极其优渥的条件,以其特有的精神内蕴与美学资源促使文化精品的莅世和文艺宏构的产生。其实,任何文化精品和文艺佳构的产生,就都是发生和发展于这一特定的思想空间与美学空间之中的。之所以如此,惟因这个空间从来就是以正确而积极的价值标准与价值追求作为矩范和动力的。一旦有了这个前提条件,任凭作者纵横捭阖、恣肆挥洒、率性驭笔,也都是可以做到“不逾矩”和“皆创新”的,一如马克思和鲁迅那样,不论他写什么和怎样写,都会是佳品迭出、价值倍增,始终流溢着思想的新潮与闪耀着艺术的光彩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前十七年,尽管被认为是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而一定程度地限制了作家的创造性和作品的多样性,但那一时期所出现的《红岩》、《创业史》、《保卫延安》、《山乡巨变》、《红旗谱》、《三家巷》、《苦菜花》、《白洋淀》、《上海的早晨》、《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长篇小说,不仅题材广阔、内容多样、形式新颖、风格独特,而且皆以其思想的敦厚和艺术的娴稔而成为文学的楷模与丰碑,以至深刻地影响、改变和提升了几代人的心灵世界与精神架构,迄今仍旧葆有着强大艺术生命力。何以然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具有正确、积极而先进的价值导向与精神追求,作家在创作中所投诸和所凝积的不仅是思想的火光与艺术的匠心,而且更是对时代的感应,对社会的担当,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神圣使命感与崇高责任心,而绝不是对主体利益的钩稽和与商业、欲望、消费、金钱的紧张。
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来说,这不啻是一种可贵的提醒与有益的启示。
二
社会是发展的,时代是进步的,人以及人的思想内蕴、精神诉求和生活方式等,也都是在不断的流转和变革中寻求着新的突破和实现着新的提升的。于此情况下,文化自然也应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绎和流转。这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和必须的,更何况实现创新从来就是文化的永恒主题与生命弦歌。在任何时候,变革和创新都是文化获得激情与诗意、实现发展与提升的有效方式和必经路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凡“变”必升、凡“新”必优,关键还在于变什么?如何变?究竟“创”在哪里?“新”在何处?因为只有在因“变”而达优、因“新”而臻美的情况下,“变”和“新”才会具有创新价值和发挥积极作用,也才真正是本质意义上的变革与创新。
绵亘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基本上是沿着朴素唯物主义、社会人文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路径走下来的。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主义”并不算多,但变革和创新却不算少。否则,就不会形成如此灿烂的中华文明,就不会积攒浩如烟海的8万件文化典籍和出现辉映星汉的千百个文化巨子,当然也就不会使中华民族从“轴心时代”开始便一直处于世界文化的巅峰。相比较而言,新时期文化虽然只有短短30年,但却“主义”多多,“旗帜”多多,“谱系”多多,“名号”多多,唯独没有出现可以与《红楼梦》相熠的作品,或可以同鲁迅并世的作家,即使单以作家族群及其代表性作品所处的文化地位与社会影响而言,也是很难与前十七年那一批作家和作品齐埒比并的。这个不争的事实,乃是足以让我们从浮躁、虚骛和自炫自诩的陶醉中清醒过来、沉静下来,并认真进行一番清理与思考的。只有真正找出原因,特别是找出根本性的原因,才能自觉而有效地抻曲矫枉、砺锋拨翳,把事情的真相和原委看得更明白一些,也才能在清明的人文环境和忱智的文化心态中从容而自信地创造未来,实现愿景。
显然,对于现在兴时行世的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来说,并不是主体缺乏才华,缺乏知识,缺乏技能,缺乏对精神创造和艺术创新的激情、向往与追求,更不是客观上不具备酿成足以立世、铭世、传世、熠世之文化巨人与文艺杰作的环境、条件与资源,而在许多时候和许多情况下,所缺乏的恰恰是科学、正确、积极、先进的价值导向与精神追求。当然,这种缺少并不是时代、社会和生活造成的,而主要还是文化主体在创作思想与创作实践中,对正确、先进的价值导向和精神追求的自觉不自觉地排斥、放逐以至消解所造成的。比如,在以私人话语和个体经验为主要依托的创作中,对公共价值的稀释;在通过嚣攘隐私的裸露和欲望的舒张而凸显自足自恋心理冀求的过程中,对大众情怀的闭锁;在沉溺于琐屑、偶在乃至低俗的时尚刺激与小资情调时,对崇高与正义的悖逆;在着意表现“本能化”、“生理化”、“感官化”、“欲望化”的过程中,对伦常世理的否抑;在所谓纯“娱乐”、大“恶搞”、土“调侃”、洋“戏谑”的颠覆性和淆乱型叙事中,对良知和理性的撕裂;在曲意改变向度、刻意寻觅卖点、纯乎追求享乐、极度崇尚消费的所谓“时尚化”和“私人化”行文中,对文化道义与社会良知的销铄等。
所有这些现象,都程度不同地在文化层面上表现了对价值导向和精神追求的放逐与亏缺。因为一切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在本质上就都是一种趋新、求真、弘善、臻美的精神创造与思想引导,就都是一种对良知和道德的救赎、升华与强化。所以,在其创造机制和社会功能中,一旦被生理化取代了社会性、娱乐化屏蔽了义理性、利欲化腌渍了功德性、恣意化支配了规约性、附庸化替代了先导性、低俗化消解了崇高性,那它就必定会在失去本体价值的同时也失去其本应具有的社会意义与审美功能。其结果,就像马克思所断言的那样,精神产品及其创造者们一旦将高筑于民族利益和人民立场之上的崇高、正义、公理、奉献等观念、情感和追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②的时候,那它就必然会在形态、性质和功能上变为文化的块垒与精神的疣物,其价值和意义的畸变与消解自当在所难免。
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显然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流转期,这不仅得益于宽松的政治环境,而且也得益于良好的社会条件。文化观念、文化形态、文化理论、文化方法、文化结构、文化范式、文化语境、文化元素,乃至文化的表达套路和实现方略等,都在大范畴和深层次上发生了变革和进行了创新,遂使整个文化面貌焕然一新。这无疑是值得肯定和庆幸的。但也正是在这种由快速流转和样象纷繁所造成的热闹景象中,却往往耗散和淡化了对价值导向的循守与依托,对精神追求的热忱与执着,并由此而造成了一些文化产品的思想虚脱与精神贫乏。这一点,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尽管“新锐”、“前卫”、“新写实”、“后现代”之类的口号和旗帜层出不穷,但却鲜有绚能熠世、力可扛鼎的作品出现;尽管“奇幻”、“悬疑”、“侦探”、“盗墓”、“穿越”、“耽美”之类的名目和称谓让人目不暇接,但却越来越使受众对文学的热情与眷顾趋于冷淡和消敛;尽管现在每年的长篇小说出版量都在2000部左右,随便一个年份的作品产量都可大大超过前十七年的文学出版总量,但其所葆有的艺术感召力和社会影响力却越来越萎缩、越式微,就连获得矛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也难得让人悉数记住和叫出它们的名字。这与前十七年进入读者视野的长篇小说相比,确实大相径庭。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永远都在于作品本身。而就作品本身而言,关键又在于文学的生活底子虚了,目标追求变了;真情实感少了,主体欲望多了;思想内蕴小了,外部形体大了;艺术功力差了,私语雕痕多了;责任意识弱了,自恋心理重了;“大我”、“主潮”淡了,俗情琐务浓了;人民大众远了,审美眼光短了;时代精神稀了,“自我表现”强了。凡此种种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价值导向和精神追求的异质与缺位。而价值导向和精神追求的异质与缺位,则又足以使作品失去思想光彩和艺术魅力,以至于难以发挥它本应发挥的积极作用,正如歌德所说:“一个时代如果伟大,它就必然走前进上升的路,第一流以下的作品就不会起什么作用。”③
对于伟大的时代变革和社会发展不起什么作用的文化产品与文艺作品,自然是不会赋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了,当然,也就自然不会得到大众的接受和社会的认同。这,绝不是我们所要的结果。
伟大的时代,应当产生伟大的作品,也最有条件和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关键就在于创作主体写什么和怎样写。而写什么和怎样写所检测和考验的不仅是作家的智能、技巧和才情,而且更是作家的眼光、胸怀和见识,当这一切都在时代精神与生活资质的调动下逐渐聚焦于价值导向和精神追求这一质点与亮点上的时候,创作也就必然和自然会进入最佳境界,并有望精品与宏构的熠然问世。这并不是梦想,而是充满热切期望的预言。因为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一旦回到正确、积极、先进、丰赡的价值导向与精神追求的驭动之下,它就自会焕发旺盛的生力和结出丰硕的果实。
如果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心灵和大脑,那么,正确、积极、先进、丰赡的价值导向和精神追求,则就是最能赋予这心灵和大脑以强大搏动力和旺盛创造力的血脉与经络,并由此而为文化筑起永具活力与魅力的生命线和价值链。
注 释
①赵永穆译:《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5页。
③《歌德谈话录》,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