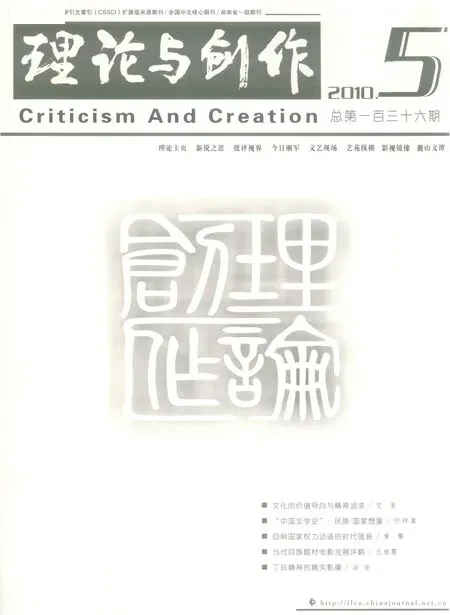《空城》的奥秘:都市女性形象背后的男性意识
■向荣 王宁
《空城》是成都作家春绿子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春绿子以一颗对女性的悲悯之心,用文字直抵城市女性的内心深处,探讨了在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都市各阶层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在对当代男权文化进行解构的同时践行一种不无痛楚的女性探索。尽管对女性的想象不无浪漫主义的成分,但作者却能在对生活世界的情感体验和内心经验中,从叙事上守护着对于女性的道德认同和命运关怀。
传统的文学作品,由于深受男性逻各斯中心思想的束缚,在描述女性时,总是从男女两性的关系着手,从男性的角度来写女性,两性之间的关系通常呈现为二元等级的对立状态,使男女在社会生活中分属两大不同的阵营:社会性的男人和家庭性的女人,并由此导致了两极分化的男女情感对立,表现为一系列的子等级的二元关系:比如智力和美貌、逻辑和直觉、现实和幻想、文化和自然等等,突出强调其两性之间的等级差别,前者通常要优越于后者。而《空城》则是站在反男权文化的伦理角度,通过两性之间在道德上的二元关系,来突出男女两性在道德上的等级差异,也就是让城市女性获得一种人格上的道德优势,而那些拥有各类社会权力的男人,总是有或大或小的道德瑕疵,这些道德瑕疵又总是同社会权力的腐化现象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如此一来,《空城》的审美意识里便蕴含着对男权文化等级关系的颠覆意识。
作者在小说的封面写到:“《空城》是一部关注女性生态的小说,一部透视社会心态的小说。”小说中充斥着男男女女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而这些人物之间或多或少都有些关系。比如尹老三与严芳、毕慧,严芳与张楚云,谢芹与曾宪、李南,苏明与李马华,杨玉琼与袁少辉等等。他们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尽管如此,小说中所有的男女两性关系,实际上都被暗置在一种权力关系之中。男人自始至终都是掌握权力的一方,他们的社会职务或文化身份表明他们是社会的“权力者”,而女人无论是中产女人或是底层女性,在权力场域中,她们都是弱势者,她们没有什么权力。如果说有,那也只有依附或屈从于“权力者”的惟一“权力”。这就说明,小说对当下城市女性命运的观照和描述依然是放置在一个男权社会的历史语境中,是从“社会心态”(即男权文化)的后面去关注“女性生态”的。这样的叙事方式和文化语境的设置,从而也使小说讲述的女性故事更多了一些普遍性的意义。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她们多多少少带有我们这个消费时代的文化特征。如女主人公苏明,有着茅盾笔下的梅女士、慧女士那类都市知识女性的影子,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还有聪明、智慧和良好的学识,对于周遭的社会现实感到压抑和不满,最后借助宗教信仰的力量提升自己,使自己超越情感困惑和世俗利益的纠缠。也有处于都市社会底层的普通市民,如谢芹、毕慧、杨玉琼等,她们拥有的是作为传统女性所具备的道德与品质,善良而又软弱,但在面临人生或情感抉择的时候,她们用行动证实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实现了精神上、人格上的超越和提升。当然,茅盾笔下的进步女性除了情感生活外更关注革命运动,而春绿子笔下的女性生存在日常化的世界中,作者就主要是在感情领域中通过男女关系透视这类女性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经验。在这些女性形象塑造中,作者肯定了女性把握自我命运的现代品格,表达了对女性主体性的尊重。不但赋予她们自强勤劳的女性品质,而且最后还赋予她们独立于男性意志之外的女性主体性。在两性互相审视时,他也总让这类女性独占道德优势和人格强势,她们虽然是现实中的弱势群体,但她们总以柔弱的坚强和温软的情怀成为那些强势男人心中的依托对象。作者以赞赏的态度塑造这些女性,让她们在叙事中占据中心位置,这不仅体现了作家对男性意识的超越和对男性中心思维的突破,还表达了作者关注女性的理想主义情怀。
作家对苏明、谢芹这类都市女性主体性的高扬,是在小说所描写的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上对女性的细心体察和理解,但同时也寄寓他自身多重的心理需求。这些心理需求,既有男性对女性的欲望,也有男性把自我人格的一个侧面转化成女性形象之后进行书写的艺术冲动。这些不同的女性形象,实则是作家内心女性视角与男性视角相叠加的艺术结果。
《空城》中的女主人公苏明是一位年轻的富商,既是市园林局处长李马华的情妇,又是市宗教局处长郑云生的女友。她相貌美、受过良好的教育且是青山绿水园林公司的经理。男人的眼睛到她那都成了扫描仪,在她身上做着全方位的扫描。每到一处,她就立即成了中心,所有的人对她的赞美中都会带有曲意逢迎的意味。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尤物”优势,在这个物欲纵流、权力至上的消费主义社会,苏明作为一女年轻开发商为了得到城北公园那项工程,为了商场上的利害得失,却始终受处在权力之上的园林局处长李马华的制约,成为他泄欲的对象,成了他的情妇。在如此屈辱不甘的情形下,为了找寻心灵上的解脱,她只能每天晚上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书写自己的心情,反复咀嚼自己写下的文字,只有这样她才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市井,远离了一切肮脏。她习惯了在每一个夜晚,在与那个网名叫“流水天涯”的一次次交流中,感受另一个真实的自我。每晚在虚空里相会,象一束淌在黑夜里的清泉,永远没有目的,没有方向,甚至没有逻辑。就像小说中所提到的“她把这小屋当作是自己最后的领地,她不会让任何人踏进半步。走出这套小屋,她就是另一个人,一个在市井里应接交际的女人,一个浑身裹满红尘的女人”。苏明试图在《庄子》中找到自我,当坐在梳妆台前,面对镜子中的自己,感觉恰是庄周化蝶的意味。她想跨出小屋里的那道门,那就是另一个女人了。“她早就觉得,这世上有两个我,一个是永远封闭在这房里的我,一个是在市井里苦苦厮混、游刃于红尘中的我。只是不知道哪个我更接近真实。”
或许是命运使然,苏明遇到了重江湖义气的况二哥。在这里,况二哥从最初的欲望对象,到对她人格的敬佩,最终把她当亲妹妹一样对待。也正是因为况二哥,才使得苏明终于摆脱了李马华的束缚。这个腐败官员在后来被况二哥开车一直追,结果栽进了鱼塘。生命的最后时刻,竟是跟一个摔烂了的坏鸭蛋在一起。也许这也正应了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如此恶报,竟打上了黑道的烙印。一种深刻的现实反讽就有些意味深长了。好在况二哥黑色的行侠仗义最终也受到苏明的道德感召,去公安局自首。而苏明得知李马华出事后,她的困惑包围了她,她只得走出了那套小屋,驾车出城。当看到“高木寺”三个字时,眼前的一切景象似都与梦中相合。苏明心里一片空茫,似乎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更不知道是不是又在另一场梦里。就在这里他遇到了郑云生,郑云生对宗教伦理的认识与对现世的领悟,又逐渐成了苏明感情上的寄托。且看下面郑云生所述:“一种必须超越精神文化和宗教伦理的力量,必须突破上帝和佛所到达的高度。我们知道,佛主张向内看,因为向内看会使我们开悟,但是我们却长了一双始终向外看的眼睛。这双永远向外看的眼睛,使我们看到的总是物质,我们便会产生求取的冲动。佛在这里遇到的难题是无法破解的。除非有一种力量能彻底还原物的本质,而不是佛所说的一切皆是幻象,我们可能会放弃追逐物质的冲动。或者改变我们的生理形态,让这双始终向外的眼睛反转过来。所以,那种力量必须是超时空的,或者超自然的。”
是的,或许还要借助郑云生所说的“需要一种必须超越精神文化和宗教伦理的力量,必须突破上帝和佛所到达的高度的力量”。苏明才能从空蒙的细雨中走出迷津,找到真正的自我。很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彰显女性独立个性、肯定女性主体性的同时,也在他的创造物身上投射了男性主体对女性的愿望。郑云生的超越性宏论,看上去总像是作者在为他偏爱和同情的苏明指点人生迷津,描绘人生愿望。这些愿望可能会符合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体现了他在平等意义上对女性的期待。但也有可能并不符合女性作为人的生命逻辑,仅仅承载着他对异性的心理需求。如果后一类愿望过分强大,就可能对现实中的女性生命形成心理压抑,尤其在男性话语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在女性外貌气质的描述上,就充分表露了男性对女性外表形象的期待,这些期待或关涉男性的精神需求,或关涉男性的本能欲望。像茅盾笔下一系列性感魅力的进步女性,它们代表着作家男性立场对女性人物世界的制约。在现代男性叙事文本中,进步女性仍需在外貌上获得男性心理需求的美感。这种美感即使溢出了某一男性人物的心理需求之外,也不能溢出男性作者对女性的心理需求。当女人们身处精神困境甚至走投无路时,关键时刻,总是有一个飘然似仙的男人站出来,为她们引领方向,指点迷津。《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对于林道静来说,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引领者”。《空城》的叙事仍不例外。由此可见,男权文化的惯习是多么的强大。它好象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在《空城》中的审美表征。所以反男权的《空城》,最终也还是在男权的岸边沾湿了裤脚。
《空城》中的其他女主人公,如谢芹、毕慧、杨玉琼等,他们虽没有像苏明那样处于社会的上层,但作为社会中下层中的普通百姓,他们身上展示的却是传统女性所具有的品质。然而,她们每个人在面对情欲时,终究也是男性欲望的对象物,只不过她们各自又有区别。如谢芹与市教育局处长曾宪。曾宪早就被她的的身材与美貌所吸引。谢芹是茶室女招待员,凭借曾宪的关系,她完全可以换个环境换个工作,但她并没有。尤其是在曾宪出事后,谢芹把他留给她的全部财产捐给了灾区。在物质、金钱利益面前,她把握住了自我。她对曾宪的感情可以说,完全是来自于自己的房客李南。李南作为男人,这个无权的打工者是《空城》中惟一的“好男人”,是整章小说中作者预设的最完整的男性形象。在小说的叙述上,作者却把他设置成了缺席的不在场。这不啻又是一个反讽,抑或是作者精妙的修辞策略——好男人即便有,他也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的“影子”,他总是以缺席的方式存在。而谢芹对李南一往情深,说到底也就是对一个“影子”的虚幻感情,于是她就把对李南的感情就无奈地放在了曾宪身上。这个缺席的不在场与小说中的其他男性人物,不仅仅是曾宪,还有尹老三、李马华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在道德品质上。从这一点上看,作者虽站在男性立场上书写男性罪恶、腐败、阴险的形象,但还是对男性形象的批判有所保留,对理想的男人有所期待。
毕慧、杨玉琼一个是茶室女招待员、茶室老板尹老三的情妇,一个是肥肠店老板的情妇,这两个人可以说也是男性欲望的对象物。她们吸引男性之处在于其外貌、老实、稳重的个性,这两个女性在这里就成了他们情欲上、心理上的需求品。这些都是自己的现任妻子所不具备的:茶室老板的妻子能做到的只是两人不停的吵架,打骂。但在小说里作者也并不完全否定这个形象,茶室老板的妻子是个好母亲,尤其是在儿子被绑架时,她的那种着急,是母亲对儿子爱的母性力量的展现。肥肠店老板的妻子张燕,每天从早到晚要做的只是一再的输钱赢钱打麻将,在面对杨玉琼时,她说话、做事是那么的干脆利落,展现出的是一幅毫不在乎的样子,杨玉琼直接就成了“老板娘”。然而,作为别人的情妇也只是暂时的。当大地震来临时,似乎所有的人在被世俗、阴暗遮蔽之后终于清醒了,终于意识到生命的价值、道德感随之萌发。作者塑造的这些底层女性形象,其情感结局是与处在中层的苏明相一致的,她们最后都寻找到了真正的、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寄托。
按照女性主义理论,男性作家在女性人物的美貌与性感上并不仅仅投射了男性对异性的欲望。其实,女性人物明艳的躯体、旺盛的生命力中所流溢出的生命活力,亦熔铸着男性对自我生命的期待。其实,何止是男性叙事对女性身体美的描述,即便是男性叙事对女性性格的描述,也同样倾注着男作家自我的人格倾向、心理需求。男性叙事中自主型女性的阳刚气度和生命激情,显然凝聚了男性作家对这种气度的渴望和呼唤。把男性自我人格的某一侧面易身为女性面目,使之超越现实限制而得到淋漓尽致的抒写,是男性叙事中常见的现象,也是男性作家借助女性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人格倾向、心理需求的结果。
作者春绿子十分强调都市女性身上的道德感和生命强力,这也是他一直赞扬的底层群体身上的闪光点,同时也是都市世界和都市男子所缺乏的。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他对种种都市病象开出的治疗药方:为都市注入市井之气、民俗之风和淳朴的自然气息,以对抗都市人生命的衰竭和生存的虚伪矫饰。那些都市女性的向往和期冀,隐藏着作者对都市男子强健生命力、对道德感的召唤。与其说是在盛赞她们,不如说是为了主题的需要而造了一面镜子,用女性的“道德强势”来衬托都市男性的精神衰竭。
综上所述,春绿子笔下的女性形象各有千秋,其形象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也能给予人们积极的启示。“她们”以自己在男人眼中不寻常的操行塑造着灵魂,揭示着人生的真谛。马克思曾说过:“每一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会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第571页)可以说,作家春绿子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艰难的创作道路上严肃、公正、客观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现实,并努力探索着以较高的艺术水准去表现女性身上那种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格力量。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