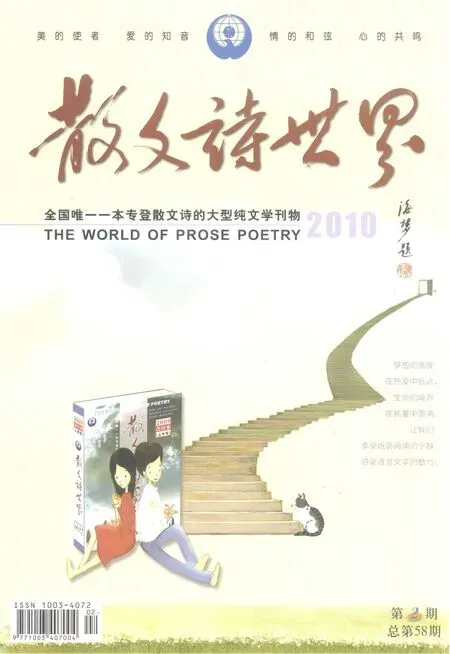城市边缘(九章)
安徽 崔国发
飙
飙:三只猛犬在这个字的偏旁上狂奔。
风,在它们的后面,怎么追不上呢?
风驰电掣的加速度,振翅疾飞的鸟,在天空上飙,不可企及的凯旋。
飙:三道亮刃,一闪而过,在暗黑的苍穹中,霍然露出洁白的牙齿。
呼啸的声音,急骤飘来,令人心惊胆颤的踪影。
倏然奔窜的狐鼠,在目不暇接的快速中,夺路而逃。
飙车的飙。飙歌城的飙。狂飙突进的飙。
一路飙升:涨价热。房地产热。股市热。收藏热。购车热。高校招生热。
甲型H1N1流感也热起来了。
飙:扬尘。沙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
一阵风吹过。三只猛犬在这个字的偏旁上,飙着,飙着,它们要“飙”到何时呢?
“来 了”
破云而出,横空出世,我听见一出戏里的台词: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
小时候,大人们给我讲过去的事情,还记得那一则寓言:狼来了。
没想到,“狼”真的来了:冰冻灾害、汶川大地震、手足口病、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
轻轻地,请它们走吧。可它们,又轻轻地来了:酸雨。毒雾。蓝藻。海洋赤潮。
嗨,赶都赶不走。
仿佛是在梦中:天天天蓝,日日日新,清粼粼的水,从我们的身边,流着,流着,绿色的命脉。
那时,我会情不自禁地呐喊:还我温暖的阳光,还我洁净的空气,还我清澈的河水!哦,来了,它们都来了!
防震演练
只那么一瞬,我们就要从这栋楼里冲出去!
警报响起。一阵阵揪心的警笛,如一声声惊雷,在我们的耳廓,发出生命的呼唤。
危机四伏,险象环生,震情就是命令,快!快撤出去,在最短的时间内,腾身跃起,穿越回廊,冲下楼梯,突破钢铁的重围。
快!走向生命的绿地,我们别无选择,一直走吧,前面就是出口!
警笛还在响着,深入神髓。绝大多数人,潮水般地从大楼里涌出。
因为是演练,也有一些人慢慢悠悠,边说边笑。狼如果真的来了,他们说:“不怕,我倒要凑上去看看,是公的还是母的!”
哪怕是坐在火山口上,他们还是这样说,有什么法子呢?
这时,我想起法国诗坛怪杰米修《在灾难中歇息》的一句话:灾难中歇息,我是你的废墟。
旧书摊
夜已降临。在喧嚣的露天市场,老王的旧书摊,被安置在半透明的边缘。
多少年了都这样,打开一只只蛇皮袋,在昏黄的路灯下,铺设旧时的月色。
挤挤挨挨的书卷,被过往的眼镜翻阅,亘古的萤光。
三个穿深蓝色制服的人,悄然来到这里,扫黄打非。
他们的眼睛,像360安全卫士扫描电脑病毒一样,环视了几圈书摊。
“跟我们走一趟吧。”
因为在一本旧杂志的封面上,刊登着这样几行文字:
六旬老翁猝死鸡窝里成了风流鬼。
著名卖淫女摇身一变为民企大老板。
某二奶席卷大款的钱财跑了。
“这样的书,你能卖吗?还有这本《包法利夫人》,包法利的夫人,你也能随便包吗?”
无可争辩,也无可逃脱,还是缴上罚款吧。
他又回到自己的书摊前,在街灯洒下的微光中,仔细打量着,大江健三郎作品集《性的人》。是的,《性的人》,不知道能不能卖?
空荡荡的夜。老王的心,颤巍巍的……
宠物狗与乞丐
宠物狗不说话,它坐在宴席上,主人专门给它点了一道菜:糖醋排骨。
主人酒兴正浓,小狗胃口大开。
宠物伸出油腻腻的长舌,并且投去一个媚眼。主人心领神会,它要喝葡萄酒,
它要在主人的倾倒中,一醉方休。
金碧辉煌的餐厅,充满着欢声,笑语,柔情。
灯红酒绿。宠物狗被主人搂在怀里,毛茸茸的,撒娇、拥抱与接吻。
吃过水果后,走出餐馆大门,宠物真的醉了,它呕吐得一塌糊涂。
“老公,家里是否有健胃消食片?”
这时,门口一个乞丐,一个蓬头垢面,清癯瘦削的乞丐,落魄的流浪汉,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他声音微弱地说:“好人哪,给点吧!”
伸出的瓷缸,却被狗的主人打落在地。
“没有硬币,请你走开!”乞丐得到了一阵斥喝,白眼,鄙夷。还有,黑色的轿车屁股里,喷出的一溜难闻的尾气。
公园一瞥
公园的一隅:那么多的青藤,在石砌的斜面上,垂挂。
绿阴纷披,在明媚的阳光下,飘拂着,柔枝的婀娜。
一朵,又一朵,淡黄色的花儿,星星似的黄花,在带露的翠叶上,散发着,一簇簇的清馨。
摘一朵给她,一只白色的蛱蝶,点缀,在香蕊上签署完一份春天的文件之后,便翩然飞走了。
这时,不妨请你认识的女人过来,告诉她你内心的秘密与空虚。
穿花裙子的女子,可能就是世间最美的花朵。
她不会搔首弄姿,她不会像羞赧的桃花一再地躲闪,她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把你搞得心事重重。
她应该感激你对她的尊重,毕竟你没有像那些沾花惹草的蜂蝶,比如说,在这公园的阴暗角落里,不是也有一对对情侣冲动得一塌糊涂么?
“你看,你看,他们怎么能够那样?”一位散步的老者走过来说。
偷吃禁果?
咳!都啥年代了,为什么要让自己敏感的心,在爱情中承受太多的痛苦?
法国诗人米修说,鸟的狂热激不起树的兴趣。
那是写诗!可是我不相信,真的,我不相信!
街巷,流动的馄饨摊
站在街巷边上,她下岗已经多年了,馄饨摊一摆,也已多年。
风中劳作的少妇,守着破旧的摊子。
过往的常客,有时也过来坐坐,忽然发现:
她那憔悴的样子,人渐渐地瘦了许多。
雨珠在帐篷上敲打着,一声声的话语,念叨
被矿难夺走的丈夫。
就在一个月前,她的丈夫还在晚间如约地来到她的身边,用平板车拉回馄饨摊。可是现在……
雨越下越大了,妇人推着板车上坡,在茫茫的雨夜中爬行,摇晃,踉跄。
心,仿佛已被车轮的压力碾碎。
回到城市的喧嚣中,她又用馄饨,多次地喂养着,她那年幼的儿子。
注定此生,沉浸在这样的爱中:
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出现命运的转折?
棚户区的雨
棚户区的雨,在青灰色的瓦砾上,泛滥成料峭的春寒。
雨什么时候停呢?
漏雨的平房,住了三十多年的简朴平房,失修的墙面,布满了斑斑点点的泪痕。雨急的时候,谁家的屋檐下,燕子竟无处藏身。
蝙蝠的翅膀,被雨打湿的翅膀,背不动,岁月的遗照。
棚户区的雨,在青灰色的瓦砾上,流不尽,青色的泪。
躺在窝铺上的居民,只是在媒体上被誉为“城市拓荒者”的居民,在昏黄的灯火中,曾经和正在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现代化的奇迹,却不能改变在阴冷、潮湿、逼仄中生存的自己:
被富人区的摩天大楼俯视成一只只工蚂蚁。
“棚户区在哪里?”从浙江来的房地产开发商,兴致勃勃地问道。
这时的雨,还在 地下。
报纸的头版头条:“本市棚户区改造工程已拉开序幕!”
闪闪烁烁,闪闪烁烁的。
不知道,是棚户区的雨?还是棚户区人喜不自禁的泪花?
秋天的拾荒者
又是一天的尘埃落定。纵横交错的蜘蛛网,已结满了屋顶。
只是屁股大的一块地方,只是一间用破旧的油毡和石棉瓦搭盖的小屋。
一个人的夜晚,在深秋蟋蟀的低吟中,应和着沉睡的鼾声。
城郊的毛毛狗,叫得更厉害了。
天色熹微。苦命的拾荒者,穿街走巷,在一贫如洗的阳光下,费尽了口舌:
收破烂 ——收破烂 ——
轻寒的吆喝声,在嗓子眼里,都冒出火来了。
躬着腰背,灰乎乎的鼻眼,满身土气,满身汗馊味。硬撑着虚弱的病体,在废品收购站,从那一条条老旧的蛇壳皮袋中,掏出嘈杂而零乱的东西:烂纸盒、旧报纸、废弃的书刊、矿泉水瓶子、牙膏皮……
拆装、打捆、过磅、算账。只是那双皲裂的手指,还显得麻利。
街面上,他经常和人打招呼:有报纸卖么?有时,又被小区保安劈头盖脸地呵斥一顿。
临近暮晚,回到住处,脱下那身脏衣服,总是背对着家的方向,倒一杯劣质的浊酒,灌醉全身心的疲惫,在那盏十五瓦的灯泡下,把龙虾壳嚼得咯嘣嘣的响。
一种自制的药丸:在民间草本的煎熬中,散发出野生的苦味。几声轻咳,哦,苦命的拾荒者,漂泊的拾荒者,挤在城市的边缘,不知道明日,明日复明日的风,究竟往哪个方向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