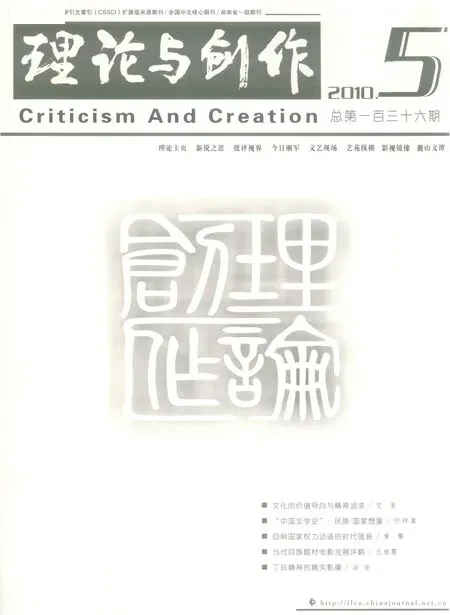1940年代知识分子的“建国”想象——以西南联大诗人群为中心
■ 赵丽苗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改革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文学唤醒民众,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一直以来都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内在的目标。近代中国的处境使得作家们不管怎样追求艺术上的完美,也始终摆脱不了家国身世的感怀,以致有评论家用“感时忧愤”或“民族寓言”来描述整个现当代文学的特点。
文学史上的1940年代通常是指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那是一个溢出常轨的时代,较之此前,中国的民族危机更为严重,国破家亡、流离失所,成为那时大部分人的普遍境遇。秉承入世传统的作家们有弃笔从戎,直接投身前线的,也有以文字为宣传工具,为抗战摇旗呐喊的。文学无可避免地渗入了战争的因素:“战争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写作心理、姿态、方式以及题材、风格。即使是某些远离战争现实的创作,也会不自觉地打上战时的烙印。”①具有学院派背景的联大师生们虽然在政治气候变化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注重学术的研究和学习”,不像后来的“整天谈政治、谈时事”②,但他们并没有躲在大后方的书斋里,有意隔绝于时代政治,而是立足于学理层面,对文学与抗战的关系做出了长远性的思考;在力图与世界文学同步发展、进行新诗“现代化”探索的同时,也通过诗歌寄予了他们的国家想象。
一、体验祖国的“山山水水”
“抗战的烽火,迫使着作家在这一新的形势下,接近了现实:突进了崭新的战斗生活,望见了比过去一切更为广阔的,真切的远景。作家不再拘束于自己的狭小的天地里,不再从窗子里窥望蓝天和白云,而是从他们的书房,亭子间,沙龙,咖啡店中解放出来,走向了战斗的原野,走向了人民所在的场所;而是从他们生活习惯的都市,走向了农村城镇;而是从租界,走向了内地……”③
“战争给了许多人一种有关生活的教育,走了许多路,过了许多桥,睡了许多床,此外还必然吃了许多想象不到的苦头。然而真正具有教育意义的,说不定倒是明白许多地方各有各的天气,天气不同还多少影响到一点人事。”④
这两段文字形象地描述了战争对作家们生活的影响。尽管身份不同,知识结构各异,罗荪和沈从文却不约而同道出了自己在战争中的两点最重要的体验:一是走过了很多以前没有到过的地方,接触了更为广阔的现实;二是与普通民众有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接触,懂得了更多的人事。这大概是战争中很多知识分子的共同体验,西南联大的师生也不例外。
虽然处于相对平静的校园环境中,但在“警报的笛子到处叫起”、硝烟味弥漫不散、生命时时受到威胁的严酷环境下,书桌再也不能如往常一般平静。原本单纯的书斋生活,无可避免地会被战争的相关经验,如动荡、奔波、残酷等所侵蚀。在敌人战火的逼迫下,联大师生们的生活中起码增添了三项平时难以体验到的内容:长途迁徙、跑警报和参军。作为整体的联大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迁校:一次是从北方迁往长沙,一次是从长沙迁往昆明。此后还有文学院的在蒙自与昆明之间的搬迁,以及后期往贵州叙永分校的继续撤退。
正如罗荪所述,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让诗人们走出了校园,走出了书房,走出了亭子间;生活范围从北京、上海等几个主要城市延展到广大的内陆地区;他们因此得以近距离触摸到祖国辽阔的土地和风俗各异的山山水水。周定一在《赠林蒲》中是这样描述诗人的生活的:“告别岳麓山,/告别多情的湘水,/诗人撑起一把伞,/坚实的步伐,/开始踏上三千里。//过万重山,/过千条水,/过神秘的桃花源。……/你旅店的情思,/飘渺于故国山河;/北地的风尘,/还遥遥在背后追赶。/你终于来到这蛮荒小城,/脱下风尘剥蚀的行装,/伴一湖清水,一园好花,/用你饱蘸感奋的笔,/写出这一路神奇。//今天你又卷起行装,/挥手向湖水,/挥手向小城,/向湖边的友人指点星星。/这满天的星斗下,/到处都是诗人的家。”经过了“万重山”“千条水”的诗人们,正是用“饱蘸感奋的笔”写出了自己对祖国的新认识。冯至将自己在此期间出版的散文集命名为《山水》,着意于呈现那些在大后方意外发现的“还没有被人类的历史所点染过的自然”:那是礁石嶙峋、风紧浪急的赣江;是昆明郊外经过民族厮杀后消隐于自然中的一个无名的村落;是像“插入晴空的高塔”一样“在我的面前高高耸起”的有加利树;也是“躲避着一切名称”却“不辜负高贵和洁白”的鼠曲草。在冯至沉潜于自然山水的同时,卞之琳也在构思着他的《山山水水》。他无意于像传统小说那样营构曲折的情节,而是以诗人的笔墨饶有趣味地讲述着他所体验到的地理、风物、典故。只不过与冯至有意忽略那些人迹的所在,在静默中寻找着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思考着人类的运命不同,经历延安之行后的卞之琳将笔触伸向了正在进行的大后方的建设。于是我们看到在诗人关于山水的讲述中出现了展示知识分子宁纶年开荒经历的《海与泡沫:一个象征》。而那部纪念延安之行的《慰劳信集》更是详尽地呈现了解放区的画面:正在修建的把各地“一块一块拼起来”的飞机场、“热和力的来源——煤窑”、“拿着锄头、铁锹、枪杆、针线”,男女老少共同开荒的场景……
在历览祖国的山水之外,联大师生还有了同普通民众进行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联大迁徙中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在一路行进中,也十分留意进行民间采风。走在内陆贫瘠的土地上,他们不仅切身体验了民间的疾苦与艰难,也发现了潜藏于其中的活力和民族的希望。这使他们再下笔写作时,就增添了比以往更多的现实感和厚重感。穆旦的《出发》、《原野上走路》就是写联大师生三千里步行南迁的见闻感受的,但这已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游山玩水,而是在用“他们的血液和原野的心胸交谈”,用他们的热情感受那“祖先走过的道路”,通过把脉来思考民族的命运:军山铺“坐在阴暗的高门槛上的孩子”、太子庙“枯瘦的黄牛翻起泥土和粪香”、蝴蝶飞过的“开花的菜田”、那“自由阔大的原野”把诗人从城市的绝望中捞起,进而激起了诗人的“野力”和对这个民族的期望。
而在战时的特殊环境中,这些山水土地上又不可避免地上演了战争的场景。大后方战时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跑警报”。据当事者回忆,昆明的警报之频繁,“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⑤每当警报响起,大家就往郊外跑,俗称“跑警报”。穆旦将这一过程形象地记录在了《防空洞里的抒情诗》里:疯狂的人们往防空洞里跑——在防空洞里的谈话和感受——警报解除后往回走——发现了被炸毁的楼和僵死的我。如果这还算常态的战时生活的话,那么亲身参加抗日远征军则为穆旦、杜运燮等提供了直接的战争经验,在他们笔下出现了描写那场艰苦战争的《给永远留在野人山的战士》、《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等作品。但仔细分析这些描写战争的作品可以发现,诗人们很少正面描写战争的场面,而是把目光聚焦在活动在这些场景里的“人”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西南联大的很多诗歌是直接以人来命名的。卞之琳的《慰劳信集》简直就是一部延安各色人物的剪影集,集中每首诗的题目都是一位或一群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如《前方的神枪手》、《建筑飞机场的工人》、《地方武装的新战士》、《放哨的儿童》等。杜运燮笔下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士兵:《号兵》、《狙击兵》、《被遗弃在路旁的死老总》、《一个有名字的兵》……在这些诗中,诗人或从战士(人)的感受来体验战争:“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穆旦《森林之魅》),或关注战争中人的处境和精神面貌。在《一个有名字的兵》里,杜运燮以调侃的笔调写出了张必胜在别人眼中冒着傻气的一生:张必胜“做过两次人:一次在家里种田,另一次是当兵”,他是个麻子,却“老实得出名”。种田的张必胜勤勤恳恳,“犁田割稻样样都行,/样样都比人家多一倍”;当了兵的张必胜挑水、砍柴、打草鞋、上火线送饭,“震醒了全连”。诗歌题为《一个有名字的兵》,但张必胜作为抗日战争中默默奉献的无数士兵中的一员,他的名字其实又往往是为人忽略的,他的生与死并没有太多的人关注。在此,诗人看似轻松和毫不在意的笔调与张必胜对“生”的认真和执着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而结尾处,诗人笔锋一转,让张必胜在庆祝抗战胜利游行后死在路旁,悲剧意蕴陡增。这种轻松与严肃、喜剧与悲剧的对比,形成一种反讽的戏剧张力,引发了读者对战争中人的境遇的思考。从人的处境和体验出发,诗歌中的战争描写就不仅是呈现一种客观的苦难画面,而是渗入了诗人的主体思考。
这种主体的密切参与,使得诗人们在了解了祖国的山水、接触了民间的现实之后,能更深入地体察分析国家的痼疾,并进而以强烈的担当意识寻找解决这痼疾的出路。
二、承担我们时代的使命
如果说1930年代的现代派还能沉浸在“深闭的园子”里做一个唯美的“寻梦者”,那么经历国破家亡的1940年代诗人,却必须面对这样的《我们的时代》:“一座偏僻的小城”,因接纳了大城市迁徙的人流而变得繁荣,也因此成为敌人袭击的目标。于是这里出现了死亡,出现了忧患,也出现了“丑恶的面目”,但我们不愿意“坐在方舟里”,不会“让什么阻住了我们的视线”,而是要“向着过去的艰苦”、“向着远远的崇高的山峰”迎上去。我们渴望着将来有一天拥抱着我们的朋友说,“我们曾经共同分担了/一个共同的人类的命运”,却“不愿听见几个/坐在方舟里的人们在说:/‘我们延续了人类的文明。’”正因为处于这样一个艰苦的时代,西南联大的诗人们不可能像他们所推崇的艾略特等西方前辈那样,沉浸在艺术反叛的满足中,以“非个人化”的冷漠姿态对资本主义文明提出质疑。他们更强调要表现“本土”的情绪,表现“茁生于我们本土上的一切呻吟,痛苦,斗争和希望”。⑥他们以直视苦难、平庸和黑暗的勇气,通过诗歌创作肩负起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使命。
基于这种直视的勇气,诗人们首先在诗歌中大胆呈现了“病态中国”的真实形象。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是晚清时期随着西学东渐而传入中国的。形成伊始,作家们就迫不及待地通过他们的作品展开了各种国家想象。不管是《老残游记》里的“危船”意象,还是《新中国未来记》中的未来展望,都是这种想象的表现。而近代中国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局面,又使得作家们往往将国家想象与“病”联系在一起,“治病”几乎成为了改变中国落后局面的不二隐喻。鲁迅在《呐喊·自序》里那段有关“病”的著名表述更是广为流传:“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⑦西南联大的诗人们,沿袭了这种“探病”的传统,以敏锐的洞察力,诊断着中国的病灶所在。于是我们看到,他们的诗歌中呈现的中国是饥饿的:“昨天已经过去了,昨天是田园的牧歌,/是和春水一样流畅的日子,就要流入/意义重大的明天:然而今天是饥饿。”(穆旦《饥饿的中国》)这个中国正面临着干旱的死寂:“所有的沟渠呈露/出干裂的泥床,像枯了的海露出水手的骨骸/落叶的树木露出干枝。”(郑敏《旱》)这个中国已成为一片“溃败”的荒村:“荒草,颓墙,空洞的茅屋,/无言倒下的树,凌乱的死寂……”(穆旦《荒村》)这个中国正处于严酷而漫长的寒冬:在中国的冬夜里,“北风强劲地扫过流血的战场”,“城市遍布着凌乱的感伤”,“饥饿死亡的交响透过冻裂的时间缓缓奏鸣”,而“当雪花悄悄盖遍城市与乡村,/这寒冷的国度已埋葬好被绞死的人性。/只有黑暗的冬夜在积聚、凝缩、起雾,/那里面危险而沉重,是我们全在的痛苦。”(罗寄一《在中国的冬夜里》)在此之前,现代诗歌中很少出现如此惨烈的意象:流血、凌乱、饥饿、死亡。但这并不是冷静、客观地展示苦难,而在字里行间渗透着诗人的体验:凄苦、战栗、哭泣,最后凝结为“全在的痛苦”。这种经由体验而凝结的意象,正是穆旦所提倡的“新的抒情”的表现,它让我们在远离那个时代的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那种痛惜和沉重。
与苦难的国家形象相对应的,是有承担的诗人主体的出现。深受西方现代派诗风影响的西南联大诗人们,虽也在努力表现现代的、“残缺”的自我,但并不局限于个人经验的小范围内,而体现了向“集体”寻求力量的强烈意愿。在讨论到“我”的发展历程时,苏格兰诗人彭斯曾对现代的“我”与伏尔泰式的“我”作了这样的区分:后者“与它所欲影响的世界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理性主义和相信‘进步’的政治观”,批评讽刺的目的是为了影响和反对现有的力量;而前者受外在的影响,透过消极态度,“来渐变他面对的世界”。⑧梁秉钧认为穆旦《防空洞里的抒情诗》等诗歌中变幻的、不确定的、毫无英雄色彩的“我”,已经表现出现代的“我”的倾向。但其实穆旦等诗人诗中虽然不再高扬“我”的主体意志,却并没有放弃相信“进步”的政治观。诗人们一方面在诗中直面着现代的、不完整的自我,一方面又展示了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生活着的民众,包括古老中国贫困的农民、抗战的士兵、积极投身建设的群众等,他们勇敢而坚韧,分别承载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成为“我”的后盾。正因为有了千万人民作为背景,诗人可以勇敢地宣称:“我们看见,这样现实的态度/强过你任何的理想,只有它不毁于战争。服从,喝采,受苦,/是哭泣的良心唯一的责任——”(穆旦《控诉》);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我敢于同古老的中华民族一起,静静地“承接着雪花的飘落”。但现代对于主体的“我”的自觉意识,又使他们不可能完全消融于大众之中,而保持着自我的独立思考。在《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中,“我”虽然自由地转换于你、我、他的身份中,是人民中的一员,却又处处呈现为具有差异的个体。在诗的结尾,“我”走出人群,独自体味了死亡:“当人们回到家里,弹去青草和泥土,/从他们头上所编织的大网里,/我是独自走上了被炸毁的楼,/而发见我自己死在那儿/僵硬的,满脸上是欢笑,眼泪,和叹息。”这里既有直面死亡的承担,又分明带着现代人独有的失落感。但这种现代情绪并没有转化为世纪末的颓废和彻底的虚无与绝望,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期待激励着诗人们,虽身处寒冬却仍要向春天歌唱。
三、面向“现代化”的“建国”展望
诗人们之所以敢于袒露和直面这个古老民族的累累瘢痕,是因为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对祖国新生的期待。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存在着两种对抗战的看法:一部分人鉴于中国当时武器装备与日本的相差悬殊,对抗战持较为悲观的态度,其代表有吴宓、陈寅恪、冯友兰等。陈寅恪曾赋《蒙自南湖》一首:“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生平;桥边鬓影犹明灭,楼上歌声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关山几万程”⑨,颇为形象地表达了“悲观派”人士当时的心态。这些熟读传统诗书、深谙历史旧事的学者们,将西南联大的南迁与晋宋南渡联系起来,既然短期内对“王师北定”不抱多大希望,那么他们希望通过保存传统文化来延续民族命脉。而另一部分亲身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或在新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师生们则秉持启蒙的理想,从战争中看到了民族发展的新契机。他们“由于对于人类历史的一种真知灼见”,“在自己的痛苦中点起一把地下火,吹燃他,扩大他,想烧毁一切,也好重建一切”。⑩首先,他们对抗战的前景是乐观的。闻一多对饭桌上充斥的亡国论调深恶痛绝;穆旦极力推崇艾青那“充满着辽阔的阳光和温暖,和生命的诱惑”的诗歌,赞颂他在诗歌中“歌颂新生的中国”,提倡诗歌“对于生命的光明面的赞美”;朱自清更将目光扩展到建国,“我们在抗战,同时我们在建国”,并因此认为诗人作为“时代的前驱”,“有义务先创造一个新中国在他的诗里”⑪。其次,他们从抗战中看到了民族新生的可能。“五四”退潮后,复古主义的兴起、思想界的沉滞、文学中的灰色情调都使新文学家们感到不满。抗战爆发固然使中华民族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但其强大的破坏力也预示了打破沉滞黑暗、重新振兴的可能。沈从文这位致力于“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⑬的作家,也从耳闻目见中发现了“湘西在战争发展中的种种变迁,以及地方问题如何由混乱中除旧布新,渐上轨道”⑬,因此寄希望于通过战争净化堕落的中国。朱自清则感到“抗战以来,第一次我们获得了真正的统一;第一次我们每个国民都感到有一个国家——第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中国是自己的”⑭。穆旦也认为抗战“使整个中国跳出了一个沉滞的泥沼,一洼‘死水’”⑯,唤起了中国人的斗志和觉醒的意识。凤凰涅槃固然要经受炼狱般的痛楚,但也正因为其敢于抛弃陈旧的过去,才能获得新生。对冬天的直视,是因为看到了春天的来临。
于是我们看到诗人们在不惮于展露丑陋和黑暗的同时,内心又充满着战胜困难的强大信心和对光明的坚定向往。穆旦的诗作《赞美》,可谓是他自己所呼吁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在这首诗里,诗人怀着强烈的对未来的期待,赞美那坚韧的历史缔造者——人民。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地因“有无数埋藏的年代”,而蕴积了“说不尽的故事”、“说不尽的灾难”,这些漫长岁月里的主角是“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伛偻的人民”,他们经历了无数朝代的变迁、经历了希望和失望的轮回,却“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延续着“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然而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刻,他们“放下了古代的锄头”,“溶进了大众的爱”,虽然意识到自己死亡的命运,意识到等待新生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但“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尽管在句句诗行中,我们可以体验到那“夹杂着纤细的血丝”的痛楚,但诗人以坚定的信心宣告:“我们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对抗战胜利和民族新生的展望,让诗人们不仅将目光投向当下的抗战,也开始关注未来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朱自清在《诗与建国》一文中,从理论上明确提出应在诗歌中表现国家现代化的要求。他认为现在的诗人大部分在“集中力量歌咏抗战”,他们虽然也相信“建国必成”,但较少地在诗中表现现代化建设的成绩。而这是抗战以后的目标。只有出现了“歌咏现代化的诗”,才能“表示我们一般生活也在现代化”,因此他呼吁“建国的歌手”的出现。⑯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这里所说的“现代化”,已不同于1930年代现代派诗歌中出现的都市现代化。他所指的不是跑马场、电影院、舞厅等现代消费场所,而是大后方经过战争破坏后的重建,包括新的公路铁路的开通、城市市容的整修和防空洞的挖建等。
在这种理论观照下,杜运燮的《滇缅公路》就被朱自清称赞为是朝着“现代史诗”方向努力的作品。在诗人笔下,滇缅公路已不仅是一条实体的交通线,同时还承载了整个民族的等待。它不仅连接着原始的过去、无情的现在,也会通向光明的未来。这条“不平凡的路”的“不平凡”的建设者也许在承受着饥饿、辛劳、阴谋的剥削,但从来不缺乏勇敢与坚韧,也不会丧失对自由和胜利的期待。这些“每天不让太阳占先,从匆促搭盖的/土穴草窠里出来,挥动起原始的/锹镐,不惜仅有的血汗,一厘一分地/为民族争取平坦,争取自由的呼吸”的劳动者,同英勇的战士一样,成为促进民族发展的群体英雄。正如朱自清所称赞的,这首诗“不缺少‘诗素’,不缺少‘温暖’,不缺少爱国心”,它表现出“忍耐的勇敢,真切的欢乐,表现我们‘全民族’”,是对整个民族前途的展望。⑰这种表现现代化建设的诗歌,同样出现在卞之琳的笔下。只不过卞之琳无意于史诗式的长篇书写,诗中也很少有那种沉雄磅礴的气势,而是充满了独特的“卞式”机智和幽默,但其中同样表达了对“建设者”的赞美:“所以你们辛苦了,不歇一口气,/为了保卫的飞机、联络的飞机。/凡是会抬起头来向上看的眼睛/都感谢你们翻动的一铲土一铲泥”(《修筑飞机场的工人》);他还看到了群体的创造力:“如今你们把一条支线/扭转了方向,断断又连连,/十里,十里,又九里十九盘,/转上去,转上去,转进了太行山,/回想起来我还是惊奇:/时间抹不掉这条痕迹!”(《抬钢轨的群众》)
在《想像中国的方法》一书中,王德威先生提出了“小说中国”的概念,指出小说流变与中国命运的关联。他认为“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小说记录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种种可涕可笑的现象,而小说本身的质变,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表征之一。……谈到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乃至国史的编纂,我们不能不说叙述之必要,想像之必要,小说(虚构!)之必要。”⑱这一论述一方面肯定了小说这种文体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在正统的历史叙述之外,文学想象的重要性。比较小说而言,中国的现代诗歌固然不以虚构见长,然而其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记录这进程中“种种可涕可笑的现象”的作用却应是一致的。西南联大诗人们1940年代的诗歌创作,为我们呈现了大一统的建国神话之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认识和展望。在诗歌“现代化”的探索之外,为我们思考文学与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从这个层面上或许可以说,“诗歌中国”与“小说中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注 释
①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5页。
②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谢》,《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49页。
③罗荪:《抗战文艺运动鸟瞰》,《文学月报》第1卷第1期,1940年1月。
④沈从文:《云南看云》,《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⑤汪曾祺:《跑警报》,《汪曾祺全集》第3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页。
⑥穆旦:《他死在第二次》,《穆旦精选集》,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⑦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⑧转引自梁秉钧:《穆旦与“现代”的我》,《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
⑨王云:《访蒙自随笔二则》,《笳吹弦诵在春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页。
⑩李广田:《诗人的声音》,《李广田文集》第3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⑪⑭朱自清:《爱国诗》,《朱自清全集》第 2 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9页、第359页。
⑬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 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⑬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 1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⑯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穆旦精选集》,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⑯⑰朱自清:《诗与建国》,《朱自清全集》第 2 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1页、第353页。
⑱王德威:《小说中国》,《想像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