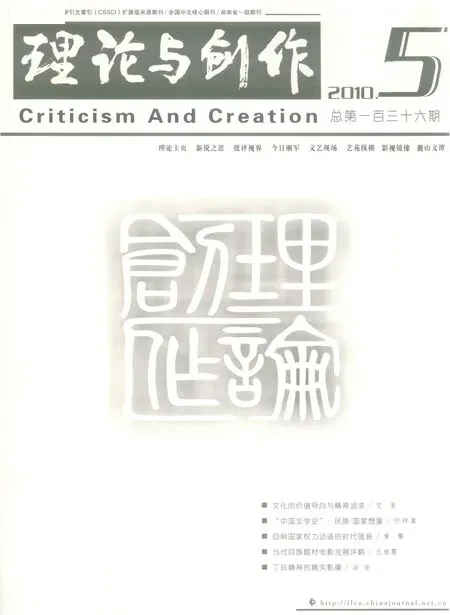论中国当代文学对新历史主义的接受与变异❋
■ 陈娇华
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于美国的一种文学批评实践,它以反抗旧历史主义、清理形式主义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由于与马克思主义、尼采历史系谱学、福柯权力话语及格鲁兹文化人类学等理论的复杂渊源关系,“无法定论”成为其重要特征。不过在长期批评实践中,新历史主义还是形成一些基本观点①。新历史主义于1980年代中后期传入国内,经由印象式评介,到系统化、理论化译介和阐发研究,再到实践操作和批评运用等,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较早涉及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是1986年王佐良《伯克莱的势头——一次动情的旅行》,认为新历史主义与布罗代尔新历史学有关,是“联系社会制度来研究文学”②。随后,施咸荣介绍美国最新文艺理论时提到,新历史主义是“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探索文化”③;王逢振在《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也论及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作品不是某种特殊的东西,“历史的叙述与文学的叙述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文学是一种交流方式,是某个特定历史时刻的文化方式”,必须把作品放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考察等。④这些尚属粗略的印象式评介。1991年赵一凡《什么是新历史主义》、晓风和晓燕《新历史主义批评对解构主义的超越》,及1992年张京媛《新历史主义批评》、李淑言《什么是新历史主义》、毛崇杰和钱竞《论新历史主义》等文章中,新历史主义的思想渊源、生发背景及主要观点开始得到具体阐述,触及到冲击传统史学整体模式、打乱目的演进秩序、瓦解宏伟叙事的新历史观念,及文本历史化和历史文本化、消解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等级和界限、创作与批评活动的政治性等理论。但直到1993年后,对新历史主义的系统化和理论化译介和阐发研究才真正开始。涌现盛宁《历史·文本·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刍议》、徐贲《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王一川《后结构历史主义诗学——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述评》、杨正润《文学的“颠覆”和“抑制”——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功能论和意识形态述评》等系统化和理论化阐述文章,及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盛宁《新历史主义》、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等系统翻译和阐发研究专著。大约于1995年前后,新历史主义理论开始运用于文学批评与研究实践,即从新历史主义理论、视角研究文学创作和文学现象,这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在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相当盛行。当然,中国当代文学在接受新历史主义理论同时,也在进行着同化和变异。这里,主要从文学创作、文学史重写及文学批评与研究等三方面进行梳理和考察。
一、文学创作:从解构走向重构的新历史小说
新历史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是对传统历史观念的冲击和解构,涌现“新历史小说”创作热潮。新历史主义在美国是一种文学批评实践,但在引入国内时,最先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是其历史观念的变化。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就是我们对过去的看法,是一个不断结构的本文。“历史是解释的而不是发现的结果,历史研究者永远只能构设历史,而不可能复原历史。”⑤因此以“小写复数化”、“对话过程化”及“偶然即兴化”历史观念⑥冲击和解构传统的整体化客观历史观念。
1980年代中后期新历史小说,莫言《红高粱》、乔良《灵旗》及苏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等,不是西方新历史主义自觉影响的产物,创作目的不是为了消解和颠覆传统历史观念,而是旨在消解政治意识形态、进行审美探索创新。但在历史观念和哲学意识上却与新历史主义具有同源性。形成新历史主义思想观念基础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潮等也是中国新历史小说创作出现的重要原因。1990年代后新历史主义理论在国内得到系统化理论化译介和阐发研究,理论与创作形成互动。新历史小说如李锐《旧址》、苏童《我的帝王生涯》、刘恒《苍河白日梦》、刘震云“故乡”系列等受新历史主义影响明显。形成以解构传统创作观和历史观为主、倾向新历史主义的创作特征:(一)不再追求所谓客观历史真实,历史成为淡远的背景、氛围及情调;(二)以边缘性村落史、家族史和欲望史取代以往宏大社会政治史;(三)主体肆意穿行于历史中,想象和虚构历史,形成历史与现实、死者与生者对话关系等。
不过,这些创作在接受新历史主义影响同时,也在进行中国化变异。其一,解构中蕴涵人性真实与审美探索。初期新历史小说莫言《红高粱》、乔良《灵旗》等,由于激进形式探索导致整体历史被割裂成碎片,解构性成为显著特征,但并未完全否定历史真实。《红高粱》反拨占主流话语地位的“红色经典”,“力图恢复历史真实”,⑦《灵旗》“要真实可触地再现那段历史”⑧,都试图从人性、情感角度恢复和丰富历史真实。周梅森、李锐、苏童等虽然质疑本质论历史真实,但陷入人性/情感真实或审美探索中。周梅森说历史“是阴谋和暴力的私生子”⑨,苏童认为历史只是探索人性、存在和审美可能性的“符号式的东西”⑩,李锐不相信所谓“统一‘真实’的历史”,于是“走进情感的历史,走进内心的历史”。⑪因此,他们都在质疑、解构历史,把历史视为探索人性、存在及审美载体同时,又以人性、情感真实去丰富、补充历史真实,呈现历史复杂丰富的原生样态。新世纪初《生死疲劳》《圣天门口》《笨花》等新历史小说,更是在质疑历史真实同时,体现出对历史的尊敬和慎重态度及对历史真实的信任感。而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客体,即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只存在于作为表述的现在模式中,除此之外就不存在什么历史客体”⑬。因此避开历史客体,转而关注历史文本与别的文本之间的关联。其二,丰富和完满历史叙事。新历史小说多取材于边缘性家族史、村落史或欲望史,类似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以取代和颠覆主流历史叙事。但“文化诗学”主要挑战“占统治地位的语言表达的典范规则”,发掘历史内里的“诗学”性质,⑬揭发“边缘”背后隐匿的“权力运行的内在轨迹”⑭。而新历史小说选择边缘题材主要为了反拨以往历史文学叙事过于政治意识形态化以至淹没历史真相,使历史叙事趋于更丰富和更完满;同时也为了进行审美探索创新,民间边缘史蕴涵丰富神奇的审美元素。其三,纯粹的审美探索。新历史小说以限制性叙述取代全知叙述,叙述者“我”肆意穿行于历史和现实之间,任意想象和虚构历史,使以往全知客观历史个人化和主观化。类似于新历史主义的客观历史主观化。然而,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是历史的一部分,它不是被动反映外在现实,而是本身就是建构文化现实感的动因,参与历史过程和对现实政治管理。⑯格林布拉特指出:“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价值的。”⑯而新历史小说创作转向历史却是出于对现实政治和权力话语的规避。在新历史小说作家心中,文学永远是纯粹的审美艺术,任何历史元素都只是进行审美探索和人性、生命与存在探询的载体而已。
特别是新世纪初,新历史小说创作由开始解构传统创作观念、历史观念,转向回归现实主义、回归对历史的尊重和慎重,更体现出新历史主义的中国化变异。初期(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新历史小说,莫言《红高粱》、乔良《灵旗》、格非《迷舟》等,把突破现实主义成规作为发端,“都有一种对主流历史反思、质问的自觉”,及“对主流地位的‘红色经典’的一种反驳”。⑰格非说“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比‘现实主义’这样一个概念更让我感到厌烦的了。”⑱叙述形式的激进探索突破了现实主义创作观念和叙事模式,传统历史观念随之土崩瓦解。后期(9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初)新历史小说,莫言《生死疲劳》、格非《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刘醒龙《圣天门口》等开始回归和重构意向,出现对线性完整叙事、史诗性艺术及确定性价值和意义的回归倾向。刘醒龙坦言《圣天门口》“是想恢复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尊严。”⑲莫言说:“重建宏大叙事确实是每个作家内心深处的情结,所有的作家都梦想写一部史诗性的皇皇巨著。”⑳格非也谈到:“现在有些作家醉心于现实主义并非坏事……我现在更多地关注‘写什么’,而不是‘怎么写’”㉑《圣天门口》和《生死疲劳》则开始重构人道主义历史,不同的是,前者是西式基督教人道主义,后者是中国化的佛教哲学思想。《人面桃花》与《山河入梦》也以几代知识分子对乌托邦信念的执著追求,体现作者对20世纪中国革命与民众、革命与知识分子及历史与现实等问题的执著探求,其中虽不乏质疑和解构成分,但更有执著和坚守,体现作者“要亮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观念与精神立场的决心”㉒。总之,在新历史小说作家心中有一个抹不去的确定性整体情结,新历史主义完全文本化历史、实质“反历史”的后现代历史观只是带给他们一种重审历史的新视野,加深他们对历史的丰富性和驳杂性认识,而不可能完全取得他们认同。
二、文学史重写:求真和求全的整体文学史观念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新历史主义尚未传入国内,重写文学史话题就已提出。1983年朱光潜《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代序)》中指出:“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暗含对既有文学史框架的不满和要求重评意思。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明确提出,“要从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从文学的现代化,从中国人‘出而参与世界的文艺之业’,从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等重写文学史,㉓改变以往把文学史发展简单比附于社会政治史/革命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极富现代启蒙理性色彩:(一)打通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界限,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呈现整体性的文学观念。(二)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看作一个不断向前发展、转变,最终汇入开放的世界文学总体格局进程,隐含乐观的进化论思想。(三)把“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以“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暗含文学自律性要求。㉔1988年《上海文论》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具体实践这些观念。但这些重写仍拘囿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学性与政治性等二元思维模式中,没有从文学与历史关系出发,追究文学史建立背后的权力结构关系。即没有把作家作品以外的全部文学实践纳入视野,包括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建设及其运作等。
1990年代后,新历史主义在国内得到系统化和理论化翻译介绍与阐发研究。在新历史主义理论辐射及文化研究热潮(新历史主义本身隶属于文化研究范畴)影响下,80年代中后期重写文学史观念开始付诸实践,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学史重写景观。新历史主义没有专门、系统探讨文学史问题,但对历史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解放了文学史写作思维和观念。㉕并且在零散论述中也有触及,概括起来:(一)“所有文学史的构成皆是政治性的”,要“赋予那些先前遭到排斥的因素以再现,从而修正过去的政治偏私”。㉖(二)要重新考虑“那些典范的……文学和戏剧作品得以最初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它不仅与别的话语模式和类型相联系,而且也与同时代的社会制度和其他非话语性实践(non-discursive practices)相关联”。㉗(三)“任何文本的阐释都是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和文本意义的重释”,阐释者受制于现实处境,在重写历史同时也以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参与和建构未来。㉘这些冲击和解构以往单一的整体文学史神话,为重写文学史提供新的历史观念和研究思路。
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作为重写文学史成果涌现的多部文学史著都呈现了某些新历史主义特征,这里仅以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及孟繁华和程光炜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以下分别简称洪著、陈著及孟著)等为案例进行分析。其一,发掘以往被主流文学史排斥、遮掩的边缘作家作品及创作现象。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史写作从属于政治压力,选择哪些作家应该得到规范的地位,不是一场仅涉及文学天才相对优点的论争,而是一场关涉权力结构关系的斗争。主张发掘过去被排斥和淹没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以“修正过去的政治偏私”。陈著对极左年代“潜在写作”的发掘,洪著对最初异端文学(百花文化、地下文学等)的打捞,孟著对诸多非文学因素(政治文化、权力体制、外部资源等)的重视等,都暗合上述新历史主义观点。其二,重返历史现场,复原历史情境。新历史主义强调重建文学历史维度,把文学文本置于其他文本中,探究文学是如何被所处时代意识形态穿越、如何由意识形态产生、又如何作用于意识形态。上述文学史著也强调重返历史现场。洪著“竭力‘搁置’评价,把‘价值’问题暂且放在一边,而花大力气考察当代文学某些概念、事实、运动、争论、文本、艺术方法产生的背景、历史依据、渊源和变异”,以增加“靠近”历史的可能性。㉙陈著考虑的是如何从二元对立理论框架中走出来,让文学史重返丰富复杂的历史现场,恢复文学固有的艺术实践和审美趣味演变,展现比较完整的文学历史。孟著也注重从文化环境、组织制度和外部资源等,揭示当代文学的生成语境、基本面貌及其与各种权力话语(政治或商业等)间的互动关系等。其三,注重个体情感、体验的渗入和参与。新历史主认为任何历史都是文本,而“任何文本的阐释都是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和文本意义的重释”。重视个体对历史的参与和建构。文学史写作本身就是对文学历史的一种再解读,解读者的个人情感和体验自然会渗入和参与到文学史重构中。洪子诚谈到重写文学史,理论固然重要,但自身经历、体验有时更重要。“这种体验会渗透在血液中,产生重要的冲击作用,加深对原来信仰的质疑;而经验、感性留下的痕迹,常常很难擦抹。”㉚如果说洪著以史料丰富、态度严谨,坚持价值中立,显示出客观性和科学性;那么陈著以个人学术观点和生命激情强劲渗入,冲击传统文学史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理念,显示出强烈的个人化色彩。
然而与新历史主义相比,重写式文学史著明显发生了变异。首先,“大”而“全”的整体性文学史观。新历史主义从历史文本化和文本历史化观念出发,认为没有单一的整体历史,只有由各种主体产生的“多种历史”。文学史沦为消失了整体性、充满各种症侯的非连续性、碎片化“百科全书”式文学史。然而上述文学史著追求文学史的整体性和完整性。陈著力图“打破以往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角,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㉛。以民间立场、潜在写作、现代性等统一中国当代文学史,通过发掘“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性,不仅使以往偏颇、欠完整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走向一体和完整化;也把它们统合到由现代文学、新时期文学构成的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中,呈现出大一统的文学史观念。洪著虽然没有像陈著一样,以80年代后的纯文学观取代此前的革命化/政治化文学观,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对‘大叙事’的强烈兴趣”㉜,使史著贯穿着“一体化”的写作观念和思路,即把当代文学史发展线索概括为一体化的形成、发展与解体过程,也即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换过程。孟著则通过复原历史现场、细节(如评奖制度、期刊运作及“文代会”现场等),体现“对文学史整体感的追求”。可见,重写式文学史没有动摇对整体性的信念,相反不断地丰富和增长着文学史新内容,体现对“大”而“全”的整体文学史观的坚信。
其次,“求真”的本质论文学史观。新历史主义同后结构主义、福科话语理论和文化人类学厚描法等保持暧昧关系,从根本上是反历史的,不承认历史客体和所谓历史本质。历史文本化,认为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一样,都是“社会能量循环系统的一部分”㉝。其要做的是摈弃纪念碑式或档案馆式文学史,着力发掘文学文本背后的修辞策略、叙事结构、内在的文化逻辑及断裂、非连续性的差异性等,呈现充满各种症侯式的碎片化“百科全书”式文学史。但重写式文学史著却坚持文学史真实信念。文学史真实包括对文学性和文学历史真实的坚守和信任。一方面相信文学具有独立于社会政治、哲学、历史之外的审美特性,即文学性,这是文学史筛选作品的标准之一。陈思和希望摆脱已有文学史思维模式,“以审美标准来重新评价过去的名家名作以及各种文学现象”㉞。陈著首先考虑的,是从二元对立理论框架束缚中走出来,让文学史回到丰富复杂的历史现场,恢复文学固有的艺术实践和审美趣味的演变等。洪子诚也谈到,“尽管‘文学性’(或‘审美性’)的含义难以确定,但是,‘审美尺度’,即对作品的‘独特经验’和表达上的‘独特性’的衡量,仍首先应被考虑。”㉟另一方面相信文学历史是完整和真实的,尽管历史概念变化不定,但在撰史者和评论者心中始终存在一部具有整体性的真实文学历史。不论是陈思和等以“民间立场”、“潜在写作”及“现代性”等“在历史和审美的标准范围内”“拨乱反正”,整合当代文学历史;还是洪子诚以“一体化”文学观念重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抑或是孟繁华等以“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为方法重绘文学史地图等,都体现出追寻完整、真实而又不无复杂性和丰富性的文学史企图。正如洪子诚所言:我们“虽然重视历史的文本性质,重视它的‘写作’层面,但在看待历史与小说的关系上,仍会采取谨慎的态度。这是因为,我们仍信仰历史叙述的非虚构性,对真实、真相、本质仍存在不轻易放弃的信仰”㊱。
此外,重写式文学史著强调重返历史现场,重构历史情境,类似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但其实两者也有根本区别。“文化诗学”强调“对在自己出现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支配和服从的结构,以及文化符码等的规则、规律和原则表现出逃避、超脱、抵触、破坏和对立”㊲。即主要为了解构和颠覆占主流地位的“正史”,揭发边缘历史被压抑背后的权力结构关系。而重写式文学史著则主要为了丰富和补充以往文学史的遗漏和欠缺,复原文学历史发展丰富复杂的原生样态。洪著不论是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中“异端”文学的发掘,还是对80年代后文学多样化复杂历史情境的叙述,抑或是对以往“政治/文学、正统/异端、压制/驯服、独立/依附”等二元对立历史叙述模式的规避等,都是为了体现和建构“一体化”文学史发展的整体观念。陈著也努力“打破以往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角,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发掘“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潜在写作”现象,“让文学史回归到丰富复杂的历史现场,恢复文学固有的艺术实践和审美趣味的演变,展示出比较完整的文学的‘历史’”㊳等。
总之,重写式文学史著以独特的个性风格,突破以往过于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整体性文学史,从思想史、文化史及审美化和个性化等方面发掘和打捞被遮掩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呈现出新历史主义某些特征,体现出文学历史发展的多元化、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由于教学与研究、文学性与历史性、通史意识与个性独创等多方面考量,真实和完整仍是这些文学史著的共同坚守。
三、文学批评与研究:在文化中坚持审美特性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实践,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循环式阐释。考察“深入文学作品世界的社会存在和文学作品中所反映出的社会存在”,看“历史事件如何转化为文本,文本又如何转化为社会公众的普遍共识,亦即一般意识形态,而一般意识形态又如何转化为文学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㊴其二,政治化功能。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政治化的文学批评,强调“凡事都要放到政治上去加以衡量”㊵,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发掘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的异在不安定因素,揭示这种复杂社会状况中文化产品的社会品质和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方式,及它们与权力的复杂关系。㊶其三,轶事穿插法。常从一些不为人知的诗歌、油画、塑像,或一则轶事等开始分析,穿行于文学与史实之间。然后在两者间找到一个联结点,揭示文学作品“与当时的意识形态有着怎样复杂的联系”㊷等。
如前所述,经过90年代初期的系统译介和阐述研究,新历史主义在90年代中期开始对中国文学批评发生影响。研究者主要运用新历史主义“小写复数化”、“对话过程化”及“偶然即兴化”等新历史观念,分析彼时新历史主义创作现象,如吴戈《新历史主义的崛起与承诺》、吴声雷《论新历史主义小说》、李洁非《圣者之诗——对〈家族〉的体味》等。从历史观念新变出发,探讨新历史题材创作在历史观念、题材选择、叙事方式及价值倾向等方面特征。这是一种研究新历史主义创作现象的主流批评,一直延续至今。还有一种是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指离开文学研究的传统对象,转而研究广告、时装、电视节目、酒吧等大众文化研究;狭义则指把文化研究的方法、思路引入文学批评与研究中㊸,这里指后者。从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中国文学批评对新历史主义的接受由前期侧重历史观念新变,转向这时期研究视角和方法蜕变,出现“文革文学”研究、“十七年文学”研究、“再解读”思潮及“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等(前两者主要以现代性和审美性等观念重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研究思路类似“重写文学史”论文及陈著;故不再赘述,这里以后两者为例)。
“再解读”思路早在1990年代初就已出现,如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李扬《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等。但在国内批评界真正引发反响,形成一股热潮是在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涌现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等。“再解读”的实践理路几乎就是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中国运用。“不再是单纯地解释现象或满足于发生学似的叙述,也不再是归纳意义或总结特征,而是要揭示出历史文本背后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解读过程“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蔽、被涂蚀的历史多元复杂性”㊹。如以“暴力的文学形态”及“文学对暴力的转述”重读《暴风骤雨》;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基本主题的无意识重演解读《棋王》;及从作品创作、发表过程与改革开放派的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互动重评《班主任》等。
近年来兴起的“重返八十年代文学”更体现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接受和运用。倡导者自称以“当事人”和“旁观者”双重身份“重返80年代”,“处理80年代的知识背后的结构性的东西”,不仅要把80年代文学历史化,更要“重识一个方法论意义上的80年代”。㊺一方面认为“80年代的文学史,是以‘新启蒙’为中心的知识分子文学话语方式贯穿始末的,是‘精英文学(或说纯文学)’对其他文学样态的‘话语霸权’”㊻。因此要突破和颠覆这种话语霸权,重返历史现场,不再局限于精英作者创作与精英批评家的解读,而要将图书市场状况、读者的阅读预设、文学体制及整个社会思潮动向等纳入重读视域;另一方面力图揭示新时期精英文学话语体系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自身的,“把那些超越性的普泛价值和大叙事,拉回具体历史语境中,展示其认同与排斥的运作轨迹。”㊼这些显然带有新历史主义“文本历史化”及“循环式阐释”互证印迹。
然而,上述文学批评/研究决不是新历史主义的生硬移植。其一,对文学审美性的坚守。新历史主义强调跨学科研究,消解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疆界,“以一种文化系统中的共时性文本去替代那种自主的文学历史中的历时性本文”㊽,取消文学超然于历史之外的自律性特征。然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始终坚守文学审美性。前面两种批评中,第一种以新历史主义历史观念研究新历史小说的题材选择、叙事形式及形象塑造等,本身并未超出审美范畴。第二种文化批评中的“再解读”和“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等也重视文学审美性。童庆炳强调“对于文学的文化研究来说,文学的诗情画意是其生命的魅力所在……我们仍然坚持,文学批评的第一要务是确定对象美学上的优点,如果对象经不住美学的检验的话,就不值得进行历史文化的批评了。”㊾金元浦也说“文学的跨学科的努力,转向文化的开拓都是基于文学本体的基点或立足点”,文化研究“仍将逐步重建本学科的独特性或特殊性”。㊿“再解读”对文本内层的“细读”过程本身就是新批评精神的延续。“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也要面对“纯文学”问题,不论是对之的彰显还是搁置,强调文学审美性的纯文学观都是绕不开的情结。王尧指出“重返八十年代文学”要“在坚持‘纯文学’的基本价值并且也‘与时俱进’”基础上“以‘大文学史’观来看待文学的格局”。[51]其二,半循环式阐释。新历史主义以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间的循环式阐释互证取代传统“镜子”式批评和“灯”式批评。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虽然有文化化倾向,即“不再是单纯地解释现象或满足于发生学似的叙述,也不再是归纳意义或总结特征,而是要揭示出历史文本后面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52],揭出矛盾和裂隙。但也止于这一层面,至于文学(文化)是“如何建构起这样的历史叙述,在建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冲突和调整,最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叙述的‘无效’”[53],以及文学/文化文本如何参与历史建构和现实管理等,并未成为其关注重点。批评只是一种学院式学术经验描述,难以转化成社会批判力量。其三,政治化批评。新历史主义消解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界线,使文学活动参与历史进程与现实管理,文学批评走出学院式批评象牙塔,“成为论证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权力斗争、民族传统、文化差异的标本”,呈现出政治化批评色彩。[54]但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文学审美性始终作为潜在前提存在着,批评至多是对形成这种审美性的背后因素的发掘和丰富,或停留于对一种文学/文化商品化、世俗化现象或文化多元化现象的描述与欢呼。此外,常见于新历史主义的花絮式轶事穿插法,在中国文学/文化批评实践中也比较少见。
综上所述,新历史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是多方面的,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视域,把一些边缘性话语、非文学性因素等纳入到创作与研究视野;对198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日益脱离现实、沉浸于纯文学象牙塔的发展趋向起到一定纠偏作用,使之更贴近社会现实,关注民众生活和生存状态。但应当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始终未曾完全新历史主义化,而是保持对文学审美性、整体性文学观念及本质和真实等的坚定信念。这既有中国源远流长的史传文学传统,“为人生”现实主义文学的世纪主流位置,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影响;更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文学去政治意识形态化和进行审美探索创新的发展趋向所决定的。中国当代文学曾长期束缚于政治化意识形态中,进入新时期,中国文学便急切要求“去政治化”。而80年代中后期,正是中国文学急剧去政治意识形态化、进行审美探索创新和文学审美性研究时期,从西方传入的新历史主义由于强调取消文学边界和强化政治化批判功能,在当时并未引起作家和研究者注意。只有到90年代后,当强调自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日益脱离大众,却又不得不面对大众和商品化的社会现实时,文学的文化批评/研究及创作的历史重构才真正盛行起来。因此,回顾和梳理新历史主义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影响的这些历史,有利于清理一些复杂的文学现象和事实,正确认识中国文学发展与世界文学思潮关系,为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发展保持一份清醒和自信。
注 释
①许多论者进行过归纳,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8页;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第170-173页;石坚、王欣著:《〈似是故人来——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美文学〉序》,重庆大学出版社,第ⅵ页等。
②王佐良:《伯克莱的势头——一次动情的旅行》,《读书》1986年第2期。
③施咸荣:《八十年代美国文学发展的几个新趋势》,《译林》1988年第1期。
④王逢振:《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7页。
⑤徐贲:《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文艺研究》1993年第3期。
⑥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9页。
⑦⑰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⑧乔良:《时代假我之手写〈灵旗〉》,见乔良博http://blog.sina.com.cn/qiaoliang99。
⑨周梅森:《军歌》,长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70页。
⑩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3页。
⑪李锐:《关于〈旧址〉的问答——笔答梁丽芳教授》,《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⑬⑬㉖㉗㉘㊲㊽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第106页、第71页、第95页、第7页、第106页、第95页。
⑭⑯㊵㊶[54]王岳 川:《后殖 民主 义 与 新 历 史 主 义 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第170页、第170、214页、第 170页、第 170页。
⑯《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⑱格非:《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⑲刘醒龙、汪政:《恢复‘现实主义’的尊严——汪政、刘醒龙对话〈圣天门口〉》,《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⑳莫言、李敬泽:《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㉑格非、静矣:《真实的写作》,《黄河》2000年第 2期。
㉒张清华:《〈山河入梦〉与格非的近年创作》,《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㉓㉔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1页。
㉕乐黛云:《历史·文学·文学史——中美第二届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侧记》,《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
㉙《中国当代文学史笔谈》,《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㉚㊱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1页、第24、4页。
㉛㊳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第8页。
㉜陈平原:《四代学者的文学史图像》,《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㉝石坚、王欣:《似是故人来——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美文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㉞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文学评论家》1989年第2期。
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㊴㊷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页、第266页。
㊸㊾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第3页。
㊹[52][53]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页、第271-272页、第277页。
㊺杨晓帆等整理:《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研讨会纪要》,《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㊻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㊼贺桂梅:《80 年代作为“方法”》,《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㊿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51]王尧:《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