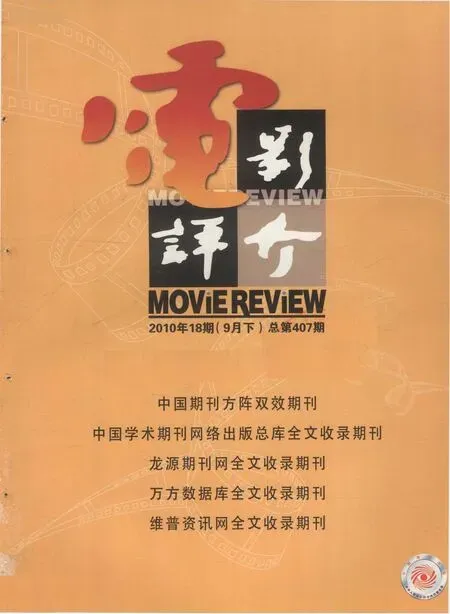早期儒家关于礼乐关系的定位、原因及意义
先秦儒家在恢复崩坏了的西周礼乐的同时,还注重对礼乐精神的探讨。特别是到了战国末期,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对礼乐精神及礼乐关系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看法。而经汉儒整理的《礼记•乐记》(以下简称《乐记》)篇,虽然主要内容是探讨乐的精神,但又“每以礼相配而言之”[1](p.987),因此,该篇是研究早期儒家礼乐关系观的重要文献。
关于早期儒家对礼乐关系的定位问题,在已有的关于儒家礼乐精神的研究中,大多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在对此问题的专门研究成果中,最重要的当属庞朴先生的《儒家辩证法研究》一文。庞先生认为,儒家心目中的礼乐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而统一的连接点是“中”[2](p.456~471)。此外,还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礼乐同构说”[3]、“内在张力说”[4],等等。笔者认为,《乐记》和《荀子•乐论》所反映的礼乐关系观是早期儒家不断探索、逐渐完善的结果,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已有的研究成果很少注意到这点,多为静态描述。本文即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早期儒家关于礼乐关系的定位及意义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礼、乐的内涵
要把握儒家对礼乐关系的定位,须先弄清楚礼乐的内涵。
关于礼,儒家在不同的层面上对礼有不同的定义,“礼”有三个涵义层面:一是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礼节、仪式,即所谓“仪”;二是典章制度,所谓“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5](p.1266);三是宇宙天地间的一切法则,所谓“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5](p.1457)。
对于“乐”,也有不同层面的涵义。《乐记》曰:“(人心)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1](p.976)儒家认为,“声”仅为单一音调的重复(郑玄注:“宫商角徵羽单出曰声”[6](p.662)),而多个音调的杂比排列则为“音”,即“今之歌曲也”(孔颖达疏)[6](p662.),但严格说来,这都还不是儒家所讲的“乐”。只有在“音”的基础上加上各种乐器的伴奏(“比音而乐之”的“乐”作“乐器”解),辅之以文舞武舞等舞蹈动作,方称得上真正意义的“乐”。所以,儒家所讲的“乐”,严格地讲,是集歌曲、诗、舞蹈、乐器伴奏等于一体的综合表演体系。当然,在不严格区分的情况下,儒家所说的“乐”,有时又单指“音”或“舞”。 ①
二、乐统同,礼辨异
就礼乐关系而言,早期儒家认为,分而言之,礼与乐一方面功能相反,一方面又可以补对方之缺,即相反而相成。对于礼乐的不同作用,《荀子•乐论》中指出:“乐合同,礼别异”[7](p.382)。换言之,乐是用来统合人心的,而礼则是用来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乐记》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乐统同,礼辨异”,又言:“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二者对礼乐功能的认识是一致的。儒家认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8](p.399)。儒家一方面承认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种种差异,另一方面又将其中的重要差异如男女、长幼、贵贱、尊卑等予以等级化,这就是礼。因此,礼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表现、维护这种差异,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7](p.347)。儒家认为,只有这样,社会成员之间才不至于发生争斗,社会才能有序。但有序并不代表和谐。礼在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分的同时,很有可能造成社会隔离,尤其是不同等级的社会成员有可能因“辨异”而疏离,甚至不满乃至相互敌对,反过来影响到社会秩序。而乐则可以弥补礼的缺失,因为“乐者,乐也”,乐可以使人欢乐,可以使不同等级、不同社会地位的成员产生心理上的共鸣,拉近他们的心理距离,从而产生相互亲近的心理需求。“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1](p.1033)这就是儒家所讲的“乐统同”。当然,如果只有“乐”,则社会成员就会狎昵无别,同样会发生混乱,所以还需要用礼来对他们进行区分。儒家认为,只有功能相反的礼与乐共同作用,才能实现既有差异又和谐的秩序世界。正如瞿同祖借用社会学的概念所揭示的,礼的作用在于维护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而乐的作用则在于维持社会团结(social solidity),二者皆为社会组织所不可或缺[9](p.296)。
早期儒家不仅认为“礼辨异,乐统同”是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而且还认为是天地自然的启示。儒家认为,“天高地下,万物殊散”[1](p.992),是“异”的表现,故与礼的功能相对应。“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1](p.993)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1](p.993)。凡此尊卑、贵贱及性命之种种差异,“皆礼之见于天地者” [1](p.993),天地自然之序别是礼的“辨异”原则的体现。同时,宇宙万物又“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1](p.992),“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1](p.993)天地之间,阴阳二气相互激荡,万物赖以生长,体现的是合同兴化的“乐”的功能。就天地自然而言,礼与乐分别表现为“天地之序”与“天地之和”[1](p.990)。“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1](p.990)在儒家看来,礼辨异与乐统同的不同功能的共同作用同样可实现宇宙自然的有序和谐,“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 [1](p.994)。另一方面,儒家又认为,“乐由天作,礼以地制” [1](p.990),“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1](p.992)儒家认为,天高地下、天尊地卑,乐的功能是和合,体现的是天之德,阳之性;而礼的功能是“别异”,体现的是地之德,阴之性。因此,虽礼乐虽功能相反而相成,但在形上的层面上,乐的地位被进一步抬高了。
当然,早期儒家对于“礼辨异,乐统同”的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尤其是,儒家对乐的“统同”的社会功能的认识更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西周统治者在制礼作乐时,乐本与礼为一体,在祭祀、朝聘、燕乐等礼仪中,都需要有乐的辅助才能完成,可以说乐的作用赞礼、成礼,礼乐是不可分的一体,这从《礼记•仲尼燕居》的一段记载中犹可窥见这点:“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县兴,揖让而升堂,升尝而乐阕。下管《象》、《武》、《夏》籥序兴。陈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规,还中矩,和鸾中《采齐》,客出以《雍》,彻以《振羽》。是故,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1](p.1269~1270)这时不仅礼乐不分,而且还要共同发挥合同辨异的功能,如《乐记》所载:“圣人作为鞉、鼓、椌、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者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1](p.1018)礼乐一体的另一表现是,乐制本为礼制的一部分,不同贵族在各种仪式场合下所允许使用的乐器的类型、数量、型制以及所允许使用的舞是有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和礼一样,乐也体现了等级,起到“辨异”的作用。总之,西周时的礼乐为一体,且无论在初始功能还是在制度方面,乐都是礼的附庸。春秋以降,礼乐发生了危机,而所谓“礼崩乐坏”的过程也是礼乐逐渐分离的过程。礼的危机主要有三点:礼制的破坏,作为仪的礼的过于繁琐,社会成员普遍不愿意守礼。乐的危机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而这三方面又往往交织在一起:一是诸侯国君、大夫对乐制的僭越。如鲁国季氏“八佾舞于庭”[10](p.41),又(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者以《雍》彻”[10](p.43),这都是对乐制的僭越,对礼制的违背。二是贵族蔑礼而崇乐,乐由赞礼、成礼之具变成了贵族娱乐、享乐的工具,由此而来的是靡费钱财,加重民众负担。三是民间音乐的兴起对“古乐”带来了挑战。面对礼乐的危机和挑战,儒家逐渐淡化了乐作为礼制的色彩,将乐制体现等级的“别异”功能移交给礼,乐则承担起和合民众的作用。对于乐的这个重要功能,我们可以从先秦儒家典籍中寻绎出早期儒家对此的认识过程。在《论语》中,孔子主要把“乐”看作修养心性、成就君子人格的重要内容,“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10](p.160)。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在与齐宣王就“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8](p.100)的讨论中,提出了“与民同乐”的思想,已初步具备了乐统同的思想。到了战国末期,荀子认为礼乐可各司其职、功能相反而可以互补,确立了“乐统同,礼辨异”的功能格局,从而将乐的社会功能及其与礼的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外,受《易传》思想的影响,战国末期的儒家还将“乐统同,礼辨异”比拟于天地自然,将乐的地位抬高到礼之上。②
三、以乐和礼,情理交融
儒家在推行礼治的时候,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人为什么要守礼?因为尽管礼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必要的制度(institution),但毕竟是“自外作”的,是强加于人身上的外部行为规范,未必能使每个人获得内心的认同。道家尤其是庄子就激烈反对儒家的礼制,认为是“以人变天”,违背了自然的人性,是对人性的戕贼。按照儒家的解释,礼是因人之情而设,“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1](p.1281),又言“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1](p.1468)但本来是缘人情而作的礼,却反过来对人性造成了束缚,使人感到不适,礼的功能发生了一定的异化。以继承西周礼制为志的儒家必须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使社会成员能够心安理得地知礼、践礼,实现儒家理想的礼治世界。对此,儒家将乐的“敦和”精神注入礼中,因为乐可打动人心而致和,以乐和礼,可使社会成员的内心的和敬之情与外部的威仪动作贯通起来,从而自外作的礼转化为内心主动、自觉的心理诉求,践礼就显得自然而不做作。原本儒家以理释礼,“礼也者,理也”[1](p.1272),礼为理之不可易者,即强调礼的“合理”这个面相。儒家在注入了乐的精神之后,礼又在“合理”的层面上增加了“合情”的内容,使礼“合情合理”,从而更加接近礼缘人情而设的初衷。故此,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主张,这是礼的精神发生重大的变化的标志,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礼必和顺于人心,当使人由之而皆安,既非情所不堪,亦非力所难勉,斯为可贵。若强立一礼,终不能和,有何得行?故礼非严束以强人,必于礼得和。”[11](p.19)并认为“此最孔门言礼之精义,学者不可不深求” [11](p.19)。就礼的预期作用效果而言,虽然儒家仍强调礼主敬,但其极致却不是“极敬”而是“极顺”,所谓“乐极和,礼极顺”[1](p.1030)。对此,孙希旦的解释是:“乐曰‘极和’,而礼不曰‘极敬’者,盖礼之用,和为贵,礼之顺,即敬之根于心而行之以从容不迫者也。”[1](p.1031)有了乐的“和”的精神,自外作的礼可唤起人内心的自觉意识,这样,人的践礼行为就如同乐章一样从容而和谐,“乐所以和礼,而礼之从容不迫者即乐也” [1](p.987)。
四、以礼节乐,礼体乐用
乐者,乐也。乐可以给人带来欢乐,这是先秦诸子都承认的。但乐也不是没有流弊。墨家和道家就对乐的消极方面提出了批判。墨子和老子虽然都承认乐可以使人欢乐,但墨子认为,乐成为了贵族享乐、纵乐的工具,属于“亏夺民衣食之财” [12](p.255)、“厚措敛乎万民”者[12](p.254),是于民有害的无用之物,故从兴利除害的角度看,应在废止之列。老子则对沉湎于乐的危害极为警惕,警告世人“五音令人耳聋”[13](p.6)。儒家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们认识到,“乐胜则流”[1](p.986)、“乐盈而不反则放”[1](p.1031)。如果对乐本身没有规定约束,乐就成为宣欲的工具,从而对社会造成危害。
针对乐的流弊,儒家的补救措施是:以礼节乐,即将礼的“辨异”和“节坊”功能嵌入乐中,用礼的原则约束乐,使乐从表演方式、内容和社会功能都带上了礼的色彩,直至将乐纳入到礼的体系之中。礼对乐的节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表现在乐的基本要素与表达方式上,其二是乐的社会功能方面。就乐的基本要素而言,宫商角徵羽本为乐之五音,但儒家却将君臣关系比附于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食,羽为物” [1](p.978)。宫商角徵羽五音其音本是存在由浊而清的次第关系 ③,儒家却将此次第递减之关系比附于君臣关系,认为“宫必为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为臣,而不可上于君;角民、徵事、羽物,各以次降杀” [1](p.979~980),又认为“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乱,则声音和谐,而无怙懘敝败也” [1](p.980)。这是儒家将“礼辨异”的功能赋予乐之五声。就乐的表达方式而言,儒家虽然承认乐是本于人心者,是人的喜怒哀乐得以宣泄的表达方式,但儒家又担心这种情感的过度宣泄的危害,于是又以礼的节坊原则来制约乐,使乐的表达方式趋于适中而不趋于极端,这样创作出来的乐就是“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14](p.46),形成执两用中、不走极端的表现风格,符合儒家的中庸原则,是为“德音”。相反,不符合中庸原则的乐则为“溺音”:“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1](p.1016)子夏将郑卫的新乐贬之为音而不称其为乐,就是因为郑卫之乐在表达方式上没有礼的节制,易使人的情感表达趋于极端。在儒家眼中,礼是乐的灵魂,乐的制作必须遵循礼的原则和法度,所谓“若无礼,则……乐失其节”[1](p.1296)。这样,嵌入了礼的原则的乐,在社会功能上要发挥和礼一样的作用,这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乐既要导民之情又要节民之欲,这与礼的作用是一致的。“礼,节也,故成”[7](p.491),乐也是如此,“乐也者,节也”[1](p.1272),这样乐才能使民众既“欣喜欢爱”[1](p.991),又“论伦无患”[1](p.991)。合而言之,“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1](p.986),礼乐同样都起着“节民心”[1](p.986)的“民坊”作用,所以儒家说“礼乐之情同,明王以相治也”[1](p.989)。其二是,有了礼的节制,乐不仅可“统同”,而且还涵有“辨异”的功能。“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行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 [1](p.1000)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乐就可以通伦理,“知乐则几于礼矣” [1](p.982)。经过儒家改造的乐,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乐了,而是处处体现的是礼的精神的表演程式,形成了礼为体而乐为用的“乐”观。这是儒家对乐的看法有别于先秦诸子的最显著特征。
总之,早期儒家对礼乐关系的看法是极为丰富而又充满了张力的。他们一方面认为礼与乐功能相反而互补,是相反相成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以乐和礼,以礼制乐,将本属礼与乐的各自原则来节制对方,形成相互制约、相互涵摄的关系,结果就是“二者并行,合为一体”[15](p.1028)。就礼与乐的相对地位而言,从形而上的层面看,乐的地位高于礼;但在形而下的层面上,礼又是乐的灵魂和主宰,乐仅是礼的表现形式,礼的地位显然高于乐。这种礼乐观的形成,既是早期儒家针对礼乐之弊和礼乐之偏而做出的思索,也是对先秦诸子的批判做出的回应,同时还是儒学不断发展的结果。早期儒家独特的礼乐观对后世影响很大,汉代以后的儒家对礼乐关系的看法无外于此;在实践上,这种礼乐观成为指导统治者制礼作乐的依据。
注释
①郭沫若认为,乐不仅包括音乐、诗歌、舞蹈,还包括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艺术,甚至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郭沫若.青铜时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41),这显然放大了乐的范围。实际上,《乐记》里所讲的“乐”当为音乐、诗歌、舞蹈三位一体的综合表演体系。
②早期儒家将“乐统同,礼辨异”与天地自然相联系,这种思想显然是受《易传》的影响,甚至《乐记》里的字句都与《周易•系辞传》相同或相似。
③孙希旦《礼记集解》引刘氏注曰:“五声之本,本生于黄钟之律,其长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为宫声之数。三分损一以下生徵,徵数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数七十二;商三分损一以下生羽,羽数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角数六十四;角之数三分之不尽一算,其数不行,故生止于五。”又言宫弦八十一丝为最多,其声至浊;商弦用七十二丝,声次浊;角弦用六十四丝,声半清半浊;徵弦用五十四丝,其声清;羽弦用四十八丝为最少,而声至清(见〔清〕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979)。
[1]〔清〕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庞朴.庞朴文集(第一卷)[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3]陆建华.荀子礼乐同构论[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3).
[4]李宏峰.传统礼乐文化的内在张力结构[J].中国音乐学,2007(4).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6]〔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清〕阮元校勘.礼记注疏[M]. 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
[7]〔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8]〔清〕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9]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0]〔清〕刘宝楠.论语正义[M].上海:上海书店,1986.
[11]钱穆.论语新解[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6.
[12]〔清〕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3]〔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经[M]. 上海:上海书店,1986.
[14]〔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清〕阮元校勘.尚书注疏[M]. 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
[15]〔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