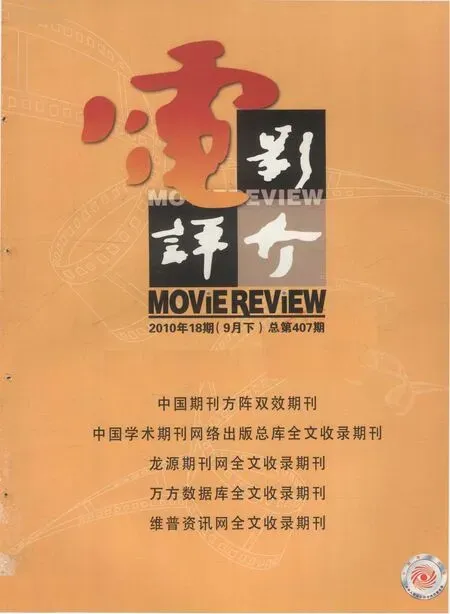指向现实问题的一根刺——浅析《蜗居》的深层隐喻
2009年春季以来,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量价齐升”,与此同时,一部名叫《蜗居》的电视剧也在全国各地陆续热播。该剧根据六六同名小说改编,围绕“借钱筹款买房”这一核心事件,直击当今社会“腐败、二奶、房奴”三大热门话题,播出之初就受到了观众的热烈追捧。据报道:“该剧在各地播出均获得收视冠军。知名影评网站豆瓣网上,超过80%的网友给出了四星以上的高分,网上展开了关于房奴、二奶、贪官的网络大讨论,让人心有戚戚。”[1]但是,《蜗居》引领的年末电视剧收视热潮,也因其剧情的现实映射性和伦理观的非主流化,引发来自各方的争议,甚至质疑。一个电视剧文本,随即演变成年末岁首的文化话题。
有人说,因为2009年中国一线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房价的疯狂上涨,催生了电视剧《蜗居》;而主人公郭海萍、苏淳为一套住房奔波的辛酸生活,以及郭海藻背离初恋情人、沦身为政府官员二奶的故事,似乎又印证了房价快速上扬的社会现实。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实际上,如果看完全剧,我们不难发现,《蜗居》在内容上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家庭伦理剧的范围,其关注的对象也由具体的家庭危机和情感困惑出发,辐射到了对更加广阔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问题的考察。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蜗居》在剥离情感戏的外衣之后,真正呈现给我们的,是一部具有严肃态度和深刻内涵的现实主义作品。而剧中一直存在的“蜗居”情结,在艺术表现上又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它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物象——住房,它还有更为丰富的隐喻内涵,也就是具体物象背后的深层关照。
一、住房的“蜗居”——媒介的隐喻
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是麦克少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这种关系将整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和缩小、着色,并证明着一切存在的理由。[2]
在剧中,“蜗居”的第一层内涵是实体性物象,它具象化为一套住房。可以说,以郭海萍夫妇为代表的“房奴”,已经成为今天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一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该剧将“房奴”的生活作为表现对象,无疑具有了广泛的现实代表性,每个看过此剧的人几乎都曾经发出过类似感慨:在这部电视剧中你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观众不免触景生情获得共鸣,这也是该剧在播出之初就能获得高收视率的原因。
“蜗居”的深层意象是郭氏姐妹以及苏淳、小贝这样的“小人物”为了融入城市,在都市中获得生存的一种符号隐喻,这种隐喻要求观众做积极的、富有想象力的解释和联系。作为一部35集的电视连续剧,《蜗居》非常大胆地使用了二重线索:郭海藻与宋思明的关系发展,郭海萍与苏淳的房子梦想为两条主线;宋思明参与房地产开发项目,谋取非法利益为一条辅线,二条线索交叉推进,在“住房”这个符号的隐喻下,自然而然牵出了情场、官场和商场的多面世界,人物性格也随着情节和事件的演变,逐渐变得丰满起来。
二、身份的“蜗居”——悖论性的角色
吉登斯认为:身份是一种关于我们自己的思考模式,我们对自身的看法会随着时空变化及情景的差异而变化。霍尔认为:人们通过与社会关系中重要他者的文化传达来形成自己的文化建构。社会认同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是别人赋予某个人的属性,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表明一个人是谁的标志。
作为姐姐的郭海萍,也许是剧中性格最为矛盾、最为复杂的人物。她对于海藻周旋于小贝和宋思明两个男人之间的行为,虽然有过劝诫,但实际上,她对海藻的行为是听之任之的,因为她住进了宋思明提供的住房,在丈夫惹上官司后又接受了宋的帮助……所以,有意无意地怂恿了海藻荒诞的“二奶”生活,但是,在剧中我们同样看出,海萍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和追求的人,她敢于臭骂不可理喻的雇主,不怕丢掉养家糊口的工作;希望办一所专门教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中文学校。这种近乎分裂的矛盾性格,让郭海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造成海藻不仅流产了,还失去了做母亲的能力。
除此之外,剧中另一个核心人物:宋思明也有着性格上的悖论化。用妻子的话说,宋思明“不是坏人”,用同事的话说,他“有能力、有口碑、很低调”,用情人海藻的话说,“他是个好男人”。可见,在不同视角下,宋思明给人的感觉的确不是一个“坏人”:他对朋友负责、讲义气,美国人马克把他当成知己,不远万里回到中国,完成他情人出国的重托;他涉足房产,攫取非法财富,却一再叮嘱手下兄弟,不要为难拒绝搬迁的老太太……这么“优秀”的男人,这么“沉稳、讲情义、重感情”的男人,似乎都无法让人把他和一个罪犯、一个包养二奶的人联系起来。虽然宋思明可以在官场与社会上呼风唤雨,可以带着小情人出席同学会,以显示自己的志得意满;但是,在宋思明的内心,却有一张网紧紧罩着他,消耗着他的精神与才智;当他感到自己即将大难临头的时候,有一场与妻子床头对话情节,在这个情节中,宋思明真诚地对妻子吐露了他对普通人平淡生活、渺小身份的向往,宋思明的这种矛盾,就像钱钟书笔下的围城一样,只有进去的人,才知道冲出重围的艰难和无助。
三、心灵的“蜗居”——人生价值的思考
虽然《蜗居》中的一套房子,几乎颠覆了大众文化的传统以及稳定的价值体系;但是,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还有深一层的隐喻,那就是对人生价值的思考。认真率直、本性单纯的小贝,发现女朋友海藻在精神、身体的双重背叛之后,他的精神分裂了:他可以因为爱而容忍海藻的背叛行为,承受一个男人最大的屈辱;但是,心中的挣扎,让小贝抑制不住灵魂的煎熬,最后他在这种煎熬和扭曲中,强暴了海藻,这样疯狂、接近变态的行为进一步促使海藻的负罪感消失了;当小贝独自走出与海藻“蜗居”多年的爱情小屋,从此消逝在茫茫人海时,画面上出现的那个孤独与无助的背影,留给观众一个强烈的文化符号。
看完全剧,不得不让人思考:物质生存压迫的时代,什么才是幸福?对小贝来说“幸福就是筷头上的肉丝”,对宋思明来说,“通往精神的路很多,物质是其中的一种”,对于当初那个青涩的海藻来说,“幸福就是可以吃上一回哈根达斯”,对于房奴海萍来说,“幸福就是拥有一件‘蜗居’般大小的房子”,对于开发商陈福寺来说,“幸福就是拥有更多的地皮和金钱”……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对于精神的追求无疑在逐渐减退,正像剧中海萍对海藻说的“文学就是鱼上的香菜,有鱼香菜才好看。没鱼,一盘香菜你吃得下去吗?”弗洛伊德说,“宗教是人类的心理拐杖”。在这个道德价值严重缺失的时代,很难想象,我们还能靠什么来安顿自己的心灵,不让心灵“蜗居”。很欣赏剧末海萍的一句话,“投机的风险远远要大于投资,投资是只要你坚持物有所值,最终它会增值并硕果累累的,纯粹追求物质不会快乐,脱离精神的物质,也不会快乐”。尽管每个人的心灵在物质化的社会实践中会经历挣扎,但只要有信念,有追求,只要坚持,就一定会比随波逐流行得远,行得正。
剧末,当海藻在经历这一切打击之后,她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记忆里的仍然是当初与初恋情人小贝在雨中相识的情景,让人不免感叹,如果真如纳兰容若写的那样“人生若只如初见”,那该有多好。
[1]白郁虹《〈蜗居〉:房奴的辛酸泪》《精品购物指南》 2009年11月6日。
[2]【美】尼尔.波兹曼 《娱乐致死.童年的消逝》 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