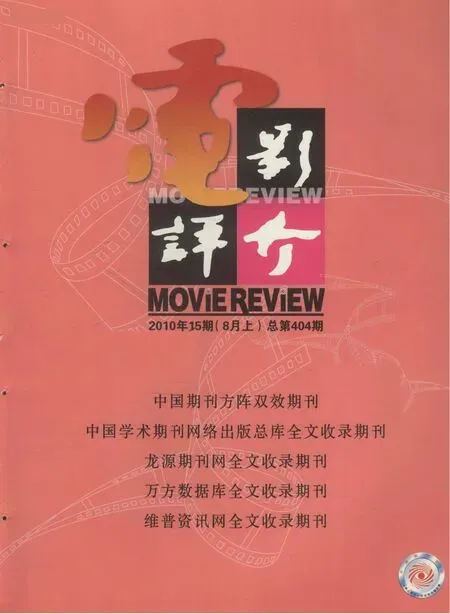浅谈电影中的象征修辞
巴拉兹:“电影艺术的基本信条之一:任何一个画面都不允许有丝毫中性的地方,它必须富有表现力,必须有姿势、有形状。”[1]象征可以为电影带来无尽的深意,成为了影片创作者在表达主题,传达深意时的得力帮手。然而在它竭力地用各种电影天然的元素来负载一个思想,一个涵义和一种可感染大众的瞬间触动时,电影的象征意蕴是否得以清晰的传达,也就是说,观众能像阅读文字一样明白它要表达什么吗?
一、电影语言不同于文学语言
电影的象征修辞不同于文学。尽管象征艺术起源于文学。象征是文学表达法的较高级模式。人们一般认为,词语中意义的生成主要依赖于能指和所指、词与物之间靠习惯形成的约定和我们对之的无条件遵守。象征主义者们的主张是:意义的产生主要是靠语言使用者的主观心理因素,它包括两点:感官的错乱和想象力。
按保罗•德•曼的说法,一个世纪前,“被认为是语言再现和语义功能相统一的表达方式的象征,其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了老生常谈,并且还是文学趣味、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历史的基石。”[2]世界的真实成为了一种想象的真实。它建立于可能性的基础上,强烈地表现于情感的真实。 想象和情感的真实可以说是美学意义上的真实,与科学意义上的真实相对应。在科学中,“真实”就是逻辑的正确,而在诗中,“真实”性是可接受性,是“内在的必然性”或者“恰当性”。因此可以认为,情感大部分时候反映的是我们对事物与我们的某种关系;在强调情感的背后,是对不可见的关系的重视超过对可见的事物的重视。
可见,文学中的象征意义的传递是自适性的。
电影语言的特殊性决定了电影中的象征是富有电影特质的象征。电影用声画“讲话”,银幕画面是电影语言的基本元素,参与画面形象创造的表演、场景、照明、色彩、化装、服装等都在构成特殊的电影语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说白、音响、音乐以其自身并以新的蒙太奇方法——“音响蒙太奇”和“声画蒙太奇”——丰富了电影语言。这间接的表达形式如何负载导演,创作者想要表达的蕴意,并不是靠文字那么简单的。费里尼:“艺术不是做你想做的,而是做你能做的。”[3]电影语言归根结底是具体的,是用声音和画面向我们表达一种态度,一种气势,或是一种情绪。电影艺术并不是简单的实物复制,而是透过镜头的另一个世界。
二、电影象征修辞
莱辛的《拉奥孔》中有这样的一个隐喻:“一个人用钥匙去劈柴,用斧头去开门,不但把钥匙和斧头都弄坏,而且剥夺了他自己再用这些工具的机会。”[4]莱辛的这种以绝对艺术界限为依据的理论,对于在绝对界限的范围内探索艺术家把“缺点”变成“优点”,使界限变成绝对意义上的相对的途径,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意义。电影到底如何运用视听语言来表达象征呢?
首先,负载象征意义的具象物在叙事机制中有意义。
在电影《甜蜜蜜》中的歌曲“甜蜜蜜”首先是男女主人公喜欢的一首流行歌曲的名称;电影《公民凯恩》中,“玫瑰花蕾”首先是凯恩生前念叨的口头禅。我们不能为了象征而在叙事机制之外强加一个具象物来负载意义。这种游离于叙事之外的象征物不仅不会为影片增添新的意蕴和升华,反而会破坏或影响原有的流畅的叙事链条,或让观众陷入疑团。例如,失败的例证中格里非斯的《党同伐异》,其叙事机制是由四个互相独立的小故事构成的:《母与法》、《基督受难》、《巴比伦的陷落》、《圣巴戴罗缪教堂的屠杀》。这四个小故事各自分属不同的时期,不存在着贯穿性的人物,但每个小故事的叙事主题都是党同伐异现象的陈述,每个小故事之间都有一位母亲手摇动摇篮的镜头启承转合。而电影艺术实践证明,这个“婴儿摇篮”的语义功能未能完成,即具象物的象征意蕴无法实现。而《甜蜜蜜》和《公民凯恩》中的具象物不仅承载了叙事机制的表义功能,更重要的是创作的主观意图被观众所接受,使影片升华。
其次,是具象物在叙事过程中得以足够强调。爱森斯坦的《十月》中当冬宫被包围了,我们未看到什么战斗的场面。我们只看到阿芙乐巡洋舰发出的第一炮,紧接着我们就看到宫殿里的华丽的枝形吊灯在晃动。这个镜头充分表现了这个吊灯的富丽的气派,它那千百枝闪闪发光、耀人眼目的水晶,不能不使人联想起皇冠。这显然是沙皇的无上威严的一个象征。但它在晃动了。开始时几乎是难以觉察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来表现使它晃动的原因了。威严的吊灯开始晃动了。当千百枝水晶灯架来回晃动、闪闪发光时,它表现了一种超人的巨大的震动,其中似乎概括地代表了俄国整个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惊慌失措的心情。摄影师基赛选用不再细致的战争场面。吊灯晃动起来了。再没有别的能更扣人心弦了。灯的摆幅度越来越大,天花板出现了裂缝,吊灯的挂钩松动了,裂缝越来越大,接着,这个富丽堂皇、光辉灿烂的精致玩意终于轰然倒地。这里象征的是什么,就不必再说明了。吊灯作为负载象征意义的具象物并不是一个多余的存在,而是我们必然会注意到的,和叙事紧紧相连接的。
1、摄影的各个元素
电影摄影的元素包括胶片本身、构图和照明。其中电影中的构图不同其他任何视觉艺术中的构图,它的关键在于活动。因为没有一个画格跟另一个画格完全一样,影像是在不断变化的,导演和摄影师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掌握它。在结构一个画格时,电影导演的主要目的是把观众的注意吸引到这个场面中,并把它准确地引导到他所需要的地方。没有一个导演会以漫不经心或随随便便的态度来对待画面构图。整部影片的成功往往取决于电影导演在构图上的“眼力”。在贝托卢奇的《巴黎最后的探戈》的“探戈舞”那个段落中,动作发生在舞厅的各个部分,摄影机几乎不停地运动。起初,它跟保罗和琴恩进来,他们穿过大厅,走到一张桌子跟前,注视着跳舞的人。摄影机的运动便和舞曲的节拍相呼应。他们在桌旁简短地交谈了几句之后,摄影机兼用移动的和静止的角度观察着跳舞的人。最后,一对情人离开桌子,再穿过舞厅,摄影机跟拍他们。在整个段落中,摄影机继续着它的缓慢的诱人的运动,从而使画格和观众的视角不断发生变化。运动的摄影机使这个段落显得生气勃勃和富于戏剧性,从而为它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电影音响的各种元素
安东尼奥尼的《奇遇》中的著名的“岛上搜索“这个段落以赏心行乐的调子开始,一群划船的人离船上岸,在一个岩石嶙峋的小岛上闲荡。突然,其中一个女孩失踪了。这个段落的成功之处关键在于当场面的情调发生变化时,海浪击石的声响逐渐增大。我们虽然在银幕上看不到海浪,但我们始终听见一阵阵刺耳的有时使人揪心的浪声。人声时起时落,呼喊着失踪人的名字,在迷茫的音浪中飘浮过来不成片段的对白,结果形成一种几乎是交响乐式的音响效果,对戏剧性动作起着烘托作用,它清楚地刻画出这群人生活内容的空虚,一如不停地轰响着的海浪百无聊赖地拍击着岩石。
还有一种特殊的声音元素是无声。如何用的巧妙和悄无声息会比有声更有感染力呢?例如《邦尼和克来德》中的结尾场面在火枪齐发之前,当邦尼和克来德相互定视时是一片寂静,接着而来的声音的冲击力将会更加强烈,令人震撼。
3、剪辑的合理运用
电影剪辑阶段是电影创作不可缺少的阶段,剪辑在许多方面是一个新开端,是对以前所做的一切的重新整合和估价,它往往控制了电影的时间、节奏和视听觉关系,每一部电影都有独特的内在和外在节拍。实际上,影片的质量和性质在许多方面取决于这些节拍或节奏,内在的和外在节奏的处理可以让电影发生化学性的变化。
来看看费里尼的《八部半》中头一部分即“矿泉疗养地”那个段落。影片描写一个既失去了目标又失去了对自己的艺术的信念的电影导演的生活。剧情发生在他即将开拍一部重要新片的时候,他被许多压力所击倒,他与妻子、剧作家和摄制组的各种其他成员一起来到一个矿泉疗养地。这个段落的目的部分在于以嘲讽的调子来评论意大利上层人士所过的饱食终日、无所事是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使电影主人公导演吉多失去行动能力的那种麻木不仁的状态。这个段落的配乐是贾科莫•罗西尼的《偷东西的喜鹊》中的快板前奏曲。然而,这些场面本身更包含着一种慢吞吞的和无精打采的节奏,它给人一种懒洋洋的、漫无目的的感觉——一种使这个段落具有出色的讽刺特质的情调。摄影机以一种几乎是人为的缓慢速度移动,尽管音乐的速度非常快,但这个段落却给人一种昏睡和死亡的感觉。
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中说道“我们发现,象征一开始时愈是不明显、不生硬、人为的痕迹愈少,它就愈成功、愈有力量。显然,象征手法的各种可能性是根据作品的风格和格调而定的”[5]。
电影从一开始就是技术的产儿,运动的声画影像的基本特征就是具体性。电影的基本技术是照相,被摄物体永远是物质现实,影像永远是物质现实的影像。这种基本特征即具体性不是一种人为的主观认定,而是一种来自基本技术层面的先天性的客观的特征。文学艺术的表现媒体:文字(语言)的基本特性是抽象性,与电影艺术比较,文学艺术永远无法达到电影艺术的直观具体性,而电影艺术则永远达到文学艺术形象在接受主体层面上的自适性。电影艺术的人物形象永远是具体的,他适性的。各门艺术的各自的特点,可能性及不可能性,都是由各自表现媒介的特性所决定的。
注释
[1][匈]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何力译。1986年第2版。第76页第4段。
[2]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3]费里尼访谈录,《看电影》,2005年,第5期
[4]转引自[德]鲁道夫.爱因汉姆〈电影作为艺术,第207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第1版
[5][法]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第1版。 第83页第2段
[1][匈]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何力译。
[2]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3]袁可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下》,中国社会科学院1989年
[4]费里尼访谈录,《看电影》,2005年,第5期
[5]转引自[德]鲁道夫.爱因汉姆〈电影作为艺术,,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第1版
[6][法]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