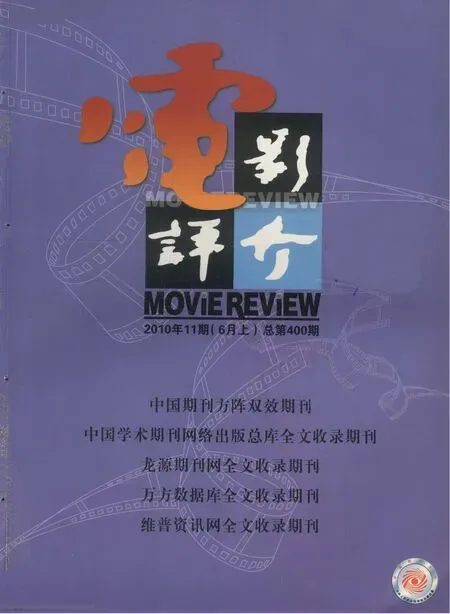余华作品中的圣经文化痕迹
一、用神学意念承载及消解生活的苦难
圣经文化的含义很广,影响也很深远。在这里,我们把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神学意念和神学模式等称为圣经文化。从这个角度说,圣经文化对余华的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余华对圣经文化的了解,喜爱和接纳主要体现在他有意识的阅读文学作品上。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洪治纲说:“阅读的启发在余华的创作中是有决定性的影响。”[1]余华也说:“我一直强调,任何一个作家首先都是一个读者,一个好的读者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这是非常重要的,作家的经验转化为一种分寸的把握使作家在叙述的道路上不迷失方向。”[2]余华不仅阅读《圣经》原著,还迷恋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尔加科夫,福克纳等深受圣经文化影响的世界大师们的作品。余华有意识、有选择地阅读和接受这些含有圣经文化精髓的作品,以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高超的叙述智慧,捕捉大师们在叙述中的细微之处和潜在欲念。圣经文化的精髓便悄悄潜入他的思维中,改变他的创作风格。他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彰显浓厚的圣经文化色彩。
让余华从“小偷”变“大盗”的卡夫卡[3],对余华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余华说他在读卡夫卡的作品时,终于感受到了什么叫做顿悟,——“我读到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部作品,给我终身难忘的印象,就是自由对一个作家是多么重要,小说里有一匹马,他想让那匹马出现,它就出现,他不想让那匹马出现,那匹马就没了。”[4]可以用圣经文化的神迹来形容这种自由之笔。神迹,是一种神学意念,其本质在于超越自然法则,他不被自然法则所理解,所容纳,他作为超自然的力量的结果而发生。在余华的作品中也出现了这样的神迹。余华把这样的神迹赋予到一个个在苦难面前顽强生活的人,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两篇文章中,余华借助“天”、“天命”和“血”等神学意念塑造了两个承受生命苦难而又有着坚韧意志的笼罩神圣光环的人物——富贵和许三观。
1、“天”,“天命”的意念
“天”和“天命”在富贵和许三观的生活中频频出现。类似于圣经文化中经常出现的上帝,具有超自然的能力,也具有人的性格,能洞察一切,主宰一切,来去自由,无处不在,惩恶扬善。
富贵一生面临巨大的变故,他不得不面对至亲至爱的人一个个离自己而去的厄运,先是儿子有庆的突然死亡,接着又是女儿凤霞和妻子家珍的死亡,然后是女婿二喜和外孙子苦根子的死亡。富贵经历与至亲至爱的人生离死别的痛苦,也承受骨肉阴阳分离的孤苦凄清。“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的平平常常……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做人还是平常点好,挣这个那个,挣来挣去赔了自己的命……”[5]富贵最终并没有在厄运面前痛不欲生,而是平静,宽容,豁达的接受这些残酷的事实。在面对如此痛彻心扉的苦难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坦然,豁达和乐观的心态?富贵把一切的厄运和灾难归结到命运,即天命。这个天命是由来无影去无踪的上帝主宰着,普通的人只等着人去承担、面对,去痛苦,去悔恨,去挣扎……在经历了坎坷岁月的富贵,炼铸了顽强生命力,他能洞察这一切,坦然面对和接受这一切。富贵最后用看似纯朴的话语,诠释了人生的大彻大悟,消解了苦难和伤痛,把一切变得自然而平常。
在许三观眼里,始终有个至高无上的“上天”存在,神秘而让人敬畏。
做了坏事不肯承认……老天爷的眼睛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老天爷要想惩罚你了……虽然日子过得穷过得苦,可我身体好,身体就是本钱,老天爷奖我的……[6]
一乐对我好,为什么?也是老天奖我的……[7]
做恶事的话,若不马上改正过来,就要像何小勇一样,遭老天的罚。[8]
老天奖我的,我就是天天卖血,也死不了。我身上的血就是摇钱树,这棵摇钱树,就是 上天给我的。[9]
何小勇再坏,再没良心,也是一个躺在医院里不死不活的人了,你还整天去说他,小心老天爷要罚你了。[10]
许三观相信有个至高无上的上天在窥视着人间的一切。每个人的善恶行为都逃不掉上天的慧眼。人行善能得到上天的褒奖,行恶会遭到惩罚。所以许三观小心翼翼的规范自己的言行,把一切善恶交给上天裁决和奖惩。他的行动充满了神性的色彩,也冲淡了苦难与凄凉的生活境况。
2、“血”的意念
“血”是《圣经》中一重要意象。在《五经》中有关礼仪的法律中,“血”占特殊位置:人血绝不能流,动物的血绝不能吃,而祭祀的血必须在祭坛上作祭祀用。血是圣神的。许三观认为他的“血”是“老天爷奖我的,我就是天天卖血,我也死不了。我身上的血就像一棵摇钱树……是老天爷给我的”。[11]许三观相信命运的安排,相信天意,这就为他的“血”着上了神圣的色彩。神是不可亵渎的,他在每次卖完血之后,都有一个重要的仪式——到胜利饭店吃一盘猪肝和二两温黄酒,这足以表明许三观对血的礼赞,对生命的尊重,对神的崇拜。虽然许三观不得不承受卖血的代价和苦难——他一生中卖过12次血,其中为了筹钱给一乐治病,他连续5次卖血,卖得晕倒,还差点送了性命。但是“血”在许三观的一生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位置,他用卖血的钱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替一乐打伤的方铁匠的儿子付医疗费,为家人在饥荒年代提供一顿美味的面条,“贿赂”二乐的生产队长,给一乐治病。血已成了许三观的万能钥匙,似乎能打开生活中的任何困境之锁。这是作者的神来之笔。许三观在卖血中得到了快乐,他的生命价值在卖血中也得到了体现和升华。这就大大削弱了生活的苦难。
许三观和富贵,都有着鲜活的生命。他们有着耶稣似的苦难,也有耶稣似的战胜苦难的豁达和乐观心态,余华采用圣经文化中的神学意念——天命和血,渲染了神性的力量,承载和消解了生活的苦难。
二、罪与救赎的主题
余华喜欢的另一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是伟大的神圣小说,基本主题是“罪与救赎”这一基督教的根本问题。余华说:“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思的作品,就是《罪与罚》,我被深深的震撼了,我受不了了,很多时间里我都不敢读他的作品。”[12]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余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冲击。
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两部作品,也存在这种“罪与救赎”的模式。即围绕“违约——惩罚——悔过——救赎”的神学观展开。
许三观知道一乐不是他的儿子时,他与一乐相处的九年感情似乎一下子全冷淡了。他几乎视一乐为仇人,“(许三观)心想一乐这杂种竟敢打我儿子,他跑出去,对准一乐的脸就是一巴掌,把一乐掴到墙边。”,[13]当一乐闯祸,砸了方铁匠儿子的脑袋时,许三观要一乐去找他的亲爹何小勇,“你敢不去,不去我揍扁你”[14]他在饥荒年代卖血让家人去吃顿面条,却惟独不让一乐去,“今天这钱是我卖血得来的,这钱来得不容易,这钱是我拿命去换来的,我买了血让你去吃面条,就太便宜那个王八蛋何小勇了。”[15]许三观人性狭隘的缺陷彻底显露了出来。许三观这种唯血缘是亲的狭隘思想是犯了罪的。圣经文化中最担心的罪之一是人的奴役之罪。人的奴役之罪中又包括受血缘家庭的奴役,“家族血缘的过度强调和一味发展将会把人至于奴役的囚笼之中……以血缘关系之亲疏远近为根据来决定人际关系的尊卑贵贱以及对他人的亲属冷暖,必然意味着取消天下人一视同仁的博爱……总之,上帝不容许浓于水的家庭血缘对人的奴役。”[16]犯了罪就要得到救赎,圣经文化强调人类改善的根本途径在于每一个内在人性和个人生命的改变。许三观在卖血的过程中,他的原罪得到救赎。救赎之物就是“血”。“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再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可以赎罪。”[17]一乐病危,需及时治疗,许三观为一乐筹医药费,在去上海的路上一共卖了五次血,差点还送了自己的性命。许三观卖血救一乐这一过程,也表明许三观已把自己狭隘的唯血缘是亲的思想彻底抛弃了,他平等地宽容地接纳了一乐,做到了爱人如己,实现了灵魂的复活。
在《活着》中,富贵同样是一个有着罪孽的人。富贵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他曾经在女人的胸脯上寻找快乐的眼泪,在她们的肩膀上招摇过市、风光无限,在赌场上心旌动摇的体味生命的刺激与冒险,最后还活活的气死了亲爹。富贵触犯了人的懒惰,邪淫和人的自我中心之罪。表现为:好吃懒做,思想涣散,淫邪作乐,只关心自己,不关心他人,处处为个人利益打算,拒绝以谦悲、热爱的态度向他人和世界开放。尽管富贵在父亲的死这件事上受到了灵魂的震撼,开始要“改邪归正”,但是他还是遭到了“上帝的严惩”:与他有着血缘关系的人一个个死去,先是儿子有庆的突然死亡,接着又是女儿凤霞和妻子家珍的死亡,然后是女婿二喜和外孙子苦根子的死亡。面对亲人的生离死别,富贵如同被刀割般悲痛万分。最终富贵只与自己的老牛相依为命,他把这一切都看成是命,唯活着就好。圣经中真正的救赎必须在个体生命内部发生,是心意的转变、精神的重生、灵魂的复活。富贵正是在接受苦难惩罚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灵魂的蜕变,他恢复了善良同情和宽厚的人性品质,并意识到了生命存在的责任和意义,在命运面前学会了宽容,学会了容纳,学会了接受。
余华正是通过了这一“罪与救赎”的主题,使《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人物和故事情节都充满了神性的色彩,从而使这两部作品更加具有震撼力。
科学没有国界,文化也是没有国界的。余华吸纳了圣经文化的精髓,他的作品充满神性的一面,洋溢旺盛的生命力,彰显震撼灵魂的力量。《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被视为当代文坛的经典作品,也正说明人们对这种震撼灵魂的作品的青睐与需求。
注释
[1][2][3][4][12]洪治纲:《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余华:《活着》,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
[6][7][8][9][10][11][13][14][15]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金丽:《圣经与西方文学》,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
[17]罗庆才,黄锡木:《圣经——通识手册》,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