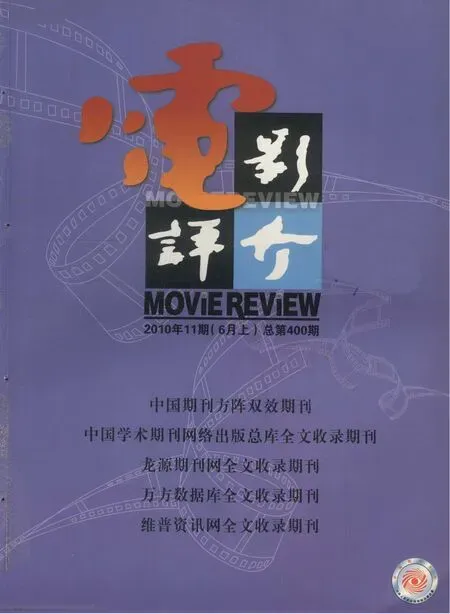《世说新语》中的曹丕形象及其成因浅探
《世说新语》作为志人小说的代表作,无疑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然今人多以此书反映了魏晋时代的真实风貌,不能不说陷入了误区。南齐人敬胤最早为此书作注,此时距《世说新语》成书不过五十年时间,他批评“《世说》苟欲爱奇而不详事理[1]”。传世的刘孝标注距离《世说新语》成书也不过百年,刘孝标在注中多次说“《世说》虚也”,“疑《世说》穿凿也。”[2]自《隋书•经籍志》起,历来官修、私修书目都把《世说新语》置之子部小说家类。《隋书•经籍志》中还有解释:“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3]可见前人早已对《世说新语》的性质有了清晰的认识和定位。《世说新语》是一部刘义庆及其文人集团辑录的小说集,它体现了辑录者的喜好和情感倾向,甚至会和事实不同。
一
《世说新语》中,共有十则故事涉及到曹丕。细而论之,《惑溺》第1则,《尤悔》第1则,《巧艺》第1则,曹丕为故事刻画的主要人物,他的表现是该门标题的注脚;《文学》第66则,《伤逝》第1则,《贤媛》第4则,曹丕为故事的次要人物,即曹丕虽非主要描写人物,但可以体现其性格的侧面;《方正》第2则,《方正》第3则,《言语》第10、11则,虽然故事中出现曹丕,但曹丕只能算一个道具,无任何形象。
从上述诸则故事,我们可大致将曹丕形象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荒淫无耻。《惑溺》第1则:“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联想到后人解《洛神赋》,谓曹植以洛神喻指甄后,甄后绝色,迷倒父子三人,真乃亘古奇观。而曹操、曹丕攻城为甄后,可谓为“冲冠一怒为红颜”典型。曹丕还不仅在这件事上占得曹操的先机,《贤媛》第4则:“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存者。太后曰:‘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崩,亦竟不临。”曹操甫去世,众法师为其招魂,曹丕就迫不及待地将曹操的侍妾据为已有。后曹丕病重,其母卞太后去探望时发现这个秘密,不禁破口大骂。显然卞太后也认为,曹丕的行为已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如此这般,曹丕不仅荒淫,且已到无耻的地步。
(二)歹毒卑鄙。《文学》第66则:“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其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这则故事是“七步诗”的由来,为我们描写曹植捷悟聪颖的同时,也刻画了曹丕残害手足的歹毒性格。《尤悔》第1则:“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閤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这么卑鄙的杀人手段,实在少见,让我们在见识曹丕歹毒的同时,也为曹丕的卑鄙所不齿。
(三)滑稽可笑。《伤逝》第1则:“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哀,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后人多以为此则赞美了曹丕的任诞。其实并非如此,该门第3则,孙子荆悼王武子,同样为作驴鸣,惹得肃穆的灵堂上“宾客皆笑”孙、王二人生活在狂放不羁的西晋,尚且如此,何况建安时期。可见曹丕的行为一定为众人内心所讥笑,只是碍于他的权势,只好照做。《巧艺》第1则:“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戏。文帝于此特妙,用于巾角拂之,无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着葛巾角,低头拂棋,妙逾于帝。”“于此特妙”,可见曹丕的弹棋技艺可称一流,表面看起来,似为正面评价,其实不然。弹棋仅为宫内消遣时光的小游戏。游戏之流,古人常以之为雕虫小技,不值一哂,难登大雅之堂,更不会沉湎于此。身为王胄的曹丕却精通弹棋,实为可笑。
简之,《世说新语》中关涉曹丕的故事无一正面评价,诸故事用鲜明的事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荒淫无耻、凶狠残暴的滑稽之徒,是一个十足的负面形象。
二
然而,《世说新语》是一部早期小说性质的故事集,部分内容带有演绎、虚构的成分。这一点,在曹丕的故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先看《惑溺》第1则,曹操竟声称,攻打邺城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袁熙的妻子甄氏,这恐怕难为历史学家所认同。而父子三人同为甄氏所惑,也令明代的杨慎很不解:“何物一女子致曹氏父子三人争之?”(杨慎《升庵集》)曹操破邺为建安九年,此时正是曹丕、曹植争夺魏王太子最激烈的时候,直到建安十六年,曹丕才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为丞相副,基本奠定了自己在太子争夺中的领先地位。这几年中,为了获得了曹操的青睐,曹丕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直为太子之位而韬光养晦。曹操最后选定曹丕,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曹丕比曹植更谨慎。如果曹操攻邺真为甄氏,曹丕断不会横刀夺父之爱。其实,刘孝标在他的注中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故事的真相,《魏略》、《魏晋世语》、《魏志春秋》三部史书的说法基本相同:曹军破邺,曹丕为先锋,于袁府内室中见甄氏貌美,有意于她,后曹操闻,为纳之。
《贤媛》第1则的荒谬就更明显了,“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丧服小记》注:“后招魂以复魄也,始死以衣招魂曰复。”即人刚死时,持死者衣裙登高,呼魂魄归来。曹操逝世,曹丕没有去想如何顺利登上魏王宝座,而是先想到父亲的那些貌美的侍妾,这实在难以让人相信。《资治通鉴•魏纪一》:“(曹操在洛阳去世),是时太子(曹丕)在邺,(洛阳)军中骚动。群僚欲秘不发丧,谏议大夫贾逵以为事不可秘,乃发丧。…鄢陵侯彰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凶问至邺,太子号哭不已。…时群臣初闻王薨,相聚哭,无复行列。…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从史实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得知,曹操在洛阳逝世,此时曹丕在邺。噩耗传至邺城,曹丕知道,曹操的突然死亡给自己平稳登上权力巅峰增添了很多变数,兄弟之中,曹植、曹彰都对自己构成一定的威胁。此时此刻,如何收拢人心,顺利即位才是最关键的,至于接收曹操的侍妾,纵然有,也是一段时间以后的事情。
《尤悔》第1则里写曹丕在母子三人团聚的时候用毒枣毒杀了曹彰,也有明显的虚构成分。曹彰在曹操去世时显露异志,为曹丕所忌恨是肯定的。再加上正史 “(曹彰)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的说法语焉不详,就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猜测。我们无法考证曹彰究竟是病死还是为曹丕所杀,但至少不是《世说》所描写的这样。叶嘉莹先生指出,黄初四年,诸王来朝的时间为农历五月,此时枣子还未熟,用枣子毒杀曹彰是不可能的,文帝约束诸王的办法还不至于要采用这种方式,曹彰是得了暴疾而死。[4]余嘉锡先生认为:“盖彰之暴卒,固为丕所杀,…世俗遂因其事而增饰之耳。”[5]刘孝标引用了吴人孙盛所作的《魏晋世语》给另外一个解释:“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得见,有此忿惧而暴薨。”
其余数则中,《文学》第66则的“七步诗”,其真伪历来就争论不休。《伤逝》第1则,刘辰翁、凌濛初对此提出疑问,认为其中杂有小说家之虚构想象。[6]
曹丕之形象,固然可以见仁见智,但纵观《世说新语》全书,无一正面评价,尤其是多处不实描写,更是给人留下曹丕过于荒淫歹毒的印象,不能不说是辑录者有意为之。
三
曹丕个人形象,历史上褒贬不一,总体来说负面评价居多。除却个人性格和历史功绩,曹丕无疑还背负着两个历史包袱:一为民间长期的“褒刘贬曹”倾向,曹丕作为曹操的继承人和曹氏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理所当然也会受到一些贬低;一为首开假禅让真篡位之先河,后代诸多权臣依仗曹丕之发明登上大位,但他们绝不会去抬高曹氏的历史地位,反而会丑化篡位者形象,严防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这样,从统治阶级到下层百姓,都乐于看到曹丕卑劣行径的故事。
曹氏集团被后人诋毁,还有其个人性格的原因。曹操奸诈,好用酷刑,曹丕气狭,外宽内忌,兄弟阋于墙内。这其中多少会有后人演绎的虚假成分,但他们的性格恰好与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背道而驰,所以就有了文人们将他们作为反面教材的机会。
曹氏集团的功过是非千百年来沉沉浮浮,每个朝代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取舍评价。西晋禅魏而来,奉魏为正统,以显示自己政权来源的合法性,故对曹氏父子评价较高,陈寿《三国志》、王沈《魏书》对曹氏父子颇多褒誉之词。从东晋开始,史家文人开始对曹氏之过加以非议,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就认为曹操父子以魏承汉是篡逆之行,晋宜越魏继汉。其原因是东晋偏居江南,仍然要自封正统,只好像蜀国那样,贬低曹魏的正统。刘义庆生活的南朝宋代,直接承东晋而来,版图亦与东晋相去不远,再加上刘义庆身为王室贵胄,贬低曹魏的正统可以想见。
刘义庆等人刻意贬低曹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南朝宋刘氏乃是汉朝宗室之后。《宋书》、《南史》均著宋武帝刘裕为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之二十一世孙,《宋书•本纪第一》还将从刘交至刘裕的二十一世的名字列出,显示了刘氏对汉宗室血统的看重和宣扬。不仅如此,史书还处处渲染这一点,以显示宋代晋的正当性。《宋书•列传二十一》、《资治通鉴•元熙元年》均有:“高祖(刘裕)将还,三秦父老诣门流涕曰:‘残民不沾王化(指汉灭亡),于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数千间,是公家屋宅,舍此欲何之?’”
注释
[1]宋•汪藻《世说叙录》之考异录《尤悔》4•敬胤语
[2]《言语》第22则、《雅量》第40则,《品藻》第19则等等
[3]魏征《隋书》中华书局
[4]《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186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5]《世说新语笺疏》1049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6]刘强《世说新语会评》368页,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1]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2]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3]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4]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6]王根林《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7]张作耀《曹操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