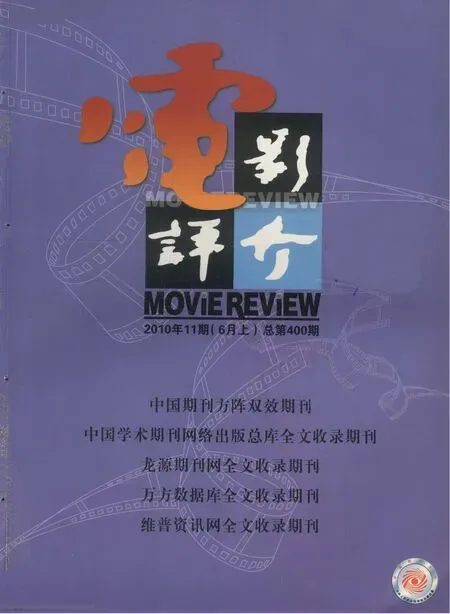浅析齐鲁电视台《拉呱》节目的成功因素
一、小众窄播——定位本土化
正确的市场定位是一个商品成功打入市场并得到肯定和回报的关键,对栏目推广和市场回报率至关重要。定位是一种逆向思维方式,不是以自己而以受众心理需求为出发点。方言电视节目将受众人群定位于本方言区的观众,走“小众窄播”的道路。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大众传媒对地域文化构成了不小冲击,文化产品的“麦当劳化”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由于第三次浪潮赫然来临,群体化传播工具不但没有扩大,反而突然被迫削弱了,它在很多战线上,正在被称之谓“非群体化的传播工具”所击退。[1]非群体化倾向使传媒日益认识到针对特定受众群体进行个性化传播的重要性,即用窄播符码来吸引有限的受众。上海大学中文系钱乃荣教授认为,“方言里有比普通话丰富得多的生活、情感用语,在动作的细微区分、事物的性状描绘等方面都更具体”[2]。不同于央视放眼世界、雄霸中国的气势,也迥异于省级卫视抢占全国收视份额的野心,《拉呱》致力于本地居民,用乡音进行交流,语气亲切,富于生活气息,使当地居民成为忠实的观众。这是对抗中央电视台和省级卫星台的强势话语权和资源优势,谋求自我生存、发展之路的有效探索。
《拉呱》的本土化定位,首先语言的亲近感是拉近心理距离的一种有效方法,从传播学上看是大众传播向人际传播的转化。由于规模缩小,更利于情感传递,因此《拉呱》在传播过程中,无论在物理距离上还是在心理距离上都更容易为百姓所接受。
二、内容为王——“三贴近”原则
方言新闻是大众传媒对民生新闻内涵的拓展,其本质是内容“民生”,体现了当今时代新闻所必须的平民精神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归结为平民视角、民生内容、平民取向。具体来说,即新闻传播者的姿态、话语方式不再是居高临下,而是与普通民众平等;新闻报道聚焦于普通民众的生计和生存,以人为本,尤其注重关爱弱势群体。
《拉呱》节目内容上十分丰富,每天平均六七条的新闻虽然都是家长里短,但是内容极为丰富,各类民事纠纷、奇闻趣事、民风民俗、公益道德等几乎无所不包。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这个角度讲,《拉呱》是主旋律节目,而且符合“后院篱笆原则”。针对节目中形形色色的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记者不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报道他们的苦恼和争吵,而是以亲历者的身份帮助排解纷争。例如2010年2月23日一则消息《大婶儿成了花脸猫 到底拜谁所赐?》,除了体现婆媳之间的冲突,记者还跟随帮助解决问题。可以说,在内容为王的时代,节目一直践行齐鲁台台长闫爱华在全国曲艺式新闻研讨会上所说:“我们现在天天号召体验生活,提倡曲艺演员要下去、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并运用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语言载体,与普通老百姓的精神生活保持零距离,体现出麦奎尔等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中心绪转换(division)作用,即电视节目可以提供消遣和娱乐,帮助人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
三、特色优势
(一)、万里绿中一点红——曲艺化锦上添花
用方言口语“说新闻”的形式使新闻节目传播更富生动性、浅显性、形象性,使节目内容更能为观众所接受。曲艺的运用则锦上添花,使节目朗朗上口、声声入耳,因此会收到语到意到、口传心受、心领神会的直接效果。
2006年10月14日召开全国曲艺式新闻研讨会,著名艺人姜昆指出,《拉呱》节目突破了传统的新闻模式,打造了一个新闻模式的品牌,他认为《拉呱》作为方言曲艺式新闻离开了曲艺的舞台,但回归了曲艺的本质。齐鲁电视台台长闰爱华也指出,新闻是最严肃的电视节目,而曲艺是最诙谐、最轻松的电视节目,《拉呱》是“曲艺式新闻”,是两极嫁接的典范。节目广泛运用快板、评书、相声等百姓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融入娱乐性、趣味性元素,大大增强了节目的可看性。曾经,一段山东快书版的开场白,着实吸引了很多观众。“咱们拉呱节目真有趣,拉的全是新鲜事;越拉越觉得有意思,越拉心里越带劲;您要是有什么新鲜事,给咱节目送个信,记者马上到家门;咱们有批评有鞭策,让大伙说说对与错,不是给您出难题,咱们是对事不对人。”不少观众在观看时,也不由得随着山东快书的节拍一起把这段开场白说了出来。
(二)、个性化的主持风格
“小么哥”已经成为《拉呱》节目的形象代言人,相声演员出身的张勇,貌不惊人,一张表情丰富幽默的脸还带点“嬉皮笑脸”,一改传统新闻节目主持人正襟危坐,演播室里一架屏风,一堵隔墙,一张书桌,主持人在桌后一站,很有现场说书的味道,拉近了新闻与受众的距离。他对新闻的串联、点评更是信手拈来,举重若轻,把曲艺的娱乐性和新闻点评的道德教化相结合,用他的语言方式,教给老百姓如何尊老爱幼,如何与朋友相处,如何在社会上处事等,把教化用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亦庄亦谐、寓教于乐。
“搭词儿的”总是一个与小么哥唱反调的“捣蛋鬼”形象,喜欢在“一本正经”的小么哥说的兴起时冷不丁插上一句,不管是机灵古怪的张帆,还是魁梧憨实的鄢磊,甚至黄渤、沙僧刘立刚等演员的客串,主持人与搭词儿的一唱一和,完成节目的串联,既有效地衔接起了新闻之间所造成的“中断”,为新闻故事的开始和结束牵线搭桥,确保节目的流畅性,同时主持中的表演因素,使节目陡生悬念,高潮迭起,妙趣横生。一方面让节目变得轻松愉悦,另外也变相地宣传了主持人和节目,有助于提升节目的知名度。
(三)、“闭门造星”、“借势造势”
齐鲁电视台充分发挥资源整合的优势,给主持人发挥才能提供广阔的空间。机制的放活使各类主持人在多种场合频频露脸,形成良好的互动。新闻节目主持人在综艺舞台上彪歌亮舞与民同乐,娱乐节目主持人也在新闻节目中客串,玩得不亦乐乎,在近乎于“自娱自乐”的过程中“偷”走了观众的心。它聪明地利用自己的平台塑造自己的平民明星,再相互利用各主持人的明星效应来吸纳更多受众,齐鲁台大处着眼“闭门造星”,各小节目则在“借势造势”进行一场场造星运动。
《拉呱》节目内部的造星除了小么哥这一极具喜剧色彩的主持人常秀看家本领外外,还提高“搭词儿的”出镜率,尽情展现助理主持人的才艺,用鄢磊和张帆两位助理主持的姓名音译板块——《雷翻天》,添加了主持人的表演。如:张帆:我男朋友特别厉害,他爸爸是个市长,舅舅是公安局的局长,叔叔是粮食所的所长。鄢磊:啊?那、那这四个人你想好选哪一个了吗?主持人古灵精怪讽刺恶搞的表演让受众在笑声不断中记住了这两个人。虎年伊始,《拉呱》节目曾出新招——借花献佛来增添节目人气。台内四小花旦、小侠女王熹、天气预报主持人等纷纷在《拉呱》节目中下了厨房。都说“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平日在节目中游刃有余的当家主持在厨房里却又舞又叫甘拜下风,博得观众一笑,为《拉呱》赢得更多人气,提高了节目的收视率。
(四)、互动中“收买人心”
随着通讯科技的发展,观众可以与节目的互动形成一个良性的沟通。很多新闻节目都设有热线电话、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等互动环节,观众通过这些途径,除了可以向节目提供新闻线索以外,还可以就当前播出的话题发表个人意见,打破传统新闻传播单一的传受途径,形成多维的互动方式。这种大众传播由此具有人际传播的交互性,同时能够让观众找到自己的“收视位置”,从而提高收视兴趣和积极性。[3]
《拉呱》节目设有热线电话,在播出过程中主持人与观众通过网上短信平台在线交流,“短信抽奖”将带有小么哥头像的茶具回馈给观众朋友,送奖小组经常深入百姓交流提问,观众往往或满载而归或赢得大奖,例如爱心蚊帐、印有主持人头像的伞具等,培养出长期稳定的受众。除此之外,节目主持人走向各地义演、做爱心宣传大使、消防宣传大使等始终活跃在各样的舞台和观众的视线中,在良好的互动循环中“收买”了人心。正如闰爱华台长总结出该台特有的“三民主义”,新闻节目体现民意,电视剧体现民乐,娱乐节目体现民秀,我们的口号是打造我们自己的互动节目。
四、《拉呱》节目存在的问题
不可否认,方言在表情达意上有时的确胜于普通话,因此也更容易在同属于这种方言文化圈的对话双方建立起认同感,但是当电视荧屏到处都充斥着操着方言的节目时,也暴露出明显问题。
(一)表象背后是衰落 ——谁为国民素质提升买单
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曼均指出,方言节目其实是以其“离谱”和另类、平民化和娱乐性、搞笑与原生态,借助现代传媒“复兴”。节目中的方言,很多都是“市井化的调味品”,并不承载地域文化特色,实际上表明了方言的衰落。乡土文化来自于民间,其文化创作中的内容必然会带有一些审美低俗、格调不高的缺点,对这些内容进行大范围的传播,可能不利于整个国民素质的提升。另一方面,乡土文化的过度风行,也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拉呱》节目也必当“一如既往地关注人的命运, 关注人的生存情态, 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 是生命力和影响力得以延续和扩大的主要途径[4]。
(二)、同质化节目泛滥,受众审美疲劳
由于方言类电视新闻节目的高收视率带来了巨大商机。商业利益的驱使,致使各地方电视台不顾自身实际,对节目进行缺乏创意的挪借,导致同质化现象异常严重,终究会导致观众的审美疲劳。就《拉呱》节目本身而言,内容的同质化现象频频出现,例如在2010年春节前后两周的节目中,仅关于婴儿被弃的内容就有四起,主持人小么哥的点评也是归于一句“你看看这样的事情最近报道了多少次了,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试想受众总是被这样同质化的内容充斥眼球,最后难免也会“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结语
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为满足不同受众或特殊观众的需求,用方言说新闻为方言区的地方文化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为当地观众提供了一次身份认同的机会。《拉呱》节目顺应了小众化传播的潮流,展现了在激烈的媒体竞争环境下差异化竞争的实力,丰富了荧屏内容。对发展中的问题,加强规范和引导,合理配置方言资源,不断完善其传播的形式和内容,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阿尔文•托夫勒.大众传播与广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7页
[2]httP://www.ehinanews.eom.en/news/2004year/Zoo4-08-19/26/4742oss.html
[3]任远 兰岚.解释《第一时间》栏目[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7期
[4]刘晓红 卜卫.大众传播心理研究[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