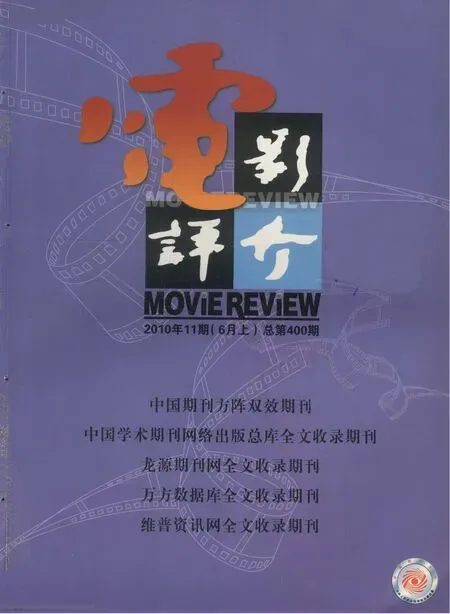何平电影的迷失——从电影《天地英雄》和《麦田》谈起
重庆大学电影学院 漆一枝
何平电影的迷失
——从电影《天地英雄》和《麦田》谈起
重庆大学电影学院 漆一枝
虽然何平导演的电影开创了中国武侠电影的一个新流派,但从《天地英雄》到《麦田》可以看出,在电影结构和故事情节上存在着简单化、概念化的不足,从矛盾冲突的选择到人物性格的刻画,导演忽视了某些艺术创作规律和生活基础,致使两部电影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困境和迷失之中。
观念化 矛盾冲突 故事情节 人物性格
何平导演是中国当代电影史上很具个人风格的导演之一,他的作品《双旗镇刀客》开启了武侠电影的一个新流派,赢得了许多荣誉和奖项。但从导演近几年拍摄的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电影的结构和故事上,存在着一些简单化和概念化的倾向。
《天地英雄》和《麦田》两部影片将目光投向了乱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乱世,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对社会、自然和人类造成了很大的灾难,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程。导演选择将故事放在“乱世”这一背景中,可想而知,必然是有着强烈的情感诉说和渴求太平盛世的非同一般的看法。这一背景有戏可写,有戏可挖。但同样毋庸置疑也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命题太大,背景太广,如何选择一个恰到好处的切入口来展开生动的而不是概念化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如何来构建一个精彩的、具有创新思维的独特的“这一个”艺术世界就成为导演首先面临的难题。
电影《天地英雄》拍摄于2003年,这是一部酝酿了15年的作品。故事讲述的是:公元七百年前,丝绸之路上,唐朝的驼队正运送释迦摩尼的舍利回长安。释迦摩尼是佛教徒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电影中讲到,拥有舍利就可以统治西域大大小小的36个佛国,突厥人和响马头子都想获得它,遣唐使者来栖和他一直追捕的朝廷钦犯校尉李不经意陷入这场佛骨争夺战。故事围绕着“护送舍利”和“抢夺舍利”这一对矛盾展开,以遣唐使来栖和校尉李的纠葛为副线,最后以这对生死冤家联手“把舍利平安地送回长安”作为结局。
《麦田》拍摄于2009年,描写的是两个逃兵暇和辄被军队追杀,亡命途中却被赵国妇女们所救,而且被当成是赵国武遂的英雄,受到留守老弱妇孺的顶礼膜拜与热情照顾。此二人只好胡吹一气,不料山贼入侵,带来赵国已败的真相,戳穿了他们的一派谎言。于是故事由喜转悲,因为剧情的发展全在观众的意料之中,故而显得平淡无奇。
纵观以上两部大片的剧情梗概,我们可以看出,何平导演选择的题材往往具有与众不同之处,要故事有故事,要人物有人物,要冲突有冲突,要画面有画面,要异域风光有异域风光……绝对是一个非常讲究光线、色彩的造型艺术大师,而且不似他同辈那些知名导演那样娇饰虚夸、以炫技惑人,他的表达以真实生活中瑰丽、壮伟而又自然朴拙的美感取胜。然而这样一位真正下功夫的艺术家,却非常遗憾地没有引起更多的观众对他的关注,他的电影作品也没有达到应达到的艺术高度,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种不温不火的局面?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去探讨。
首先,两部影片矛盾冲突的选择,存在有一种“观念化”的影响。
虽然就影片而论,导演不遗余力地描绘了大自然最原始、最壮美的生态风光,展现了撼人心魄的、宏阔的异域风情(战国时期的赵国,相对于今人而言,也是一种异域风情),镜头剪辑清晰流畅,节奏处理张弛有致,场景拍摄无比大气,让人情不自禁拍手叫好。但影片的基础却建立在一种观念化的理解之上。《天地英雄》围绕着佛骨舍利的护送与劫夺展开,两路人马争夺与厮杀。一路是以安大人为首的响马,以及背后支持响马的西突厥国的可汗势力,一路则是以屠城校尉李和遣唐使来栖大人为首的护法队伍。对这场争夺和厮杀所设置的障碍,无非是一方人多势众,一方缺水断粮。唯一的噱头就是校尉李与来栖之间还存在一层追捕与被追捕的关系,但这层关系形不成故事真正的张力,无力支撑大众的观赏兴趣,三两回合下来,就被这二人“同仇敌忾”所达成的一个类似于契约式的口头许诺而轻易化解。这种“观念化”的表达,使曾经被追捕的一群弟兄,加上当地群众的代表人物“老不死的”和流浪无居的小小少年,迅速地结成了所谓的在“正义”、“爱国”的旗帜下的“统一战线”,豪气冲天,全力以赴共同对敌。这样的矛盾设置,简单而又概念化,一波又一波地打来杀去,使影片很难引人入胜。
而《麦田》这部影片的矛盾冲突设置,在观念化思想的指导下,表现得更加简单化。选择战胜国秦国的两个逃兵展开叙事,无非是想表达战争对所有的百姓而言都是一场沉重的灾难。想回家参加收麦而不可得,只好选择冒着杀头的危险逃亡。但这并非是整部剧情的叙事线索,它在电影中只是一个“由头”,一种叙述角度,严格来说,只能是一个“引子”,引出赵国那一群身着类似古希腊妇女服装的潞邑城女性,对前往战场“保家卫国”抵御秦兵入侵的包括城主剧葱大人在内的男人的热切思盼。正是这种热情似火的、近于集体疯狂的对自家男人的期盼,构成了影片中“以喜写悲”的艺术特征:两个逃兵阴差阳错进入了赵国潞邑城,为了活命,被迫说谎冒充赵国人,并且胡诌赵国军队打败了秦国军队,潞邑城的妇女们由此“庆祝胜利”,由此欢欣鼓舞,将此二人视为“英雄”,加以膜拜。也就是说,《麦田》的矛盾的确立,乃是以一场天大的“误会”来结构全篇,是以对战争的胜负来表达包括城主骊夫人在内的全城妇女的大悲大喜,看似热闹非凡,似乎充满了荒唐与笑料,实则这种虚假的矛盾设置,无论谁胜谁负,同样都伤害了影片最初的立意。更重要的是,使影片变得概念化。如果我们将一部影片的矛盾冲突,建立在一个纯系民间式的小笑话上面,建立在一种观念化的认知上面,我们就很难撑起一部大片的叙事的坚实基础。
第二,剧中主要人物的塑造难以获得观众的情感与心理认同。
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周涌教授在《影视剧人物塑造的基本方法》一书中写到:“电影中的人物是观众欣赏电影的一个窗口,观众认同电影中的人物,亦会对电影产生强大的认同感。反之则相反。所以在塑造电影人物时,要让观众同情你的人物,认同你的人物,才会对他的命运产生深切的关注与共鸣。”这里涉及的仍然是一个影视剧作的常识,影视作品必须以观众的心理需求与情感满足为目的,中外无数优秀的影片反复向我们证实了此为亘古不破的真理。毫无疑问,何平导演也注意到了这点,比如《麦田》中两个逃兵性格差异的喜剧性对比描写,对《天地英雄》中姜文所饰演的校尉李的血性、隐忍、为他人着想的善良品性的描绘,对“老不死”立地插刀泉水喷涌而出的神来之笔的刻画等,都一一给观众留下了精彩难忘的印象。
但为什么我们仍然感到不满意?仍然认为影片中的人物显得苍白概念化,显得不丰满?仍然难以打动我们的情感?
有两点可以提出来跟何平导演商榷:其一,《麦田》中的逃兵暇和辄看似融入了潞邑城,但是他们并没有和城内任何一个女人产生情感纠葛,而潞邑的女人们与这两个秦国的逃兵之间也没任何“故事”发生,除了那些浮光掠影的荒唐打闹,几乎完全没有因人物关系而搭建起来的爱恨情仇的展示。这样的影片其看点何在?似乎观众唯一可做的,就是等着山贼前来戳破这两个秦国人的谎言。这种表达未免太“小儿科”,即使给了范冰冰饰演的骊夫人再多的镜头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位美丽的城主夫人并未卷入人物纠葛之中,在她眼里只存在一个真假判断,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事非判断,所以当秦兵杀来,暇用马车载着她准备逃走时,她毅然从马车上跳下,不愿苟且偷生,而要与潞邑城共存亡。然而这位骊夫人被刻画得如此单薄,所传递出的感情又如此单一,自然成了一个性格平面化的人物,观众势必不为所动,并没有如导演所预期的那样,这的确值得编导深思。《天地英雄》中的人物关系设置,前面已经说过,因为只有泾渭分明的敌我关系,并无相互交叉的人物关系和人物情感,因而也就很难激起观众心底的波澜。而影片中唯一出现的一位花瓶式女性,虽然她的身份是将军的女儿,但毫无作为,仅是一个“旁观者”,一个“随行者”,并未卷入人物关系纠葛之中,只是一个“自己人”罢了,而且她还装作和校尉李互不“认识”。赵薇饰演的这个角色,担任了影片的第一人称叙述人,实际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所以,当文珠与校尉李最终将舍利送达长安,在影片结尾时,她对校尉李说:“我跟你走”。观众甚至还会感到惊讶,这话从何说起?影片在此之前,对这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安排与此相应的任何矛盾纠葛,原本就无悬念,观众当然对他们的这种去向表达显得不知所措,难以产生情感认同。
其二,人物性格的描写几乎都有概念化的毛病。这个问题跟前一个问题紧密相联,或者说是前一个问题的必然结果。正如上面所说,导演对西部影片中的主要人物性格刻画确实花了不少笔墨,如校尉李的形象塑造,既有西部硬汉的一面,还有侠骨柔情的一面,对骊夫人的描写,既描写了她身为贵妇人端庄的一面,也写了她与普通女性亲和的一面。然而影片能够达到的艺术追求,仅此而已。校尉李之所以成为钦犯,是因为他违命不杀无辜的群众;他之所以参加驼队护送舍利,开始是出于报恩,因为驼队的护卫在沙尘暴袭来之时伸手搭救了他,后来也许是发现护送的是释迦牟尼的舍利,为了维护大唐,为了民族的利益而义无反顾。骊夫人的丈夫剧葱大人则是新婚燕尔,响应王命而赴战场杀敌,留下的骊夫人义不容辞地担任起潞邑城主的职责,以稳定妇女们躁动的情绪,等待男人凯旋而归——这些属于“大义”的表现尽人皆知,少了艺术家的独特“发现”,很难让观众感到震撼。大义者,大道理也,表现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怎么让它变得感人,怎么让人物经历九死一生的重重考验,而不是只有不断的打打杀杀,这对于任何一位创作者来说,都是难以回避而必须解决的问题。何平导演在自己的电影创作中,就遇上了这样的瓶颈,这是他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否则一部接一部地拍下去,老是停留在讲“大道理”上,就限制了向生活深处的开掘。记得恩格斯说过一句名言:作家艺术家必须把自己的倾向性隐蔽起来,而且是隐蔽得越深越好。往哪儿隐蔽?往人物与情节背后隐蔽。不知何平导演以为然否?
第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该从何处着力下手?
这是我国电影创作所遭遇的一个老问题,一个人人皆知可是迄今尚未很好解决的老问题。电影人可能最不喜欢讨论这个问题,认为讲故事太俗,层次太低,艺术家讲究的是光线、画面与造型。我想说的是,艺术家追求电影的艺术表现形式并没有错,因为电影如果没有自己的艺术特色,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自然也不存在了。但问题又出在这里:光线啊,画面啊,造型啊……这些东西其实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载体,虽然它们能够表达一定的意义,但它们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适应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我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否认电影所具有的独特艺术表现形式,我只是想说,电影既然是一种艺术,而且被称作“第七艺术”,它就应当而且必须具有所有艺术存在的一种“共性”: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是人类的一种精神产品。导演所创作的影片是供别人欣赏的而绝对不是个人把玩的、准备束之于高阁的“文物”,这就需要它像别的叙事作品一样,必须具有戏剧性,必须具有悬念,必须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并且故事情节还必须先于造型手段而存在。这样的话题不管我们的电影人乐不乐意听,他们都应该听下去且深思之。
这两部电影作品,当然不存在对故事情节的排斥,但故事讲得不够好,讲得很单调,不能很好地吸引观众,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两个故事讲得都一般化,没有讲出它们各自独特的魅力,没有讲出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没有讲出故事的真正精髓。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不仅要从剧作上,更要从导演本人身上去找,因为两部电影都是导演本人选定的剧本,同时导演还参与了剧本写作。以《天地英雄》为例,导演醉心于某种神秘文化,以为谁将佛祖舍利搞到手,谁就能控制西域36个佛国,这对唐朝的历史来说,是戏说而非正说。唐朝推崇佛教文化诚然是一个事实,可释迦牟尼乃天竺国(今印度)人士,为什么必须由大唐占有佛祖舍利才算皈依正宗,别人来夺取就是坏人。这个“理由”影片完全缺少交代,接着却突然来了一个魔幻处理,让佛祖舍利显灵,罩天罩地的灵光一闪,奇迹出现了:大唐护法的英雄们不战而胜,可以御敌解围,可以让死去的小沙弥起死回生。编导以为观众定然会喜欢无疑,殊不知这样一来,适得其反,影片原本就是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影片,并非魔幻片,编导心血来潮来这么一手,风格的完整性瞬间就被突兀地破坏掉了。观众反而觉得这部影片在故弄玄虚,瞎编乱造。
故事情节要引人入胜,一是要合情合理,二是要具有独创性,三是要有人文性的普世价值。如果我们把着力点用在编造离奇的故事上,或者用在观念化的层面上,纵使辛苦地进行概念化的演绎,这样的电影很难获得观众的认同。
情节不能离开故事,两者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所以情节上的困境,归根结底在于导演对创作规律的忽视。殊不知造型画面及武打技巧,统统不过是载体而已,如果故事、人物、情节的基础打得不牢固,不结实,自然是事倍功半,收效甚微。
结语
从何平导演的电影中,我们能够看到其立意的深刻,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两部电影取得的成绩,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故事本身的生命力,只有具有生命力的影片,才能够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赢得观众的喜爱。
[1]宋法刚 《突围•回家•民族主义——对<天地英雄>的三重解读》 电影评介2007.03
[2]付宇 《优质导演的摇摆创作——评析电影<麦田>的导演创作》 电影艺术 2009.06
[3]李彦 《何平“天地”纵横谈》 大众电影2003.01
10.3969/j.issn.1002-6916.2010.11.016
漆一枝(1989—),女,湖南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大学电影学院本科生,戏剧影视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