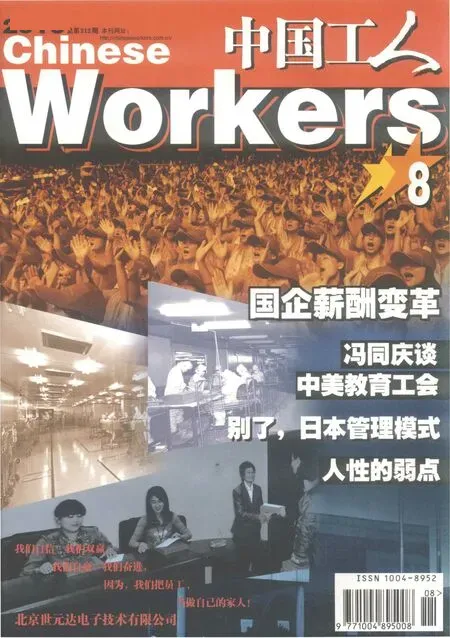人性的弱点
段 炼
人性的弱点
段 炼
人际“汽泡”
近十多年来,由于西方文化的潜移默化,国人对“个人空间”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对“私人事务”越来越尊重,这与过去只强调公共性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成反差。记得早在1980年代中期,我刚到四川大学执教,有次在课堂上讲起“个人空间”和“私人事务”问题,我说这个术语在英文中就是“隐私”。有个学生蹭地一下站起来问:“老师,你有隐私吗?”那年头“隐私”是个见不得人的坏词,猛听此问,我猝不及防,几乎语无伦次,为免自相矛盾,只好结结巴巴地说:“当然,有。”结果,教室里传出一片窃窃私语,学生们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我,个别同学则露出同情的目光。
其实,个人空间和私人事务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而且也是心理和生理的现象。过去我有个邻居,搞音乐的,每到半夜总要练琴,让我无法入睡。平心而论,那乐声并不难听,但我在半夜不需要听,那声音只能让我心烦意乱。我忍无可忍,往邻居门上贴了个条子:夜深人静,请勿扰邻。
可是,我并不真的怕噪音,反倒常常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昏然入睡,电视的声音竟成了催眠曲。有次同一个研究心理学的朋友说起这怪事,他哈哈大笑:这可不是怪事,太正常了,每个人都生存于自己的“汽泡”(bubble)里,不容他人入侵或过于靠近,邻居的音乐声入侵了你的“汽泡”,而电视的声音是你自己弄出来的,不论多嘈杂,都不存在入侵问题。换言之,这不是一个噪音问题,而是一个入侵“汽泡”的问题。朋友这样一说,我才想起,半夜时分远处大街上的汽车声,比邻居的音乐还吵闹,但因远在我的“汽泡”之外,没有入侵之虞,所以我照样呼呼大睡。
这“汽泡”便是“个人空间”,这空间里的一切都是“私人事务”,即所谓“隐私”,容不得他人干扰,北宋皇帝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是之谓。人每行一处,都要给自己画出一个看不见的心理和生理空间,就像小猫小狗到处撒尿,圈定自己的领土,宣示自己的主权。
若要确认个人空间,最好是借助对比而在公共空间进行求证。有位心理学家在医院做了这样一个实验性观察:在候诊室里放一张长座椅,可供五人坐。第一个病人进了候诊室,领了排队号码,然后毫不犹豫坐在了长椅的2/5位置上。接着第二个病人进来,取了号码,坐在了椅子的另一头。这时,工作人员往候诊室摆放了第二张长条椅,第三个病人进来时,他环顾一周,坐在了第二张长椅上,尽管此时第一张长椅上还有三个空座。显然,这三个人都本能地与别人保持距离,既尊重他人的空间,也求取自己的空间。可是,随后进入候诊室的病人越来越多,个人空间越来越小,人们只好一个挨一个地挤着坐下。个人空间的压缩,会引起人际冲突,最好的例子便是公共汽车或地铁里乘客争抢座位,或因肢体碰撞而发生冲突。
上述心理观察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我相信,尊重“汽泡”是人的本能,唯在空间不够的情况下,“汽泡”才被别人入侵。但是,有些人对“汽泡”全无意识,会不自觉地入侵他人“汽泡”,这时,我们该怎样回应?
有个周末我去成都郊外古镇洛带一游,中午到一家小饭馆吃午饭,在一张四座的饭桌前落座。我正低头吃饭时,有人“咚”地一声坐到了我对面。抬头看去,是一对老夫妇,扭头环视,旁边有一空桌,但位置不好。若是在国外,这对夫妇多半会坐到位置不好的空桌去,也许成都或北京上海也会这样。但洛带是乡下小镇,人们没有“汽泡”意识。
我在“汽泡”被入侵的第一秒钟,感觉不悦,但立刻就对老夫妇产生了好感,因为他们两人在那样的高龄还结伴下饭馆,透出一种人际的温馨。于是我主动同他们聊天:
“婆婆是这镇上的人吗?”
“是村里的,离镇上有十多里路。”
“大爷今年高寿?”
“82了,我们都82了。”
“你们在村里还种庄稼吗?”
“好多年都不种庄稼了,我们种果树,我们有十多亩果园,有桃子、柚子、橙子、橘子。”
“你们能干了果园的活吗”?
“儿子帮我们做。”
我想抓拍两位老人的照片,但面对面坐着,抓拍会有点唐突,只好问能否给他们拍照。两人闻言,立刻摆出照相的姿
势,我不得不假装摆弄相机,等他们放松下来再拍。
饭后我要替二位老人付账,他们不从,邻桌的食客目睹了全过程,便为我帮腔,说是尊敬老人,应该的。饭馆老板见状,也跑来帮腔。
付过三人的账,我与二老道别,走出餐馆,抬眼看见一片温馨的阳光。这是成都平原难得的冬日阳光,在雾气中形成一个巨大的暖洋洋的光环,像个汽泡,笼罩着古镇熙熙攘攘的游人。


没文化的旅游
出门旅游看什么,是否参观美术馆?这个问题涉及游客的文化素质问题,也涉及整体的国民素质问题。但是,若游客不参观美术馆,便真是国人没素质,还是中国旅游没文化?这问题是否更涉及美术馆的社会职能?
我买了不少出行欧洲的旅游手册,多是欧美出版的英文系列套书,既有大部头的全欧旅游通览,也有欧洲名城的单本小册子。这些手册的共同特点,是介绍各地旅游景点时,会推荐当地的主要美术馆或艺术博物馆,甚至将其列为旅游首选,例如巴黎的罗浮宫和奥赛美术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国立美术馆和泰特美术馆,以及罗马的梵蒂冈博物馆,等等。到这些地方参观,主要是看画,看欧洲历代艺术作品。
我也买了不少国内出版的中国旅游手册,也是各种套书,包括各地旅游通览和主要城市的单本小册子。这些书的最大特点,是很少有或者干脆没有各城市美术馆或艺术博物馆的介绍。比方说,前两年的夏天我都在旅游名城杭州度过,但手头的旅游书,却没有列出杭州的美术馆。我在杭州居住的时间加起来近半年,其间竟然没在当地逛过一个美术馆。不消说,看画并不在国人的旅游日程中。
我几乎每年都到欧洲旅游,在所到之处,总是从一个美术馆到另一个美术馆,马不停蹄地奔波参观,美术馆是我出行欧洲的首要目标。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游客都像我一样喜欢看画,也许他们对美术馆没兴趣,因为他们并非艺术家。那么,游客出行究竟看什么?所谓“观光”,如果就是观看风光,那么什么是风光?国内的旅游手册介绍的多是山水风景和古镇遗迹之类,即所谓自然风光和人文风光,可是,游客们也并非都是生态学家或考古学家。
此处的问题依然如故:旅游出行看什么?
我的家乡是四川成都,可是四川省博物馆我只参观过两次。第一次是20多年前,省博物馆还在人民南路旧址,其藏品很少对公众开放。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我参加四川大学和省文化厅组织的一个电视摄制组,拍摄三星堆考古发掘的专题文献片,我写作剧本,片名《蜀国之谜》。当时出土的三星堆宝藏,都收藏在省博物馆内,所以摄制组不仅到出土现场拍摄,也前往省博物馆拍摄。那是国内关于三星堆的第一部电视专题文献片,1990年在四川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后,获得了省文化厅和中央电视台当年的大奖。由于写作剧本,我第一次有机会观看省博物馆的收藏。
还在拍片的时候,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史教授易英带学生到成都考察古代艺术,想参观省博物馆,但不得其门而入。省博要么不开门,要么不展示藏品,而师生一行又无时间坐等。于是,我自告奋勇,说是认识省博的人,便与易英一道前往联系。进了省博办公室,不料那人满口官腔,说到底就一句话:不能参观。悻然告退时,易英说:我每年都带学生到全国各地参观,成都已来过多次,但总与四川省博物馆无缘。听此一说,我觉得自己实在颜面无光。
20多年很快就过去了,四川省博物馆已迁往城西的新址,并向公众开放藏品,今冬我有机会第二次参观,深叹今非昔比。如今四川省博物馆的办馆理念同西方文化大国的理念比较接近,注重藏品的陈列展示,也有文献资料的查阅研究,其服务项目、硬件设施等,基本与国际接轨。
此次参观,我在绘画馆看到了宋元明清和近代许多大师的作品,其中清人李鱓的花果册页,极富表现力,并以简约而获禅意,实为精品。清代画家中我最喜欢金陵八家的龚贤,曾写过研究其绘画的文章。这次在省博见到他一幅立式挂轴,是我在国内第一次看到龚贤山水。2006年夏天我在南京住了两个月,其间前往南京博物院,想看龚贤的画,因为那里是国内收藏龚贤作品最丰富的地方,可惜该院不对公众展示藏品。2007年夏天我前往沈阳的故宫博物院,想在满清的皇室故居参观龚贤绘画,竟然也无果而终。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就更不用说了,皇家藏品是很少对老百姓开放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其实观赏过很多龚贤真迹,但不是在国内,而是在美国的纽约和波士顿,那里的美术博物馆收藏有不少龚贤作品,并一律对公众开放,我甚至带学生去参观。2002年我有机会参观南京博物院收藏的龚贤绘画和金陵八家作品,但不是在南京,却是在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华美协进社陈列馆。由于这种讽刺性,此次在四川省博物馆见到龚贤真迹,才别有一番感叹。
言归正传,关于中国游客出游不参观美术馆的问题,在此便成了另一个问题:究竟是游客的文化素质低,还是旅游手册的编者文化素质低,或者是艺术博物馆缺乏社会职能,抑或三者互动,使中国旅游成了没文化的旅游?
偏见与妥协
偏见导致固执,妥协是否可以纠偏?
妥协是一种策略。当年我喜欢的一位学生,如今是北京某著名高校的青年教授,智慧迷人。前不久闲聊,她教育我要学会妥协,否则会在生活中碰得头破血流。我这人固执,虽表面随和,骨子里却认准一个理不回头,所以常被朋友们晓之以道。“妥协”之教,给了我当头一棒:连当年的“乖乖女”学生都明白的道理,我却执迷不悟,真是白活了半世。
中文之谓“妥协”,有单方面让步之意,以求“有话好商量”。西方之“妥协”为compromise,就是双方让步,即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圣经说“事就成了”,如今的时髦语则说“双赢”。
据说有剩女身高不足1米6,相亲条件却要求对方不得低于1米8。此类不识时务的要求,有违妥协的教义。单方面的“妥协”听起来不妥,像是劝降,可仔细一想,却是曲线救国。老子有刚柔之论,说是刚易折、柔可存,讲变通之理。当代西方思想理论界的“新历史主义”学派,主张“协商”,引申为双方妥协。生活是务实的,那些固执的想法,貌似坚守信念,实则迂腐,未能在务实与务虚之间周旋。
无论单方还是双方,妥协之妙,反衬出偏见与固执乃人性的弱点。
20年前初到北美,接触到一些粤语人士,有不愉快的经历,遂对粤语抱持偏见。其时同屋是个香港人,常流露粤语优越感,视普通话为乡下土语。此人每天下班后吃一碗方便面,然后就整晚看港产粤语录像,对警匪功夫和搞笑片大呼上瘾。目睹耳闻,我遂在潜意识中将方便面、港片、粤语视为一物,产生了生理上的厌恶感。
有次同屋的母亲从香港打来电话,儿子不在,便让我转致留言祝福生日,结语是“多揾些钱”。可怜天下父母心。
同屋的死党将自己供职公司的商业机密出卖给了对手公司,获得5000加元谍报费。为防事情败露,他不敢让对手公司将酬劳直接打入自己的银行账户,而是打给死党,由其转交。过了几天,同屋神情焦灼地对我说,若有人打电话找他,一律说不在、不知何时返回。果然,那些天总有个更加神情焦灼的人不断打来电话找他,都被我挡了驾。无数次电话后,那人终于忍不住了,可怜兮兮地对我说:死党欠他5000元钱不还、躲他、玩失踪,希望我理解他的电话烦扰。又过了几天,同屋对我说愿付我旅馆费,让我当晚别回家。问其何故,答曰有人会到家门口坐等,我若开门,等者会入室搬物抵债。
如前说言,妥协是策略,而非原则。早年留学时,我到当地中文报社求职挣学费。第一家报社的老板是港人,答应让我编写新闻、主持专栏、制作广告,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6天,月薪700加元,节假日加班无补贴。呵呵,这是海外华人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我领教了,未接受,不妥协。
第二家报社的老板也是港人,工作条件大致同上,附加一条:他在郊外的家有一间空屋,愿以200加元的低价租给我,而且每天早上可以搭他的车上班,下班后还可以搭他的车回家,车费全免,每月付点汽油费便可。呵呵,卖身为奴,我不干,不妥协。
第三家报社的老板是大陆的粤语人士,早年经香港转道加拿大谋生。谈到工作条件时他有惊人之语:这里的雇员都是香港人,他们每天下午5点准时下班,你是唯一的大陆雇员,自家人,就别按时下班了,我什么时候下班,你什么时候下班。我问:你通常什么时候下班?答:工作太多,晚上8点以后,节假前忙到夜里12点。又问:加班费怎么算?答:我付你月薪,不是时薪,再说了,都是自家人,加班算什么。呵呵,原来是剥削剩余价值,我可不是活雷锋,拜拜了您呐,不妥协。
如此这般,由于生理上的厌恶感,我对公共场所大声嚷嚷的粤语声更是深恶痛绝。我喜欢出门旅行,几乎游遍了西欧、北美和国内的主要城市,但不游粤语区,不游香港,对海外的唐人街也唯恐避之不及。
最近因公出差到香港,仿佛是纠偏之行,虽对呀呀呜的粤语不敢恭维,但对港岛却充满了好感,一因香港的人性化城市建设,二因香港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关于前者,只说从中环到半山的自动扶梯,便可见出其人性化理念,那不仅是为了方便游客,更是为当地居民的生活着想。关于后者,只消到太平山走一遭,经山间小道的浓荫曲径而享受山林之气,便不得不叹服其文明与自然的并存。
此行香港时日虽短,不能改变我对粤语的偏见,但让我放弃了今后不游香港的誓言。这放弃,是不是一种妥协?
段炼,加拿大高级教授,画家、文学家、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