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陌生化”体验的十种讲法
□ 王杰泓
一种“陌生化”体验的十种讲法
□ 王杰泓

在“当代艺术”日益沦为“艳俗”、“恶搞”、“反架上”、“后现代”、“图式复制”、“点子竞争”的代名词的如今这年月,事实上,艺术正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走向了与生活的“同一化”——机械、单调而没有新意。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曾在《杜尚、博伊斯与当代艺术的强迫症气质》、《观念艺术:“讽喻”的历史哲学》等文中明确指出:当代艺术的最大问题不在背离“架上-审美”传统,也不在“语言-图式”创新性的匮乏,而恰恰在于其自身作为一种“陌生化”存在之批判与救赎特质的缺失。艺术可以复现生活而写实,表现生活而写意,当然也可以疏离生活而抽象化、观念化,但从根本上讲,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是异质的,伏根于某种人生匮乏体验(如情感匮乏、精神迷惘、信仰失落等)的艺术,究其实质是对生活的不满与批判,而原本平淡无奇、淡乎寡味的生活也借此获得了一种被美化和被救赎的可能。
以此对艺术最朴素的定位为切入点,张立红等10人的当代油画展呈现出一种共通性的可贵的探索气质。他们出生于科班,但甚少学院气;有男有女,但执著于从“我”出发、聚焦于创作“兴奋点”的寻找抚平了性别的差异;成员中既有遭际坎坷、阅历丰厚的70后,也有初生牛犊、无知无畏的80后,但在对艺术抱怀一颗赤子之心、敬畏之心,述写个人特定的“陌生化”体验方面却是殊途而同归的。
张立红的作品延续了其在《无所谓》、《有什么》包括《蓝水》系列中的实验性,对确定性主题风格和一种赖以安顿自我的“兴奋点”的寻找使得他的创作同时充满了不确定性,暧昧而难于释读。诚如他自己所说,除非再画个几十张、达到一定的量,否则结论为时尚早。张作喜欢遣用树根、新生儿、青春少年等原本代表生命最纯朴、生动状态的形象入画,但是,瘦削的体形、惊颤的眼神以及蓝、灰、殷红的敷色处理提示着生命的“受伤”。不过与青春残酷绘画有所不同,艺术家的“受伤”体验并不外在于画面,其仅仅呈现为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淡淡意味,画面的语言表达本身是第一位的。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种个性化的摸索反倒使作品产生出“居间”的新质,即在“恋根”意向与“受伤”体验之间,在青春绘画与技术主义之间,进而言之在观念意向与画面语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艺术家自觉不自觉地把握到了一种平衡,从而令作品呈现出相当的艺术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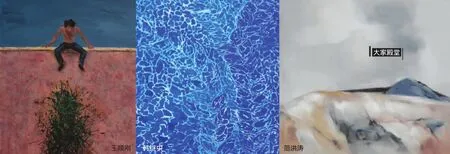
纪辉的作品源于对“文化间性”的理解与思考。作为艺术创作者和社会之一员的“两位一体”,他借用中国传统的形式符号元素,并将其置换到架上油画的创作中,人物的肢体、动作与表情在臆造的山水时空里被悄然放大,写实递渡为写意,宁静中夹杂着荒诞。无疑,艺术家企图借中西艺术语言符号的“嫁接”来审思不同文化间的矛盾冲突以及相互融合的可能。如此之技术处理同样产生出一种居间性和陌生化的效果:作品已非常态的水墨山水抑或架上油画,而是穿梭于中西两种图像之间、游离于两种艺术形式的边缘,个中所裹挟的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个体人与社会人、现实与理想、记忆与梦幻等等诸如此类的芜杂体悟,启人遐思。
画面是思想的形态学。解读王顺刚的作品无法回避其介入意识与观念诉求,但是,与时下热衷于猎巫、猎奇、猎艳或者沿袭光头、大头、卡通图式不同的是,他的作品表现出一种简洁的叙事性。主题上,艺术家关注外部物质世界挤压下个体的生存状态与情绪体验,并且择以一种讲故事式的直白方式直呈这种体验。而在画面的处理上,他将人物尽量缩小、不作细部特写,将色彩压缩至极简、近乎单色,同时“故意”运用溅、洒、刮等手法,造成粗糙的“坏画”感。此外,作者很注意作品命名的趣味性与直观性,譬如《骑墙记》、《找天使》、《莫名的兴奋》、《不高兴的鸭子》等,然而,简洁而有趣的命名恰恰反衬出主题的灰色与忧郁,正如作品形式的轻松与直观实质在转喻内涵的沉重与压抑一样。
韩继中自谦是画画的后学者,但这反而给他的创作带来一种“意外”的单纯与质朴。他的作品以单色(如绿、黄,或蓝)为主,突出精细的手工描绘。无论是含苞待放的麦子,葱翠欲滴的叶子,抑或是类似于茎叶状的臆想中的麦枝,画家均耽思一虑,一笔到底,一色到底,力求画面整体的极简与静穆。然而,刻意的手工无掩于艺术家观念的诉求:作品中的麦子一律呈透明状,宛如塑料而迥异于生活中我们所见的充满生命活力的麦子——这是对生存“异化”的某种提示。倘使我们进一步将一个个单幅平面连缀成一组有变化的图像(就像看电影那样),从黄到绿再到蓝,我们似乎还能从画面形象的更迭、递渡体味到画家心理的纤微变化,其中包含着他对用色的理解,也包含着一种对生命复苏的渴望……
风景入画是中国山水画的传统,而范洪涛的油画风景则代表了其对一种唯美诗意与纯净精神的向往。在当下绘画风格多元化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情境下,艺术家试图摆脱既往过于追求写实的油画画风,突出对风景的抽象写意。作品往往以高度概括的线条描绘山石之大形,以沉稳而含蓄的灰色来表现风景的色彩,同时舍去了多余的繁枝冗节,去除刻意的修饰,形成了一种简约、滋润、通透的画面效果。这种中西合璧的艺术处理,使得艺术家的系列作品兼有“具象变形”和“寄言出意”的审美特征,融注着个体自我一种宁静与单纯的心境。
与参展的男性艺术家相比,孙小蒙的绘画有一种特有的“女性”气质。爱美是人之天性,更是女人的“精神鸦片”。在孙小蒙的作品中,她以敏感、纤细的眼神凝视着那只美丽的手:妩媚、时尚,充满人工打磨的痕迹;或执上半株朴素、天然的花朵,或舞蹈着一个蒲公英的梦——相互冲突却又相得益彰,于对美之短暂的抱憾中浸润着对生命自恋式的怜爱。画面以红、黄、蓝为背景色,顺着画家感受现实所得的各种不同的假设,不断将观画者的想象引向一个个童话般而不失理性的想象空间。

在10位参展作者中,周璐也是一位喜欢讲述心灵故事的艺术家。如其自己所言:“我的作品如同日记,表现了我对生活和环境的阶段性思考。”在勤奋的她看来,能想到的就能写出来,写得出来的就试着画出来,写不出来也画不出来就留着继续酝酿。人和人之间真的能相互理解吗?周璐用叙事性的画面告诉我们:或许可以,但也只是彼此“以为”的可以,如此而已。两个身体靠在一起便是微温,但这并不足以驱除各自内心深处那份绝对的孤独。毫无疑问,艺术家不是一个冷血的悲观主义者,透过简单、率真的表达方式,其对生活真实和人际温情的信任仍然清晰可辨。
刘宏晖的作品聚焦于一种对时间的陌生化体验。世间万物有生必有灭,诞生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注定走向灭亡。在此意义上,时间并非永恒,时间其实也是毫无意义的。基于这种异乎流俗的理解,艺术家曲笔式地撷取金属物而非生命体来表现。在具体刻写金属物(如煤气罐、大卡车)时,他采取了新旧对比(通过不同颜色标识)的方式,尤其是对金属物报废后橙红的“锈迹”作了重点渲染。生锈意味着腐蚀,腐蚀的结果就是消失——金属物如斯,生命更是如此。“锈迹”的美绚烂多彩,同时也变幻无常,这令艺术家沉迷其间。整个作品不仅有形式的美感,而且内蕴着一种对时间不可逆转的伤感和莫名的荒诞感。
80后的李贤术有一种可爱的“愤青”或理想主义味道。他的若干大幅作品中都有一堵墙,一堵带窗户的灰色的墙;都有一条鱼,一条想要飞却被拴住的塑料鱼。地表是单色的,单调而压抑;建筑是死寂的,像一座座荒原中的坟墓;童年记忆中那在小河里自由嬉戏的鱼儿也变成了非生物化的怪物,游魂似的滞留在无趣而乏味的城市(尘世)间。显而易见,这是一幅幅“乡愁的隐喻”画。对于80后的年轻人而言,童话原本是恍如昨日、招之即来的,但现实却宣告着美好不再。这无疑是最让人伤感的。透过对冷漠、无趣的现实生活的反讽性述写,作品所暗含的其实也是对一种本真、有趣的生存状态的“招魂”。
“伤在外,必返其家。”概括此次参展的10位年轻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尽管我们可以指出其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譬如技术主义、经院主义痕迹,想法过多而大气不足,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他们在执著于表现由切身体验而延伸的观念意向上令人感佩。在当代艺术、当代生活一再遭受恶意的戕害,人的情感、精神与信仰无从安顿的当下,作为无名者的他们惟倚一腔赤诚、深入人性的迷惘,然后用一种最朴质的方式将其所思、所想、所悟表现出来。如此之可贵的探索无论是放在当代艺术史的坐标上考量,抑或是置于寻找“还乡路”的艺术的根性角度评价,其意义与价值都是深远而巨大的。相信他们会是未来艺术的引路人!
王杰泓,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武汉大学艺术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本文系作者作为策展人为“方式·方言——湖北美术学院当代油画十人展”(2010年3月于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所作的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