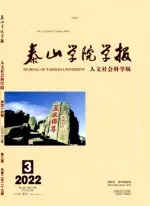论明代胡应麟《经籍会通》的编辑学术特色
梅焕钧,阎现章
(1.泰山学院学报编辑部,山东 泰安 271021;2.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河南 开封 475001)
在编辑出版、科学研究和古籍整理的学术文化传播活动中,对于史料和古代流传的书籍之真伪进行辨别,去伪存真,由此而形成了一门专门的辨伪学学问。辨伪就是控制文献信息传播的失真,把文献中的伪信息揭示并汰出传播过程,保证真实信息的传播,它是控制或避免文献传播失真的一种有效方法。而对于古书的真伪进行科学的辨伪,也是编辑出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辨伪学的学术发展历史上,明末胡应麟撰写的《四部正讹》,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辨伪专著。胡应麟在总结前人辨伪成就的基础上,并结合自己实践建立了考辨伪书的理论和法则,从而使辨伪学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同时他对历代图书编辑源流、散失混杂、刻印收藏等进行综合性和比较性研究后,撰写的《经籍会通》是一部随笔性的编辑笔记,也同样具有较高的文献史和编辑史的价值,这对于学术研究和图书出版传播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胡应麟的编著学术活动
胡应麟(1551-1602年),字元瑞,明代浙江兰溪人。《明史》在《王世贞传》中简单附记说:“胡应麟,幼能诗。万历四年举于乡试,久不第,筑室山中,购书四万余卷,手自编次,多所撰著。”据吴晗先生在《清华学报》1934年第 1期发表的《胡应麟年谱》所载,胡应麟“晚更字明瑞,尝自号少室山人,已而慕其乡人皇初平叱石成羊故事,更号曰石羊生。又号曰芙蓉峰客,壁观子。儿时肌体玉雪,眉目朗秀”。
他好学成性,幼年时代就留心经籍。《少室山房类稿》卷 92《二酉山房记》说:“始余受性颛蒙,于世事百无一解,独偏嗜古书籍。七龄侍家大人侧,闻诸先生谈说文典,则已心艳慕之,时时窃取阅。”嘉靖四十四年 (1565年),他 15岁时就编辑诸小说为《百家异苑》。他深受其父的影响,喜好书籍,并节衣缩食搜求图书,在收藏图书和学术研究中十分艰辛。隆庆六年 (1572年)胡应麟 22岁,《胡应麟年谱》据《少室山房类稿》卷 92《二酉山房记》记载,是年“夏,束装南返,便道还里中。宋宜人顾从宦日久,田园芜。又先生素羸,因请留处家,而副宪公入楚督漕粮。命下束装日,宦橐无锱铢,而先生妇簪珥亦罄尽,独载所得书数箧,累累出长安。自是先生奉母宋宜人里居十载,中间以试事入杭者三,入燕者再,所涉历金陵吴会钱塘皆通都大邑,文献所聚,必停舟缓辙,搜猎其间,小则旬余,大或经月,视家所无有,务尽一方乃已。市中精绫巨轴,坐索高价,往往视其乙本收之。世所由贵重宋梓,直至与古遗墨法帖并,吴中好事者悬赀购访。先生则以书之为用,枕藉揽观,今得宋梓而束之高阁,经岁而手弗敢触,其完好者不数卷,而中人一家产立尽,亡论弗好,即好之胡暇及也,至不经见异书,倒庋倾囊,必为己物,亲戚交游上世之藏,帐中之秘,假归手录,卷帙繁多,以授侍书,每耳目所值有当于心,顾恋徘徊,寝食俱废,一旦持归,亟披亟阅,手足蹈舞,骤遇者率以为狂,而家人习见,弗怪也。自先生为童子至今,年日益壮而嗜日益笃,书日益富,家日益贫。副宪公成进士,剔历中外滋久,乃敝庐仅仅蔽风雨。而先生所藏书,越中诸世家顾无能逾过者。盖节缩于朝哺,辗转于称贷,反侧于寤寐,旁午于校雠者二十年于此矣”。[1]其藏书搜求之艰辛,于此可见一斑。
胡应麟搜求和收藏图书以实用为主,在藏书的同时主张进一步去阅读和进行研究,来获取新的知识信息进行学术创作。他的《少室山房笔丛》卷 1《经籍会通》就是在收藏图书过程中,对历代图书编辑源流、散失混杂、刻印收藏等进行综合性和比较性研究后,撰写的一部随笔性编辑笔记,具有较高的文献史和编辑史的学术价值。
他反对那种藏书而不读书和不研究的方法,对于藏书与读书的关系,在《经籍会通》(四)中针对洪景庐“以博洽名,而早列清华,或未晓此曲折,诸家亦鲜论及”的情况,他明确指出:“博洽必资记诵,记诵必藉诗书,然率有富于青缃,而贫于问学,勤于访辑,而怠于钻研者。好事家如宋秦、田等氏弗论,唐李邺侯何如人?天才绝世,插架三万,而史无称,不若贾耽辈之多识也。扬雄、杜甫诗赋咸征博极,而不闻蓄书,雄犹校雠天禄,甫僻居草堂拾橡栗,何书可读?当是幼时父祖遗编,长笥胸腹耳。至家无尺楮,藉他人书史成名者甚众,挟累世之藏而弗能读,散为乌有者,又比比皆然,可叹也!若刘氏父子,张、陆诸人,庶几兼之矣。”因此,胡应麟把藏书家划分为“好事家类”和“赏鉴家类”两种,他接着说:“画家有赏鉴,有好事,藏书亦有二家。列架连窗,牙标锦轴,务为观美,触手如新,好事家类也。枕席经史,沈缅青缃,却扫闭关,蠹鱼岁月,赏鉴家类也。至收罗宋刻,一卷数金,列于图绘者,雅赏可耳,岂可谓藏书哉!”有的藏书家,比如唐李邺藏书多达三万余卷,但却很少翻看,图书新如手未触摸过一样。对于这种藏而不读,胡应麟在《经籍会通》(四)的结尾议论说:“夫书好而弗力,犹亡好也,故录庐陵《集古序》。夫书聚而弗读,犹亡聚也,故录眉山《藏书记》。夫书好而聚,聚而必散,势也。曲士讳之,达人齐之,益愈见聚者之弗可亡读也,故录易安《金石志》终焉。”鉴于此,胡应麟才把藏书与读书和研究相互结合起来,他的《经籍会通》正是其在整理图籍和系统研究以及考察图书出版传播情况后的编辑作品。
胡应麟癖嗜古籍图书,若遇到稀世刻本,虽解衣典质也不惜。比如张文潜的《柯山集》100卷,胡应麟旧藏仅有 13卷,属于抄合类书刊刻者,并非原著的旧版本,“余尝于临安僻巷中,见抄本书一十六帙,阅之,乃《文潜集》,卷数正同,书纸半已漶灭,而印记奇古,装饰都雅,盖必名流所藏,子孙以鬻市人。余目之惊喜,时方报谒臬长,不持一钱,顾奚囊有绿罗二匹代羔雁者,私计不足偿,并解所衣乌丝直掇青蜀锦半臂罄归之,其人亦苦于书之不售,得直慨然,适官中以他事勾唤,因约明旦。余返寓,通夕不寐,黎明不巾栉访之,则夜来邻火延烧,此书倏煨烬矣,余大怅惋弥月。因识此,冀博雅君子共访,或更遇云”。[2]由此可见,胡应麟对于稀刻典籍的重视程度,以至于该书被大火烧后“怅惋弥月”。
胡应麟藏书筑室山中,取名二酉山房藏书楼,王世贞曾作《二酉山房记》,对于胡应麟嗜书,读书和搜集收藏图书的情况进行了描述。“余友人胡元瑞,性嗜古书籍,少从其父宪使君京师,君故宦薄,而元瑞以嗜书故,有所购访,时时乞月俸,不给则脱妇簪珥而酬之,又不给则解衣以继之。元瑞之橐,无所不罄,而独其载书,陆则惠子,水则米生,盖十余岁而尽毁其家以为书。录其余赀以治屋而藏焉。屋凡三楹,上固而下隆起址,使避湿,而四敞之,可就日。为庋二十又四,高皆丽栋,尺度若一。所藏之书为部四,其四部之一曰经,为类十三,为家三百七十,为卷三千六百六十。二曰史,为类十,为家八百二十,为卷万一千二百四十四。三曰子,为类二十二,为家一千四百五十,为卷一万二千四百。四曰集,为类十四,为家一千三百四十六,为卷一万五千八十。合之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元瑞自言,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饥以当食,渴以当饮,诵之可以当韶,览之可以当夷施。忧藉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而是三楹者无他贮,所贮亦独书。书之外,一榻、一几、一博山、一蒲团、一笔、一研、一丹铅之缶而已。性既畏客,客亦见畏,门屏之间,剥啄都尽,亭午深夜,坐榻隐几,焚香展卷,就笔于研,取丹铅而雠之,倦则鼓琴以抒其思,如是而已。故人黎惟敬以古隶扁其楣,曰二酉藏书山房,而属余为之记。……今元瑞以匹夫之致,而阛阓之守,仅十余年,而至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不亦难哉!虽然,世有勤于聚而倦于读者,即所聚穷天下书,犹亡聚也;有侈于读而俭于辞者,即所读穷天下书,犹亡读也。元瑞既负高世之才,竭三余之晷,穷四部之籍,以勒成乎一家之言。上而皇帝王霸之猷,贤哲圣神之蕴,下及乎九流百氏,亡所不讨核,以藏之乎名山大川,间以余力游刃,发之乎诗若文,又以纸贵乎通邑大都,不胫而驰乎四裔之内,其为力之难,殆不啻百倍于前代之藏书者,盖必如元瑞而后可谓之聚,如元瑞而后可谓之读也。噫,元瑞于书,聚而读之几尽矣。”[3]胡应麟在万历四年 (1576年) 26岁时中举,参加乡试以经义中式成孝廉,后也曾赴京参加会试。但他并未进入仕途,而是醉心于古籍的收藏和研读,并对所收藏的 4万多卷图书整理编辑目录,在 38岁前著书 18种,辑书 6种,编辑类书 4种,是明代中期一位著名的博学家,与杨慎、陈耀文、焦竑齐名。
其著作集有 120卷的《少室山房类稿》、48卷的《少室山房笔丛》等于世流传。万历三十年(1602年)病逝于家中,享年 52岁。他“髫龄事学,即已驰誉两都,长而跋涉南北,所与游多一时名下士,达官巨卿,均折节与交。中年与王世贞兄弟汪道昆游,盛得奖掖,益自力于著述,虽间以病废,且性好游,足迹遍南北,而其著述之富,犹复前无古人。王世贞、汪道昆殁后,先生称老宿,主诗坛,大江以南皆翕然宗之,诸词客裹粮入婺者莫敢有异同。……身后极萧条……所筑二酉山房归同邑武进士唐骧家,改颜曰古梿书屋。藏书俱散逸无存者”。[4]
二、《经籍会通》的编辑学术特色及其成就
胡应麟正是在这样的搜书、求书、读书和编辑整理的校雠、考证实践中,以及在对前人关于伪书鉴别丰富经验的总结基础上,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撰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辨别伪书的著作——《四部正讹》,从而建立起了一门专门的辨伪学学问。《四部正讹》的问世,标志着图书辨伪学的正式建立,对于古籍的编辑出版和整理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万历十七年 (1589年)七月,他撰写了具有重要编辑学术价值的著作《经籍会通》。
胡应麟的《经籍会通》共四卷,关于此书的写作原委,他在自序中说:“凡前代校综坟典之书,汉有《略》,晋有《部》,唐有《录》,宋有《目》,元有《考》,《志》则诸史共之,肇自西京,迄于胜国,纪列纂修,彬彬备矣。夫其渊源六籍,薮泽九流,绎百家,溯洄千古,固文明之盛集,鸿硕之大观也。昭代綦隆,钜儒辈出,诸所撰造,比迹黄虞,惟是经籍一途,编摩尚缺,概以义非要切,体实迂繁,笔研靡资,岁月徒旷耳。夫以霸闰之朝,草莽之士,犹或拮据坟素,忝窃雌黄,矧大明日揭,万象维新,岂其独盛述鸿裁,彪炳宇宙,而脞谈冗辑,阔略曩时哉!辄不自揆,掇拾补苴,间以管窥,加之棁藻,稍铨梗概,命曰《会通》,匪直寄大方之嚬笑,抑以为博雅之前驱云。”[5]可见,胡应麟鉴于当时对于历代图书出版传播的“编摩尚缺”,以及“概以义非要切,体实迂繁,笔研靡资,岁月徒旷”的主客观原因,静下心来“脞谈冗辑”,对于所藏之图书进行编辑整理和编辑论证,“掇拾补苴,间以管窥,加之棁藻,稍铨梗概”,在进行编辑记载和考论的过程中,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会通”的编辑思想,因此将其编辑整理和考论的著作以“会通”名之。
一般认为,该书是胡应麟考论书籍的撰著、传播和收藏情况的,是一本对历代书籍编纂源流、散失混杂、刻印收藏等情况作综合性、比较性研究后的成果,也是一种议论与记载合编、考辨与传闻共存的古代文献史笔记。其实,从出版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该书也是一部反映古代图书出版传播历史的专书。该书的编写体例,除了总序外,每一卷也都有简短的序文(序例)来阐发本篇章的内容,其分门讨论,有条不紊,结构合理。“述源流第一”(卷 1),主要对于历代图书传播收藏和散佚情况,结合有关资料进行述论。“坟籍之始,肇自羲黄,盛于周汉,衍于梁晋,极于隋唐。一烬于秦,再厄于莽,三灾于绎,四荡于巢。宋氏征求,力倍功半,元人裔夷,事轶言湮,聚散废兴,概可睹矣,述源流第一。”其“述类例第二”(卷 2),主要对历代图书编辑分类的发展变化历史结合有关史料进行述论,并对目录图书的编辑分类原则和方法进行探讨,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经史子集,区分为四,九流百氏,咸类附焉,一定之体也。第时代盛衰,制作繁简,分门建例,往往各殊,唐宋以还,始定于一。今稍掇拾诸家,撮其大略,以著于篇,述类例第二。”其“述遗轶第三”(卷 3),主要对于古今的一些图书进行辩驳诬谬,其中以子书为主。“古书历世,兵革洊更,间有残编裂简,仅以空名,寓于载籍。辑录之家,存而不论;博雅之流,论而不议;钓奇之士,顾有取焉。编摩之暇,辩驳诬谬,联络遗亡,与癖古者共之,述遗轶第三。”其“述见闻第四”(卷 4),主要叙述胡应麟所见的明代图书出版传播的史实。“古今坟籍,梗概略陈,然率综核陈编,未遑近迹。余九龄入燕,往来吴越,垂三十载,涉历宾游,脞言鄙事,时有足存,辄缀大都,附于简末。后之博雅,征求故实,万一在焉,述见闻第四。”
从出版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经籍会通》的成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编辑、编录、摘编了历史上及明代有关图书出版传播和收藏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出版传播史和文献史意义。同时,该书也附有编者对有关问题的议论考辨和编辑点评,将历史记载与编辑个人的评论两者合而为一,富有特色。
比如对于陆子渊的《统论》、欧阳修的《集古录序》等文章全部编录。陆子渊家多藏书,所著别集中有记述古今图书传播简况的《统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胡应麟就予以编录。“自古典籍兴废,隋牛弘谓仲尼之后,凡有五厄,大约谓秦火为一厄,王莽之乱为一厄,汉末为一厄,永嘉南渡为一厄,周师入郢为一厄。虽然,经史具存,与孔壁汲冢之复出,见于刘向父子之所《辑略》者,为书凡三万三千九十卷,孔氏之旧,盖未尝亡也。至隋嘉则殿,乃有书三十七万卷,可谓富矣。柳顾言等之所校定,才七万七千余卷,则是重复猥杂,张其数耳。《七略》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诸史群撰具焉。南朝盛时,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万余卷,尚有重本,则传世之书,惟存旧数而已。散亡之极,犹不失万卷。唐世分为四库,开元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晋所增,与释老之编,杂出其间,亦不过三万余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二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乱后,备加搜采,而四库之书复完。黄巢之祸,两京荡然。宋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余卷,自后削平诸国,尽收图籍,重以购募。太平兴国初,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固半实尔。庆历《崇文总目》之书,三万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略》,顾有不及,参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书邪。洪《容斋》谓《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书,十亡八九。而姚铉所类文集,亦多不存,因以为叹。然经史子集之旧,宋亦未尝阙焉,宣和访求,一日之内,三诏并下,四方奇书,有此间出,见于著录者,溢出二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馆阁。高宗渡江,书籍散逸,加意访求,淳熙间,类次见书,凡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数虽过于《崇文》,而新籍兼之。至于绍定之灾,而书复阙矣。”[6]以上是胡应麟所编录的陆子渊所记古今书籍的梗概。紧接着,他在编辑点评中认为:“颇为简明,大都本马氏《通考》所载而节略之。然《隋书》三十七万,柳顾言等除去猥复,止得三万七千,见《通考》甚详,而此以为七万余卷。梁任昉、阮孝绪等目录,大约不过三万,虽云释典在外,要不过二万余。元帝收集煨烬,乃得七万,未必无重复也,唐《志》开元书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学者自为,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共八万余。陆所言释老之编杂出者三万余,迄不详何所指,考新旧《唐书》咸不合。宋嘉定中,续得一万八千余卷,陆亦未及载也。”于是,胡应麟又在后面附有“漫识”性的考论,并提出了历代图书在传播的过程中曾经遭遇有“十厄”。
他说:“牛弘所论五厄,皆六代前事。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而女真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蒙古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大业一也,天宝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绍定五也,通前为十厄矣。”对于古今书籍的聚散传播状况,他评论说:“等而论之,则古今书籍,盛聚之时,大厄之会,各有八焉。春秋也,西汉也,萧梁也,隋文也,开元也,太和也,庆历也,淳熙也,皆盛聚之时也。祖龙也,新莽也,萧绎也,隋炀也,安、史也,黄巢也,女真也,蒙古也,皆大厄之会也。东京之季,纂辑无闻 (班《志》率西汉东京甚希,他无校集者),魏晋之间,采摭未备,卓、曜诸凶,摧颓余烬,于聚于厄,俱未足云……大抵历朝坟籍,自唐以前,概见隋《志》,宋兴而后,《通考》为详。第其卷帙之数,往往异同,缘诸家辑录,或但纪当时,或通志一代,或因仍重复,或节略猥凡,故刘、班接迹,繁简顿殊,三谢并兴,多寡悬绝,即博洽之流,勤于论核,而疑似之迹,未易精详。”鉴于这种情况,胡应麟“绎群言,旁参各代,推寻事势,考定异同”,[7]对于从西汉到宋代的图书聚散之数结合史书材料,进行了精细的考证。
第二,综合分析历代反映图书传播历史的史志目录、官修和私编目录之成就和缺失,并对各家目录书的书目编辑得失和编辑分类 (即类例)进行评论,因此该书也是一部记载中国古代书目编辑史和编辑提要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在综合评论书目和类例的编辑得失时,胡应麟一般都有节录和分析。他认为,“观其类例,而四部之盛衰始末,亦可以概见矣”。从对图书编辑分类的检阅中,就可以看出编辑分类相互承继创新的状况,考察出图书编辑盛衰的发展历史。比如刘歆的《七略》,“一曰《六艺》,一曰《诸子》,一曰《诗赋》,一曰《兵书》,一曰《术数》,一曰《方技》,而首之《辑略》,以总集诸书之要,则分列品题,实六略耳。班固《艺文志》,增入五家,而省其十家,共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歆原数三万三千九十卷,固节其猥冗,仅得十之三四,大概新莽之乱,焚轶之余故也。然《七略》原书二十卷,班氏《艺文》仅一卷者,固但存其目耳。向、歆每校一书,则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近世所传《列御寇》、《战国策》,皆向题辞,余可概见,因以论奏之言,附载各书之下,若马氏《通考》之类,以故篇帙颇繁,惜今漫无所考,详其义例。《六艺》,经也,《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四略,皆子也,《诗赋》一略,则集之名所由昉,而司马氏书,尚附春秋之末,此时史籍甚微,未足成类也”。[8]
对于王俭的《七志》,“一《经典》,二《诸子》,三《文翰》,四《军书》,五《阴阳》,七《图谱》”,他认为“前六志咸本刘氏《六略》,但易其名,而益以图谱及佛、道二家,名虽曰七,实九志也,然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于卷首,盖亦《辑略》之意。按经不曰《六艺》而曰《经典》,则史固渐备矣,隋《志》谓其文义浅近,远非歆、向伦。余谓俭,齐相佐命,百事填委,故无暇此,浮剽其名耳”。阮孝绪《七录》,“一《经典》,二《纪传》,三《子兵》,四《文集》,五《技术》,六《佛》,七《道》。又本王氏而加《纪传》,并《诸子》、《兵书》为《子兵》,《阴阳》、《术艺》为《技术》,又益以佛、道二家,史书至是渐盛,与经子并列,而佛、道二家之言,大行中国矣”。
胡应麟认为书目文献的编目分为四部,“实魏荀勖始之,一曰甲部,纪六艺、小学等书。一曰乙部,纪诸子、兵术等书。一曰丙部,纪史记、皇览等书。一曰丁部,纪诗赋、图赞等书。此时史、集二部尚希,故王、阮二目,更从刘氏分七类,至唐大盛,于是史居子上,次经、佛、老附子,次史,而终之以集,定为四部,宋氏以还,递相沿袭,而作者之意,未有所明。马氏始仿刘向前规,论其大旨,体制骎骎备矣”。[9]
胡应麟通过对《七略》、《七志》、《七录》以及荀勖《晋中经簿》四部分类和唐代元行冲《群书四部录》的综合分析,认为“前史所述魏晋诸家书目,条流仅举,诠次靡详。惟阮氏《七录》始末,备载《弘明集》中,余睹其分门创义,损益前规,综核之功,勤且力矣,隋、唐《志》率沿此。”他对于《七录》的书目编辑成就予以肯定,此外,对《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也都有所评述,大致比较科学地总结了明代以前目录图书编辑发展的历史。
第三,对于明代中期以后图书的刻印传播情况,根据其所见闻进行了记载,这对于研究明代图书出版传播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胡应麟在《经籍会通》(四)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明代中叶后图书刻印传播的状况。他说:“余自髫岁,夙婴书癖,稍长,从家大人宦游诸省,遍历燕、吴、齐、赵、鲁、卫之墟,补缀拮据,垂三十载。近辑山房书目,前诸书外,自余所获,才二万余。大率穷搜委巷,广乞名流,录之故家,求诸绝域,中间解衣缩食,衡虑困心,体肤筋骨,靡所不惫,收集仅茲。至释、道二藏,竟以非力所及,未能致也。”详细地讲述了自己求购书籍的艰苦历程。
他根据自己所历所见,认为明代“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适东南之会,文献之衷,三吴七闽,典籍萃焉。……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
对于图书交易传播的书肆,如燕中书肆、武林书肆、金陵书肆的具体位置以及书肆的盛况也都有所描述。“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
当时刻书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越、秦、楚,今皆有刻,类目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刻印书的纸张,“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箧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
通过对书籍的比较,胡应麟认为:“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抄刻,抄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
同时,胡应麟又结合叶少蕴关于雕版印刷的说法,进行考论和发挥。
“叶少蕴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书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对此论,胡应麟说:“此论宋世诚然,在今则甚相反。盖当代板本盛行,刻者工直重钜,必精加雠校,始付梓人,即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抄录之本,往往非读者所急,好事家以备多闻,束之高阁而已,以故谬误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抄本价十倍,刻本一出,则抄本咸废不售矣。(今书贵宋本,以无讹字故,观叶氏论,则宋之刻本患正在此,或今之刻本当又讹于宋邪,余所见宋本讹者不少,以非所习,不论。)”
叶少蕴说,“天下印书,以杭为上,蜀次之,闽最下”。到了明代则有所变化,胡应麟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诸方与宋世同。(叶以闽本多用柔木,故易就而不精,今杭本雕刻时义,亦用白杨木,他方或以乌桕板,皆易就之故也。)”
应当指出的是,胡应麟由于对一条史料记载认识的失误,从而导致了他误认为雕版印书始于隋代。“叶少蕴云,世言雕板始自冯道,此不然,但监本始冯道耳。柳玭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所鬻字书小学率雕本,则唐固有之。陆子渊《豫章漫抄》引《挥麈录》云,毋昭裔贫时,尝借《文选》不得,发愤云,异日若贵,当板镂之,以遗学者,后至宰相,遂践其言。子渊以为与冯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玭后也。载阅陆河汾燕闲录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 (593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此印书之始,据斯说则印书实自隋朝始,又在柳玭先,不特先冯道、毋昭裔也,第尚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本矣,唐文皇胡不扩其遗制,广刻诸书,复尽选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馆抄书。何邪?余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经像,盖六朝崇奉释教致然,未及概雕他籍也。唐至中叶以后,始渐以其法,雕刻诸书,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于今而极矣。(活板始宋毕昇,以药泥为之,见沈氏《笔谈》十八卷,甚详。)遍综前论,则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此余参酌诸家,确然可信者也。然宋盛时,刻本尚希,苏长公《李氏山房记》,谓国初荐绅,即《史》、《汉》二书不人有。《挥麈录》谓当时仕宦,多传录诸书,他可见矣。”
对于胡应麟误认为雕版始于隋朝的说法,《四库全书提要》指出:“又云刊板当始于隋,引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为证。然史文乃废像遗经,悉令雕造,非雕板也。”
就图书的制作、传播技术和方式而言,胡应麟对比古今说:“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书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简,冗重艰难,不可名状。秦汉以还,浸知抄录,楮墨之功,简约轻省,数倍前矣。然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一纸表裹,常兼数番,且每读一卷,或每检一事,阅展舒,甚为烦数,收齐整比,弥费辛勤。至唐末宋初,抄录一遍而为印摹,卷轴一变而为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四善具焉。溯而上之,至于漆书竹简,不但什百而且千万矣,士生三代后,此类未为不厚幸也。(又前代篆隶,与今楷书,工亦有难易也。)”[10]
胡应麟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博学者,也是一位颇有见识的编辑家,他取得成就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就主观上来说,他富有远大的志向,广泛搜求书籍,藏以致用,并对图书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和考辨;就客观上来说,图书编辑出版传播业到明代已很发达,各种书籍车载斗量,这为他成就的取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对于胡应麟的学术成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他“与李维桢、屠龙、魏允中、赵用贤称末五子……而记诵淹通,实在隆万诸家上,故所作芜杂之内,尚具菁华,录此一家亦足以为读书者劝也”。《四库全书》的《少室山房笔丛》编辑提要评价说:“其中征引典籍极为丰富,颇以辨博自矜,而舛讹多不能自免”,比如沈德符《敝扫轩语》、王世祯《香祖笔记》、张文岚《螺江日记》多有驳正,有人驳正则说明了胡应麟的学术思想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并得到了传播,这是一种健康的学风。“沈德符等之所纠,盖捃摭既博,又不复自检点,抵牾横生,势固有所不免。然明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应麟独研索旧文,参校疑义,以成是编,虽利钝互陈,而可资考证者亦不少。朱彝尊称其不失读书种子,诚公论也。”[11]
[1][4]吴晗.胡应麟年谱[A].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81,425-426.
[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A].经籍会通 (3)[M].北京:中华书局,1958:51.
[3][8][9]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A].经籍会通(2)[M].北京:中华书局 1958:33-35,21,22.
[5]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甲部)[A].经籍会通·引言[M].北京:中华书局,1958.
[6][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A].经籍会通 (1) [M].北京:中华书局,1958:6,7-8.
[10]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A].经籍会通 (4) [M].北京:中华书局,1958:55-61.
[11]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子部杂家类)[A].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