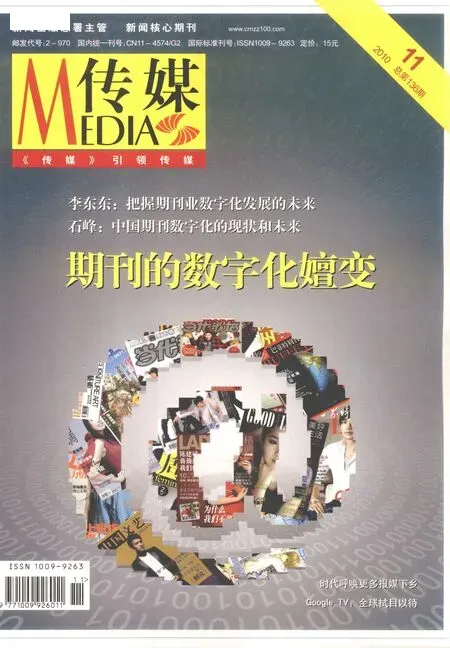传媒与司法冲突的法文化反思
文/林 林
2010年上半年以来,中国传媒界接连遭遇一系列被粗暴对待的事件:“赵长海被通缉事件”、“霸王员工冲击报社事件”、“郭德刚弟子打记者事件”等等。这一系列事件集中发生,反映了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领域之外特别是传媒与文化领域法制体系建设的严重滞后和整个社会法文化培育的严重缺失。《环球时报》8月6日的一篇社评提出,这些事件表明“不仅一些官员,中国的大量企业、个人都极不适应舆论监督。中国全社会都应温习民主政治的这一课。能否善待媒体,是一个社会文明和理性程度的重要标志”。
事实上,类似上述事件近十几年来并不鲜见,除传媒受到地方行政权、司法权、企业、公众人物等无理粗暴干涉等事例呈增长之势外,传媒因报道涉及名誉权等侵权官司的比例更是直线上升。据不完全统计,自1985年以来,新闻官司案立案的已超过千起,其中以媒体侵犯公民名誉权和舆论监督为主。
在中国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公民自我权益保护意识大大提高的背景下,中国当下传媒业蓬勃发展,也迎来了动辄处于“被干扰”乃至站“被告席”的高发期。传媒似乎成了谁都可以轻易以诉诸法律相胁迫的对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这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对民主政治法律文化的无知和偏误。
提高全社会对传媒天职的正确认知
传媒是社会的良心。传媒的表达自由,并不是传媒自身随心所欲的信息采集与传播的自由,它体现的是民主社会所赋予传媒对公众知情权、信息发布与传播权、对公共事务监督批评权的担当。因此,联合国“关于媒体与司法独立之间关系的马德里原则”开宗明义指出,“媒体自由,作为表达自由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对实现法治的民主社会至关重要。”其基本原则提出,“媒体的职能和权利是收集并向公众传递信息,以及对司法管理加以评论,包括在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审理前、审理中和审理后的案件加以评论。”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可以说,作为当代民主政治的基石,言论出版自由也即公民的表达自由都是一项宪法性权利,而传媒采访报道的自由,其法理的渊源即来源于此。对传媒报道自由的司法保护和尊重,也要高于其他职业的一般性权利保障。这是由传媒的天职和社会担当所决定的。在西方,新闻媒体被称为“第四种权力”,新闻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被西方普遍纳入宪法性权利范畴之中,明确加以保障。

与西方新闻传媒具有的由公民言论自由引申出的独立的舆论监督权不同,中国的新闻传媒作为国有的、党政部门隶属的一个事业单位(尽管现在正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将绝大多数的经营性质的新闻机构转为企业,但在主管、主办、舆论导向、干部任用、资产监管等方面,其根本性质并未改变),其舆论监督权属于“内部监督”,是非独立的监督,也是一种有限的监督。故而,新闻媒体有限的批评报道,时常还受到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政府行政部门的约束。也正因如此,社会上对传媒职能与法律地位的认识极其有限,普遍将其视为一个信息发布的机构,隶属于各级各地的政府、企事业单位和民间团体。在官本位和行政权超强的中国社会语境下,新闻传媒单位在一般民众眼里的印象也仍然是一个“政府性且能发布新闻”的令人生畏的机构。而在行政强力部门、司法机关、公众人物眼里,却是一个弱势单位、弱势群体。所以,一旦发生与其相冲突的情况,他们就能轻易采取强力的、强硬的对抗姿态。可见,中国的传媒(机构、个人及其新闻采集发布权)缺乏应有的权利保障,以及公民社会缺失对传媒“自由”报道和传播权具有的上位的法律地位的意识,是根本原因。
传媒与司法关系解决的域外借鉴
考察西方在对待新闻传媒与司法机构、行政权力、公众人物等出现纠纷时是如何应对的,显然有利于中国建塑起有自身特色的传媒法律文化。纵观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对媒体因诽谤罪而予以刑事处罚的判决已越来越少。在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刑事诽谤案已基本遁迹。法国也在20世纪60年代即从刑法中删去了新闻诽谤和侮辱的条款,仅在《出版自由法》中保留了惩处的相关规定。可以说,对新闻侵权而处以刑罚的规定被民事赔偿责任所代替,已经成为国际通例。
据著名学者陈志武教授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发生新闻官司时,中国新闻界的一审败诉率远远大于美国的媒体官司。他选择了中国法院判决的132个新闻侵权诉讼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媒体一审败诉率高达69.23%,而美国近30年来媒体遭名誉权诉讼时败诉率为8%,也即胜诉率为92%。当公众人物(包括政府官员)以名誉权被侵害为由起诉媒体时,在中国媒体的败诉率高达71.68%;而一般公众起诉媒体时,媒体败诉率也达到了62.16%,比前者略低了不到10个百分点。但在美国,如果是公众人物状告媒体侵害名誉权,媒体败诉率仅约4%;而如果是普通公众起诉媒体,媒体败诉率则达到了24%。
大多数情况下,英国媒体可以自由地报道案件审判过程中的任何方面,但在报道时也不是没有限制条件的,如不得侵犯个人名誉、家庭隐私,像录音、录像、摄影等现代高新技术设备不能带入法庭。在有关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案件,1933年颁布的《青少年法》、1960年制定的《司法法》都规定不得报道任何与未成年人监护程序有关的案件,不得披露青少年姓名、住址、学校等有助于识别身份的信息,不得披露青少年的照片和影像资料等,也不得披露被指控的犯罪实情,证人、律师、代理人姓名,保释情况等等。
在美国,解决传媒与司法的冲突,经历了为体现法院审判的独立性而对大众媒体报道进行限制,甚至以藐视法庭罪等处罚媒体的报道自由,到寻求体现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和公平审判的平衡点的转变过程。总体上看,将尊重公民的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权利放在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1941年以前,美国法院对出版物藐视法庭罪适用的主要是两个原则:一是审而未结原则,即案件尚在诉讼进行时,不得出版针对法庭和法官的批评性言论,也不得发表未加证实的有关案情的消息。二是合理倾向原则,即出版物的言行只要符合法官所认定的可能影响司法运作的“合理倾向”,就够得上处罚。而1941年联邦最高法院对Nye v.United States一案的判决中已对合理倾向原则作了限制和事实上的否定,并在同年著名的Bridges v.California一案的审理中首次适用了“明显且即刻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原则。此后,无论在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以藐视法庭罪对待媒体的批评报道,实际上已失去了作用。

在美国,由于对媒体所代表的出版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的尊重,自1976年New York Times Co. v.Sullivan一案开始,正式区分了媒体批评个人与行政官员所涉及的法律案件适用的不同情形。通常政府行政官员会通过诽谤诉讼来回击媒体的批评。但从此案开始适用更为严格的标准,即是否属“实际恶意”原则。
1950年以后,美国联邦法院在限制以藐视法庭罪起诉大众传媒言论批评行为的同时,开始将关注的重点从保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与尊严逐渐转向保护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权利,防止大众传媒大量的对案情有明显倾向性的报道、消息披露对陪审员的影响,从而使被告难以获得宪法第六修正案所确认的受到“一个公正的陪审团”审理和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的保障。
最典型的是1966年Sheppard v.Maxwell案。该案被告人塞姆•谢泼德医生因涉嫌杀害已有身孕的妻子而被捕。此案公开后,立刻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强烈反响。而在谢氏正式被逮捕前,就有大批报纸认定他犯有谋杀罪。在其被捕后,媒体的此种结论性报道越发铺天盖地,诸如“邻居揭露谢泼德有‘性伴侣’”、“车库发现血迹”等消息和评论频频出现,吊足了读者胃口。在整个庭审过程,媒体更是紧追不舍,对包括陪审员选任、举证质证等细节,媒体均事无巨细地披露渲染。而主审法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保障陪审团不受媒体与社会舆情的影响。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对谢氏做出有罪的判决才基本告歇。由此,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初审法院未能及时保护谢泼德免受有明显倾向性的报道影响陪审员的独立判断的不作为,违反了正当程序,剥夺了谢氏享有的公正审判权。为此,做出了无罪裁决、予以释放。最高法院并指出,初审法院应控制向媒体的信息披露,应当签发禁言令以防止庭审当事人等在法庭外发表不当言论,以影响陪审团的公正判决。
为保障被追诉人有获得公正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应当针对审前的过多报道采取预防或消解措施。在美国,具体的方法大致有:一、发布“禁言令”。即申请法官签署命令,禁止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向公众谈论敏感的案件,防止公众舆论对审理程序的公正性及程序的尊严造成损害。二、对媒体事先限制。即禁止媒体报道任何有可能威胁被追诉人公正审判权的内容。不过,针对媒体的限制令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限制的范围也由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然而,就是这种限制令也常常被最高法院所否决,体现了更尊重新闻自由这一宪法权利的至高性。三、预先甄选。即对陪审团成员进行预先甄选,以确保组成一个没有偏见的陪审团。四、陪审团指示。这是指法院可以给予陪审团特别指示,以减少媒体对案件审判的过度报道所导致的偏见的影响。五、隔离。即法院通过限制陪审团接触审判外的信息试图确保陪审团能够完全依据法庭上出示的证据做出不偏不倚的判决。六、延期审理。是指初审法官为了保障陪审团无偏见地做出判决,而推迟审判日期,待舆论减弱,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后,再行启动审理程序。七、变更审判地点。即初审法院可以将案件移送到另一个未受到新闻报道影响的地点进行。
我国直到目前尚未出台《新闻法》、《出版法》,对传媒涉及司法关系的法律界定及其依据,主要还是以《宪法》、《民法》、《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作为参照。而《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1997年修订)中,也只是概略地提出要“积极、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并未就传媒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地位和权利依据给予界定和肯定。尽管第三条单列了“遵守宪法、法律和纪律”条款,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宣传纪律”,“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前作定性、定罪和案情的报道;公开审理案件的报道,应符合司法程序”。但传媒单位和记者自身对司法审判活动报道监督的权利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要尊重司法机关上,而没有认识到尊重司法独立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内在联系,没有认识到这与传媒报道维护社会公义的本质目的是一致的。而在具体的司法规定和运行中,更是缺失明确的法律规定。由此,传媒与司法之间将长期隐伏着紧张乃至冲突的关系。
中国传媒界面临司法纠纷日益走高的趋势,表面上看,是传媒报道引发(不论正面还是负面)的结果,而折射的是整个社会对传媒权利缺乏法理认同和法律保障的观念;更深层次看是在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更多关注了具体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而忽视法律精神和法律文化的培育。传媒所代表的知情权、发布权、监督权等是法律体系建设和公民法律意识培养中首要确立的观念。传媒权利被侵害和剥夺,就是对公众权利的侵害和剥夺。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韦尔伯•施拉姆指出:“如同国家发展的其他方面一样,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只有在适当的法律和制度范围内才会最合理、最有秩序地进行。”
因此,建设法治国家固然要看立法数量多少和体系是否完善,但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人民对法律精神的终极追求和普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