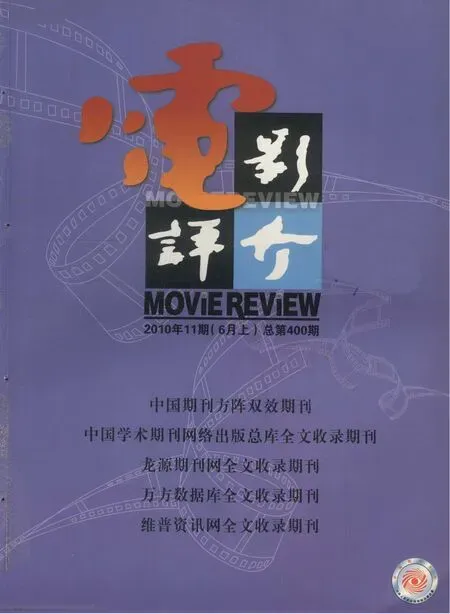视觉文化语境下的底层叙事跨媒介转换——以电影《盲井》对小说《神木》的改编为个案
刘庆邦小说《神木》获得老舍文学奖,导演李杨据此改编的电影《盲井》同样取得了成功,这两个文本可以说是底层叙事跨媒介转换的突出代表。本文比较《神木》和《盲井》叙事结构和叙述方式的异同,揭示电影对小说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对主题表达的影响,并以此为突破口分析底层叙事跨媒介转述背后的文化逻辑。
一、叙事结构元素的重组
首先,情节的变化。情节是叙述者在因果关系和时间上对故事事件的重新安排,可以压缩、拓展或者改变故事,从而使故事重心发生变化。希区柯克认为,电影是把平淡无奇的片段切去后的人生。与小说相比,电影叙事节奏更加明快,更注重悬念的营造。《盲井》开头是宋金明、唐朝阳钓元清平的经过,而《神木》直接以元清平被杀作为第一场戏,一开头就通过残酷的井下杀人吸引了观众眼球。电影还增添了一些富有戏剧色彩的情节,如《盲井》中对宋、唐引诱元凤鸣同行的经过做了详细叙述,从中表现唐朝阳的狡诈和唯利是图、元凤鸣的老实单纯和宋金明的良心未泯。
其次,人物的更改。人物是叙事要素中的重点,马丁所谓“一条导线”[1]。参照格雷马斯矩阵,本文将故事中人物列表如下:

小说中,作恶者宋金明一直面临着为善和作恶的激烈挣扎,他与唐朝阳在狡诈、残忍的程度上不分上下,但在回家探亲后产生强烈的罪恶感,人性逐渐复苏,对元的救护是灵魂的自我救赎,他最后的自杀更是良知醒悟的标志。而电影中,宋金明一开始就显现出与唐的不同,他关爱家人、良知未泯,被元凤鸣的单纯善良感动,从精神分析来说,他对元的回护还带有某种“移情”、“自恋”的意味,一直不忍下手。元凤鸣的位置在上表中有两处,小说中他和父亲元清平一起,站在“受害者”一方,而电影中他处于一个灰色地带。小说中元凤鸣学生气更浓,,有些自命清高,宋唐死后,他主动向矿主说明真相,尽管最终一无所得空手离开,但对良知的坚守仍透露出人性本善的光芒。电影中,元单纯善良不变,初步产生对女性身体的向往,更符合青春期的特点,也增强了电影的观赏性,但最值得关注的改变是,他步上宋唐的后尘,在二人死后,以沉默作为一种谎言,从矿主那得到了抚恤金,在此这单纯少年似乎已经被罪恶染黑,从“受害者”一方移向“作恶者”,他的“被动为恶”使电影故事更加黑暗。
再次,环境的异同。在巴特的研究中,环境与人物行动一起被纳入情节框架,环境指构成人物活动的客体和关系,是故事结构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神木》和《盲井》都刻画了煤矿周边荒凉的风貌和黑暗逼仄的矿洞等自然环境,主要不同在对社会环境的展现上:《神木》主要通过宋金明、唐朝阳的所见所闻使人物与煤矿之外的社会发生联系,如小说第7节老乡的“教育”解释了宋金明和唐朝阳走上这条犯罪之路的直接原因,赵铁军可能遇害失踪,村长叮嘱在外千万小心,第8节唐朝阳钓“点子”遇到同行,这些描画出一个人心惟危、尔虞我诈的可怖社会,恶的主要表现是道德败坏者谋财害命的行径。《盲井》则通过电视新闻、矿主的话语等等,从侧面展现了整个社会环境从上至下的腐烂面,把罪恶产生的根源直接指向了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和丑恶风气,影片因此带上了意识形态批判的色彩。
二、叙述视角的变化
当代叙事学将叙述视角分为“谁看”与“谁说”,申丹分别称之为叙述眼光和叙述声音。叙述声音——叙述者,谁在“说”故事。《神木》中的叙述者属于弗里德曼《小说中的视角》所分八类的第一种“中性全知”,整体展现人物所见所闻所感,不仅对各个人物的每个行动了如指掌,还常常直接叙述各个人物的心理活动。《盲井》叙述者同样外在于故事,镜头运用拟纪录片,采用弗氏第七种“戏剧方式”,追求一种客观纪实的效果。叙述眼光——叙述聚焦,透过谁的眼睛看待其他人物和所发生事件。《神木》主要采取零聚焦,也就是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事,而在第二节宋金明钓“点子”、第四节杀元清平、第七节回乡过年三个章节中,采用了固定式第三人称内聚焦,让读者跟随宋的眼光感受周边的一切,增强代入感,使宋最后的觉醒在逻辑上显得真实可信,更好地表达了小说人性复苏的主题,《盲井》则全部采用外聚焦,电影的特性使人物的感受直接通过画面传达,如元凤鸣偷看半裸女图画的动作、招妓后独自在澡堂洗澡的微笑和失神等都可以传达出他此时的心理动态。而外聚焦的影像传达使观众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能据前后情节揣测人物心思,很难预料人物下一步行动,增强了戏剧效果,更能吸引观众。
三、叙事介质的不同
小说以文字为唯一的叙事介质,电影叙事手段则极丰富。小说是线形展开的历时性叙事,龙迪勇在《时间性叙事媒介的空间表现》一文中谈到,由于感觉世界的整体性,在同一单位时间内,我们的意识中可以出现许许多多的事件,这些事件本身处于一种共存性的状态之中的。为了便于把握,我们必须把共存性的经验转化成相继性的经验。自然,经过这种转化之后,事件会呈现出一种线形排列状况,这正适合语言文字这种线形的叙事媒介来加以表现——遗憾的是,这种表现已经远离了意识的原始状况[2]。因此,小说在表现世界的纷繁意象上逊色于电影。电影的具像性使线性符号中存在的故事在转换成共时性的空间画面时,传达出比小说更丰富、更复杂的信息。《盲井》画面摄影采取了纪实风格,大量的跟拍、尾随长镜头,往往展现全景画面,这使观众产生现场观看的拟真感。矿洞戏也独具匠心地运用了矿工头顶的矿灯作为光源,这种小灯刚好相互照亮脸庞,既令人感到真实可信,又使人脸得以显现在矿洞暗无天日的背景中。在杀元清平一场戏中,三盏小灯发出昏黄沉闷的光将三人笼罩其中,唐朝阳和宋金明身体隐在黑暗中,仅仅显出模糊的脸庞,表情隐约狰狞,环境的阴森和弥漫的杀气立刻扣住了观众的心。再者,《盲井》中人物口音、画外音等各种声音也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叙事效果,如片中大部分人物说一口夹杂大量俚语粗话的方言,这切合人物的底层身份,形象更加真实;再如唐朝阳杀元清平时,鹤嘴锄在矿石上划出尖锐清晰的撞击声,在沉寂的矿井下听来格外惊心,这成为一个杀人的信号,过后每次听到这一声,观众都会绷紧神经,等待预期的杀戮,增强了紧张色彩。
四、主题的延异
延异(différance),是德里达所创造出来的“非概念的概念”,指运动和变化中的差异化本身。本文套用他的理论认为,小说一旦被制造出来,就成为鲜活的文化生命体,它具有被阅读、被分析、被阐释的无限可能,更在跨媒介的影视化转换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阐释空间。从《神木》到《盲井》,主题呈现出一条延异之流,这其中有几个突出点。
首先是人性的平面化。底层叙事对人性的书写始终是重中之重,表现底层就是要表现在恶劣的生存状态下人的挣扎和奋斗,从而体现人性的伟大和人的尊严。正如洪治纲[3]诗意的表述,“书写底层生存的苦难时,叙事话语中始终洋溢着某种宽广而温暖的人性。这种人性,超越了日常伦理的规约,甚至屏蔽了简单的道德判断,仿佛岩隙中的甘泉,从生命里自然而然地缓缓涌出,悄无声息地浸润着读者的心扉”。刘庆邦的小说原著不乏对人性透彻的理解和真诚的关注,而电影由于叙事时间有限,并往往只能以外聚焦的方式展现人物言行举止,人物显得比较平面化。以宋金明为例,《神木》相当深刻地写出了宋的悔悟。他的人性复归来自内心的罪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灵魂煎熬过程。他一开始只知卖力挣钱,受引诱走上犯罪之路,但一直受到良心的煎熬,回乡探亲的见闻加重了他的罪恶感,他杀害了元清平,被害者的儿子现在又落到他手上,让元家“绝后”的不安促使他进一步反省自己的罪孽,最后终于以自杀作为对自己罪孽的救赎。这一个过程总体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充分表现出人性的复杂。而《盲井》中,宋一开始就毫无理由地处处表现出比唐朝阳更高的道德水准,更轻易被元凤鸣感动,呈现出护犊姿态,因庇护凤鸣受到唐朝阳猜忌,冲突中被杀。宋的积极向善显得太直奔主题,感染力和现实感较弱。
其次是苦难的表层化。塔可夫斯基曾说:“人类天赋的良心使他在行为与道德规范相抵触时饱尝煎熬,这么说来,良心本身就包含了悲剧成分”[4]。底层民众的悲剧往往并不仅仅是生活的重压本身,痛苦的体验更来自为谋生而不得不做违背良心的事情。刘庆邦小说把眼光向深处穿透,表现了向城求生的务工农民在合法收入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被迫异化成底层的食肉动物,吞噬比自己更弱的同类,承受着良心与欲望分裂所带来的撕裂之痛。这是社会的断裂与分化以及人性本身所造就的深层次的苦难。而《盲井》中,底层的苦难似乎就仅仅源自被压迫被欺凌的生存状态,例如唐朝阳所说“这井下的罪实在难受”,他虽然杀人,但看不出有多少罪孽感;宋金明把“给孩儿挣钱交学费”随时挂在嘴边,把杀人的恶全归咎于社会不公,似乎这样就有了某种合理性。人物的痛苦来自外部,看不到人物灵魂焦灼的痛苦。
最后是社会批判的强化。电影在人性探讨的深度上不如小说,但社会表现广度更大。例如片中矿主听说井下出事,家属要抚恤金,帮闲直接就建议“把他们给办了”,矿主不想找公安部门和有关单位来解决矿上事故问题,因为“这些货一来,吃、喝,还要拿,没有十万八万根本下不来”,另一矿主直言“吃饭就得拉屎,下井就得死人。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宋金明看到电视里贪污犯审判的场面,说“贪污了几百万,枪毙了都不冤,我要有个几十万,都给孩存起来读书”。 这些台词配合画面极具感官冲击力,给观众留下强烈的印象。通过这些对白,影片展示了社会的不义、官僚的腐败、既得利益者对底层大众生存权利的蔑视,社会批判的态度更加鲜明。
综上,本文通过对小说《神木》与电影《盲井》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在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上差异明显,并产生主题的延异。而这反映出当下社会大众文化心理状况。
正如詹姆逊所言,当前时代的特征是把现实转化为影像,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当今社会,视觉文化统治了大众生活[5],对“看”的倚重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人类创造文化,使用符号来表达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文化主导形态的变化体现了人类生存状况的变化。人类文化不再是“内容”的,而是“外观”的。马歇尔•伯曼曾说,“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于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冒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6],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却发现,在获得自我创造的能力和机会的同时,失去了对终极审判的畏惧,对永恒价值的追求,对不朽的向往。如果说现代社会中人还可以用理性作为理解世界和人本身的坚强依托,那在后现代社会,这块最后的精神基石也逐渐风化消逝,人们无力把握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退回到自己的小壳里,不再渴望进入世界,而是要求世界进入人,以“看”与“被看”与外界沟通。纷繁复杂的物象化为一目了然的图像,电影每秒24帧的变幻频率正契合我们对瞬间感受的追求,抽空了一切深沉的思考,不想也无力作为主体去经历和感受,只要在被动的观看中得到满足。这样的时代,小说流传的范围和接受程度远远不如电影,文学叙事通过影像媒介传播,可以扩大影响力,获得更丰富的阐释。但电影对小说的改编是全方位的,不仅是传播介质的变化,更从情节、人物、视角等各方面都发生改变,乃至故事的核心主题都被重新诠释和表达。
近年来,底层的惨淡处境引起了大众的注目,知识分子积极为底层代言,涌现出大量底层文学,而电影对小说的改编则扩大了底层叙事的受众面,通过富有震撼性的影像冲击,直观展现底层的艰难境遇,对引起大众对底层的关注热情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值得激赏。但在视觉文化的语境下,当底层的生活状况被搬上银幕,观众不需直面赤裸的真实的苦难,不需要严肃深沉的思考,可以在屏幕的这头漫不经心地“欣赏”他人的生活,还可以从“看”中得到悲天悯人的自我道德升华感,关注底层的生活状态,却宁愿将底层的真实化为变幻的画面,将“他们”和“我”隔离在屏幕两端,仅仅满足于对苦难“看”的体验,这未必是影视创作者的本意,但的确可能是底层叙事影视化热的潜在原因。这其中蕴含着底层叙事被异化的风险。研究者对此应有清醒认识,警惕底层叙事在消费社会演变为一种展览苦难奇观博取眼球的视觉文化商品。
注释
[1]【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人物是一条导线,正是人物使理清母题的乱团成为可能,并允许它们被归类和整理”。
[2]龙迪勇:《时间性叙事媒介的空间表现》,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3]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4]【俄】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陈丽贵、李泳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
[5]这一说法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时代》中,声称世界将作为图像被把握和理解,今天所谓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按照国内视觉文化研究的先行者周宪的说法,视觉文化的基本涵义在于视觉因素,或者说形象或影像占据了我们文化的主导地位。
[6]【美】马歇尔•伯曼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张辑、刘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5页
[1]【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2]【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3]【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文化》,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
[4]【法】雅克•奥蒙、米歇尔•马利:《当代电影分析》,吴佩慈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5]【法】A•J•格雷马斯:《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吴泓缈 冯学俊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6]【加】安德烈•戈德罗、【法】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刘云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7]【法】莫尼克•卡尔科-马塞尔、让娜-玛丽•克莱尔:《电影与文学改编》,刘芳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
[8]【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倪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9]申丹:《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法】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神木大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