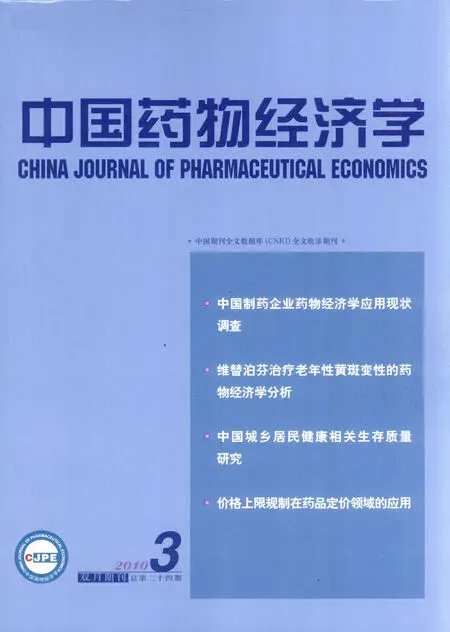价格上限规制在药品定价领域的应用*
常 峰 张子蔚
1常峰,博士,副教授,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产业发展研究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药品价格、医疗保障和药品流通规制政策;江苏南京 211198 2张子蔚,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社会与管理药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药品价格规制;江苏南京 211198
一、引言
价格上限规制的实施是20世纪80年代众多产业规制改革进程中的一项关键措施。从固定价格到价格上限(price cap/price ceiling/maximum price)的转变蕴含的要义是强调价格规制在成本节约上的激励作用,并鼓励创新[1][2]。正因为节约成本和激励创新是药品价格规制者的两项核心任务,因此价格上限规制(PCR)已经越来越频繁应用于众多国家的药品价格规制中[3][4]。
二、价格上限规制
(一)价格上限规制产生的原因
在垄断行业定价方法上,PCR是以投资回报率规制(rate-of-return regulation,ROR)继任者的身份出现的。投资回报率规制以成本为基础,是一种成本加成定价(cost-plus pricing),因其造成厂商生产效率降低而遭受口诛笔伐已长达数十年。对此规制形式最早的正式分析来自于Averch and Johnson(1962)。他们指出,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回报率规制下的厂商在任何产量水平上都不会最小化生产成本,因而产生了巨大的无效率情况。公司甚至会以低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出售具有竞争性产量的产品,以此来建立更丰厚的利润率基础[5]。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PCR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激励性质的定价方法开始在垄断行业的价格规制中出现,试图解决原有定价体系中信息不对称和激励失灵等问题。PCR的实施是这一时期众多产业规制改革进程中的一项关键措施。
(二)价格上限规制的基本理论
价格上限是政府和受规制厂商之间的契约,此种规制允许公司分享由效率增长带来的经济效益,被认为能有效地激励厂商最小化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并追求具有经济效益的创新。规制者可以在一个非竞争市场中设定上限,并允许公司进入竞争性市场中生产任何产量水平的商品。与ROR相比,纯粹的价格上限规制(PCR)破除了回报比例设置和公司成本之间的联系(Braeutigam and Panzar,1993)[2]。在许多系统中,PCR也包含了对回报率的控制,如对公司所能持有的利润率进行控制。这意味着公司可以保留低于某个利润率水平的所有利润,并分享超过这个水平的部分利润。
纯粹的PCR拥有最高价格或一个价格指数的最大值,规制者一般通过外生因素确定这些参数。PCR模型有很多种,其中较为常用的是Littlechild于1983年提出的模型[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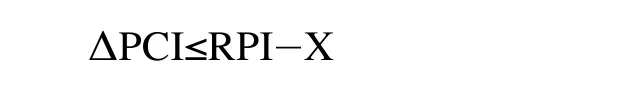
其中,ΔPCI为垄断产品名义价格的变化幅度;RPI为零售价格指数;X为规制者限定的一定时期内的技术进步率。此模型的另一种形式为:

其中Pt+1为第t+1期的价格,Pt为第t期的价格。各国在具体使用PCR时采用了不同的具体形式。
(三)价格上限规制的效果
PCR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一些文献的证实。Coco和De Vincenti(2004)构建了一个两阶段模型,其中公司可以对努力进行重复选择,并且努力对成本函数具有长期的影响[1]。结果他们发现当需求弹性低于某个特定阈值时,价格上限能增加生产效率。此外,他们运用“阿罗效应(Arrow,1962)”证明,在第二阶段开始时进行上限价格审查能导致公司在此阶段投入更多的努力[7]。Coco和De Vincenti(2008)进一步研究了价格上限的价格审查间隔对规制效果的影响。他们认为,在给定特许期范围内,确实存在PCR能够提高成本效率比的情况。同时,在讨论了最佳审查次数与需求函数斜率以及努力负效用等因素的关系后,他们提出审查次数存在一个最佳水平[1]。
另一些文献认为,对上限价格进行审查的效果可以分解为对厂商的激励作用和对福利的分配作用两个方面。周期性的审查允许规制者设置更多的关联价格,有助于激励垄断者在未来实施更多缩减成本的努力;但审查并设置一个新的上限又会降低节约成本的动机,因为它降低了公司适应成本节约所产生利益的时间范围。另一方面,为了将从成本节约中获得的利益重新分配给消费者并获得生产效率,检查和调整又是必须的[8]。因此,Armstrong and Sappington等人总结道[9],规制调整间隔越长,规制的激励特性就越好,但重新分配福利的品质就越差。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1992年的一份报告表明,政府对AT&T实行PCR取得了积极的效果(FCC于1989年7月对AT&T的长途电话费用采用PCR,取代了原先的回报率规制)[2]。采用PCR后,市场竞争性明显增强,电信产业的技术也得到了迅速升级。这种激励性的规制方法避免AT&T和FCC继续深陷于成本检验、成本合理性判别、成本的项目分摊以及合理回报率数值设置等繁杂问题的泥潭当中,同时避免了A-J效应(由于允许的收益直接随着资本的变化而变化,而导致被管制企业将倾向于使用过度的资本来替代劳动等其他要素的投入,导致产出是在缺乏效率的高成本下生产出来的,此即所谓的A-J效应)。
三、价格上限规制在药品定价领域的应用
虽然有不少国家在药品价格管理中使用了PCR,但必须认识到,大部分药品市场不具备自然垄断性质,各国所使用的PCR仅保留了其在垄断市场时的最原始特征,即由规制者制定最高限价。因此,在药品市场中应用的PCR并非是对垄断市场使用模式的完整移植。
(一)价格上限规制与国际基准定价
绝大多数国家将PCR与国际基准定价结合使用,即将国际基准定价作为设定本国药品价格上限的基准。奥地利的新药价格不得超过其他欧盟国家[10]。在爱尔兰,药品的出厂价格不能超过英国相应药品的最低价格;同时也不能超过丹麦、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的平均价格[11]。葡萄牙的药品价格不能超过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最低价格。丹麦可补偿药品的上市价格,但不得超过11个欧盟国家以及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冰岛价格的平均值。意大利的药品价格不得超过12个欧盟国家的平均值[10,12]。瑞士药品价格不能高于德国、英国、丹麦和荷兰平均价格的103%[13]。通常,超过价格上限的厂商必须主动降低价格,退还超额收入,甚至还会受到处罚。
荷兰和加拿大的价格上限系统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其中也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国际基准定价。荷兰于1996年颁布了最高价格法案(Maximum Price Law)。它规定了所有可补偿药品的最高批发价,并根据化合物、剂型和剂量的不同分别计算,且每两年检验一次。这个最高价格是4个参考国(比利时、德国、法国和英国)“具有可比性”药品的平均价格。荷兰的价格规制范围包含了非专利药品,在计算非专利药品的价格上限时必须同时参照原研药和仿制药。仿制药和品牌药具有相同的上限,这一方面会降低价格上限对仿制药价格的限制作用,另一方面也使非专利药的价格上限降至相当低的水平。实行这一政策时,荷兰的药价比欧洲平均价格高出20%,而现在荷兰已成功将药品价格降至欧洲平均水平[14]。
加拿大的专利药品价格检查委员会(Patented Medicine Prices Review Board,PMPRB) 负责制定所有专利药品的价格上限(出厂价),并实行不定期的检查来确保价格没有超过上限。通过上市审批的药品可以自由定价,但当获得专利后,其价格就必须受到PCR的控制。PMPRB在为药品设置价格上限时首先将药品分为3类,分别为:已有药品的新剂量或新剂型品种,由相似剂型和已有计量作为标准来计算上限;突破性药品,采用参照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的中间价格为最高价格;me-too药品和已有疗效相似的药品使用共同的价格上限,没有相似产品存在时,采用国际基准定价[15]。除了上述规定外,PMPRB还要求价格增长不能超过CPI增量的1.5倍[16]。
(二)价格上限规制与参考定价
参考定价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价格上限,即补偿价格上限,或者理解为一种可以通过患者自付得到拓展的价格上限。近年来的一些文献对价格上限和参考定价进行了比较研究。PCR和参考定价是规制者在药品市场最常应用的两种规制政策,二者的目标都是合理控制药品费用:上限规制通过防止厂商索要高价限制了其攫取市场权利的能力;而参考定价则通过增强需求弹性刺激了竞争[17,18]。
Brekke,Grasdal和Holmås (2008)以及Brekke,Holmås和Straume (2008),运用挪威独特的政策变迁对这两种规制的效果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挪威于2000年开始对所有处方药实行PCR。2003年3月开始,一些非专利药品被纳入称为“指数定价(index pricing)”的参考定价系统中,脱离了PCR;而对其他药品仍实行PCR。这为实证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自然试验条件)。纵向差异模型的推导得到两点重要发现:(1)从PCR到参考定价的转变导致了仿制药市场份额的增加;(2)如果PCR不是非常严格,那么这种政策转换还会造成品牌药和仿制药价格的下降和相对价格的下降。这由实证研究的结果得到了良好的印证。实证研究表明,和PCR相比:(1)参考定价导致品牌药和仿制药价格的降低,而对品牌药价格降低的幅度更大,因此造成了更低的相对价格;(2)参考定价通过大幅度降低品牌药市场份额而激发了仿制药竞争;(3)参考定价很大程度降低了相同通用名药品的平均价格,意味着产生了可观的成本节约。因此,他们认为在非专利药市场,参考定价比PCR更有效[17,19]。
Danzon(2001)也具有类似的观点,她认为参考定价会造成药品价格的收敛,而PCR却迫使疗效相似药品的价格更加分散。荷兰同时应用参考定价和价格上限的结果是补偿价格上限最终充当了价格上限,并且补偿价格上限有所下降[14]。
四、对我国实施药品价格上限规制的建议
由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药品市场在价格形成上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通过限制最高零售价来控制药品价格和药品费用是各国普遍采用的手段之一。2000年开始,我国将限定最高零售价格作为主要规制手段。虽然最高零售限价规制从形式上看是上限规制和成本加成定价的结合体,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价格调整机制(价格调整时主要依据的依然是生产成本),制药厂商没有得到明显的生产效率改进激励。因此,我国的最高零售限价规制在本质上更接近基于成本加成的投资回报率规制。实行标准的PCR有利于对制药厂商改进生产效率产生必要的激励。
(一)实行药品价格上限规制的基本建议
不同药品的市场结构不同,需要根据药品的市场结构特征来确定其是否适合采用上限规制以及具体如何进行规制。
首先,在具有垄断结构的药品市场中,目前的基于成本加成的定价方法对制药厂商很难产生成本节约的激励作用,采用标准的PCR将有助于改善这一状况。因为PCR最初的设计就是针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改进的,所以在这类市场中用PCR取代目前的成本加成的投资回报率规制是合理的。能够形成垄断市场结构的药品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其治疗领域内没有可替代的药品,或者替代药品的疗效或安全性明显劣于该药品;二是该药品的市场进入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如在专利期内属于创新型专利药品的情况,或者虽为仿制药但属于首先仿制且被仿制药品尚未在国内上市的情况。国家为制止仿制药市场的无序竞争,开始在政策上对再仿制药品的定价进行更严格的控制。最新颁布的《改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发改价格[2009]2844号)规定:对今后国内首先仿制上市的药品,价格参照被仿制药品价格制定;被仿制药品在国内尚未上市的,首先仿制药品的价格依据其合理成本制定。再仿制上市的药品,价格按照低于首先仿制药品价格的一定比例制定。这会抑制厂商再仿制的动力,从而使得首先仿制的药品可以在市场上有相对的垄断性。
其次,在具有一定竞争性的药品市场中,目前的基于成本加成的定价方法对于生产效率是具有一定激励作用的。但是,由于需要政府核查的药品多达数千种,涉及的制药厂商也有数千家,成本核查工作量非常巨大,进行一轮成本核查至少需要花费几年时间。虽然药品价格管理部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仍然很难及时地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如此多药品的价格进行调整。最近几年药监部门出台的很多新规定,对维护市场秩序和患者权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药品价格却未能获得及时的调整。因此,在具有一定竞争性的药品市场上,实行PCR一方面有助于减少药品价格管理部门的工作负担、简化管理程序,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强对制药企业成本节约的激励。
最后,对于在国际上领先的原创性药品,我们不建议在专利期内实行PCR,而是由企业自主定价,专利期过后再根据市场结构决定其是否需要采用PCR。这样有助于确保对药品研发的足够激励,有助于最终提升我国医药产业的竞争力。
(二)药品价格上限规制设置方法的建议
PCR的结构主要包括基准价格的确定和价格调整机制两个方面。
基准价格制定可以依据成本加成的方法,也可以依据参考国际同类药品的价格。鉴于我国药品价格水平在国际上依然偏低,因而主要以成本加成的方法来确定基准价格仍然是恰当的。但对于在国际上有同类产品的创新型药品,可以参考国际同类药品的价格作为基准价格。
价格调整机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基准价格重新核定的周期,二是药品名义价格公式的确定。对于基准价格的核定周期,我们认为,近期可以依据药品成本核查部门的工作周期来确定。对于药品名义价格公式我们建议可以考虑两种方案:一是使用Littlechild建议的名义价格公式,即Pt+1=Pt(1+CPI-X)[6]。这需要我们认可药品价格可以与其他竞争性市场中的商品价格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同时我们还需要以某种方式来确定各类药品的技术进步率。二是使用公式Pt+1=Pt(1+EMPI),其中EMPI是基本药物价格指数(基本药物价格指数是我们创造的概念,可以根据我国的基本药物目录内药品的价格变化来确定,由于基本药物的价格是通过一省一制的集中招标产生的,价格信息准确且易获取,确定基本药物价格指数并不困难)。由于基本药物的质量差异相对于其他药品不特别重要,因而基本药物的招标价格是得到充分竞争的价格,它的价格变化能够反映药品市场价格的正常变化,所以以这个指数来确定其他受规制药品价格的正常变化是合理的。
五、结束语
PCR最早是针对自然垄断行业,作为投资回报率规制的替代制度出现的,它较好地解决了自然垄断行业效率激励不足的问题。随后,这种规制方法逐步扩展到更多领域,包括由政府规制的非垄断行业。本文根据我国药品市场的基本状况,有针对性提出了在我国药品价格中使用PCR的具体建议,以期对我国药品价格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尽绵薄之力。
[1]Coco G,De Vincenti C.Optimal price-cap reviews [J].Utilities Policy,2008,16: 238-244
[2]Braeutigam R,Panzar J.Effects of the change from rate-of-return to price-cap regulation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3,83(2):191-198
[3]Danzon P M.Pharmaceutical Price Regulation:National Policies versus Global Interests [M].Washington: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Press,1997
[4]Kanavos P.Overview of pharmaceutical pricing and reimbursement regulation in Europe [R].Report for a project sponsored by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DG Enterprise,February 2001
[5]Averch H,Johnson L.Behavior of the firm under regulatory constraint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2,52:1053-1069
[6]Littlechild S.Regulation of British Telecommunications Profitability,London:HMSO,1983
[7]Coco G,De Vincenti C.Can price regulation increase cost-efficiency?[J]Resarch in Economics,2004,58:303-317
[8]Green R,Pardina M.Resetting price controls for privatized utilities.A manual for regulators [R].World Bank,Washington,DC.1999
[9]Armstrong M,Sappington D.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y of regulation [A].In: Amstrong,Porter(Eds.) [C].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07,3:1557-1700.
[10]Martikainen J,Rajaniemi S.Drug reimbursement systems in EU Member States,Iceland and Norway[R].The social insurance institution,social security and health reports,2002,in Finland.ISBN: 951-669-612-0
[11]Barry M,Tilson L and Ryan M.Pricing and reimbursement of drugs in Ireland.The European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04,5(2):190-194
[12]Haga A,Sverre M.Pricing and Reimbursement of Pharmaceuticals in Norway [J].The European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02,3(3):215-220
[13]UK’s Office of Fair Trading.International survey of pharmaceutical pricing and reimbursement schemes[R].An annexe for OFT’s report: An OFT market study of Pharmaceutical Price Regulation Scheme,2007
[14]Danzon P.Reference Pricing: Theory and Evidence[A].Lopez-Casasnovas G,J nsson B.Reference Pricing and Pharmaceutical Policy: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s and Innovation [C].Barcelona:Springer-Verlag Iberica,2001:86-126
[15]Menon D.Pharmaceutical cost control in Canada:does it work? [J]Health Affairs,2001,20(3):92-103
[16]Paris V.,Docteur E.Pharmaceutical Pricing and Reimbursement Policies in Canada [R].OECD Health Working Paper,No.24,2006
[17]Brekke K R,Grasdal A and Holm s T H.Regulationand pricing of pharmaceuticals: Reference pricing or price cap regulation? [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8,doi:10.1016/j.euroecorev.2008.03.004
[18]常峰,张子蔚,赵雪松.国内外药品价格规制政策述评[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9(4):49-50
[19]Brekke K R,Holm s T H and Straume O R.regulation,generic competition and pharmaceutical prices [J/OL].working paper,File URL: http://www3.eeg.uminho.pt/economia/nipe/docs/2008/NIPE WP 1 2008.PDF,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