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浩:我是说实话的既得利益者
燕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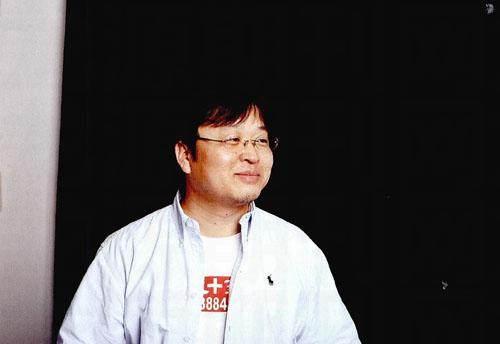
你做批评就是做实事,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一个文人你不希望他批评,难道希望他从政吗?
不知从何时开始,1972年出生的吉林小伙罗永浩就被人称为“老罗”了。
“老罗英语培训”位于北京新中关大厦12楼,他亲自设计的招生广告闪烁在附近地铁过道的灯箱上,会议室里还看得到老东家“新东方”的北京总部。2001年3月至2006年6月,高二就退学、自学英语的老罗在“新东方”当起了GRE培训教师,他的“一哥”地位直到离开前半年多才被一位新来的词汇老师改写。
老罗活泼、幽默且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授课内容被新东方的学生们悄悄录音,并于2003年左右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由于我的没出息,第三年我就应该走了,但是为了养家糊口,又忍了两年。”2006年6月,五六十万元的年薪再也阻挡不住老罗对自由天性和“舒服”境界的追求,他不能忍受上市在即的“新东方”的日趋商业化以及对最初理想的背叛。
老罗和“新东方”的恩怨并没有写入新近出版的自传性作品《我的奋斗》。离开“新东方”两个月后,老罗开起了云集各界明星博主的“牛博网”,并在2007年关注厦门PX项目和拯救黑窑奴工及2008年汶川大地震募资捐款的活动中出力甚巨。
2008年5月,老罗又开起了“老罗英语培训”,合伙人黄斌从尼日利亚经商归来,这位发小的几百万元投资被轻而易举地拉来完全归功于老罗“人格的力量”——黄斌告诉他:“当年我换毛片看的所有朋友里,你是唯一一个从来不把长的转成短的来骗我的。”
自2009年年初关停的“牛博网”还在等待着第五次开张,老罗像他的朋友韩寒一样编起了同名杂志《牛博》,8月就要面市了。老罗粉曾轶可,仅仅因为她的歌声中“那种带有缺陷的、朴素的、打动人的东西”,所以不遗余力地说服周云蓬、张玮玮等人帮她录歌,但他并不介意曾轶可不能参加《我的奋斗》在北京的首发式;他和他的同事还正筹划着组建一个乐队。
为了回应网友质疑,老罗郑重其事地主动“召回”《我的奋斗》,但迄今只收回两本退货。后续印刷中,老罗的专业精神细化到纸张的选用。这个应试教育的成功叛逆者的自学能力很强,小到出版细节,大到培训机构的管理,都是自学得来的。
老罗自信,不乏骄傲,竭力追求他推崇的善良、诚实以及所有“年轻时认为的那些正确的、美好的、理想的东西”,他做人的目标应该就是将自己和那些缺乏这些美德和操守的各色“流氓”区别开来,他欣赏的“成功人士”是“只要自己活得开心,而且坚持了自我”。对于《我的奋斗》的报道和评介并不鲜见,但显然,网上一位“80后”的评语“大朋克罗永浩”最得老罗的心。
两个小时的采访进行到最后,老罗实在坐不住了,站起身答问的他还真有点马上就要去“亲自授课”的架势了。
在中国,很多东西都是对付
《新民周刊》:你说如果有不满意的可以退这个书,有读者退过吗?
老罗:现在就退了两本。当时定这个规矩,我们同事还紧张,现在发出去了10万册左右,万一退个一两万怎么办。我说不可能,退个一两千都不错了,3000本就是极限了。
《新民周刊》:(老罗接电话……)刚才听你打电话,你对纸张的型号、厚薄什么的很了解。
老罗:对。我开始做公司之后,感到在中国有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就是从事专业技术工种的人全都很不专业。这个是我们国家发展状况决定的。你去印刷厂,比如我们去找设计师,我让他给我出一张图,发现这个家伙做了4年设计,操作Photoshop会的快捷键没有我多,这就很让人寒心。
一个小伙去印刷厂跟我追色,这个在发达国家是难以置信的。比如我有个朋友“老六”张立宪编《读库》,每一册出来他都半夜去印刷厂盯,现场调色,因为不能放心那些人给你调的色。
张立宪是个编辑,那儿调色的是专门的技术人员,结果你一个吃专业饭的调得不如我一个文字编辑。这个没有技术含量,就是你不用心。
《新民周刊》:你对这些技术细节这么熟,是因为这次出书吗?
老罗:不是,有些是以前知道的,关于图书出版的知识很多是被迫硬着头皮自己去研究的。其实我只是Google了两天,基本就明白了。但是那帮孙子,他们的特征就是全都给你对付。在中国,很多东西都是对付。
这书第二批印的总共7万册,光盘有半数左右是不读盘的,那是光盘厂那边出了问题,他们也承诺有问题的都给免费调换。但是毕竟恶劣影响已经出去了,所以我后面印的,印厂是指定的,纸张是指定的,然后负责的技术人员有必要的话也是指定的。在中国,你要想把一件事情做得好一点,你就会很痛苦,因为所有人都在奉行一个原则:差不多就行。
我的动机不那么纯粹
《新民周刊》:我读你的书的时候有感动的地方,即人的可能性跟人的有限性。人的有限性,就是不一定这个人他的品格多么高尚,可能就是因为一些很世俗的原因,客观上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你要有坚持,不“助纣为虐”,在合适的机缘下还是能做成事情的。
去年巡讲的时候,当时专门要求挂一个横幅,说你这是“非公益”的演讲?
老罗:对,去年高校巡讲是我以培训学校的名义去讲的,那到这些高校去你就是为了商业,但是高校不允许你上去演讲推荐产品,但他不排斥你是一个企业家。
那像李开复这种就可以假裝青年导师,整天跟你讲什么“成长的10个启示”,讲一些陈词滥调的人生观。讲得没什么意思,但是他是个企业领袖。其实也不是企业领袖,就是个打工仔嘛。
不管你是“打工皇帝”还是企业老板,你去高校讲这些东西,肯定或多或少是有商业目的的,那你不提不就好了吗,你就说我是一场演讲。但是这帮家伙很喜欢打上“公益演讲”。你心虚个屁,高校没有要求你必须打上“公益”,你自己不要脸然后还在那打“公益”,就是很伪君子,我看不惯这个。
在我们英语培训行业里,半数以上的都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我去登台演讲就有个心理障碍。我们可以不讲商业内容,但是我来还是间接地为了商业目的。
所以呢,我注意到他们都在打“公益”,我就想打个“非公益”以示区别。你也可以认为这是炒作,没有问题,它具有话题性。我每次做事情的时候,动机都不是那么纯粹的,但是我不介意,为什么呢?因为我做这件事是诚实的,同时我提到了宣传、炒作的作用,不会为此觉得不体面、难堪或者良心不安,没有任何问题。
《新民周刊》:你有这种强调和区分。而我会经常关注一些图书排行榜,觉得中国存在一种大面积的人格分裂,不单单是那些高级白领,他们可能迫于工作压力会看一些讲养生讲生活方式的书,但是他自己的工作方式就是不健康不环保的。甚至知识分子在上电视做嘉宾时讲一套,现实生活中他可能去跟人家争教授职称、一些科研项目,总是反其道而行之。而且对于这种犬儒主义,他会有借口说不得已啊,迫于生存压力。
老罗:对,这个社会到处都是那些脑子分裂、精神糊涂的这种人,比如他自己每天干那些缺德事、违法的事去赚钱,但是对别人一些个人的选择还强烈地鄙视。你整天干那些生小孩没屁眼的缺德事,结果你还觉得比人家高尚。就是特别分裂,而且完全不自觉,全是这种人。
《新民周刊》:是不是还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商业发展和一些利益分配环节的驱动,也可以形成一个机制来鼓励大家讲真话,或者尽量不违心尽量不讲假话?
老罗:整体上还是高风险的选择吧,至少在起初的时候,必须有你信奉的一些东西来支撑才可以。但是到了一定阶段,有人因此获利了,比如我,那么后边就更容易了。但是在起初的时候,如果是为了就像你说的有一个奖励机制鼓励更多的人愿意去说实话,这个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你在中国,单纯是为了生存方面的好处、现实利益的好处的话,说实话是高风险的选择,撒谎、同流合污是一低风险的,所谓升官发财的成功也是可以预期的。
《新民周刊》:我来的时候看见你们公司的广告,也看到很多“新东方”的,你当初因为“新东方”上市前有很多商业化的行为而退了出来。那你现在这个培训机构慢慢壮大,到时候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老罗:起步的时候是最艰难的,起步的时候面临的是生存与死亡,将来就是多挣少挣的问题,你要耍个流氓,今天就是20亿,你不耍流氓,今天就是15亿,那5个亿他怎么舍得放掉呢?但是我现在启动资金只有300万,是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就做到了。我们的员工一辈子没有用过正版的Office,是到我们这里才第一次用的。
加班全部给加班费,而且是主动打到卡里的。你看他们其他企业,还是上市企业,要经过5到6个部门带有侮辱性的手续后才能领到加班费,使得很多人主动不去领加班费。而我们是主动打进卡里的,我们没有赖过一分钱。其实我们加班也不多,就是偶尔,而且我们“五险一金”,签了正式劳动合同。
我经常和我的员工在开会时吹牛皮,说我们这个企业虽然不大,但是所有的都是大企业(的做法)。除了规模不大,所有都是大企业。而且我们会计做一套账,这也是他们想不到的。在中国有多少国企只做一套账的?我之所以这样也能做下来的原因是,我选择上的明智。教育培训在中国年年当选十大暴利行业,这也是为什么让出一部分利润,我们没有倒闭的原因。
如果我们去做制造业,制造业利润3%~5%,按我这个方法去做,肯定做不到就倒闭了。这个期间我是很焦虑的,每周平均睡觉不超过40小时,如果一旦赔光,以我的性格,肯定要到处打工,把我这300万的债务还上。虽然法律上不要求还,事先要求不要还,但我丢不起这个人。因为机构投资是纯粹赤裸裸的商业行为,但是朋友的钱是有信用在里面的。说是投资,但是真的一旦赔了,你也不好意思不还给别人吧?你把这个钱还上,你才是一个牛逼的人。马克·吐温就是这么做的,马克·吐温做生意赔光了,破产了不用还那个钱,但是他丢不起那个人,所以他下半辈子到处去写书做宣传,做演讲,把这个钱还上了。我肯定也是这样的,年底发双薪的时候我的手是抖的,因为我一直在亏损,每个月最多亏的是20万,但我还是给他们发双薪,就没有耍过一点流氓。
很多失败是外部因素造成的
《新民周刊》:一路走来,你对理想主义的宣扬和实践让我很有敬意,但是这也会跟机遇这种小概率的东西有关,比如做牛博。
老罗:跟经验也有关系。
《新民周刊》:你的朋友黄斌给了你投资,如果没有这样一些人在这个时机出现,有可能你现在就在做不一样的事情。
老罗:对,可能会做得更吃力。所以,我就特别讨厌那些成功人士升了官发了财,然后出来讲,你只要努力就能成功,你只要没成功就是不努力。我们失败的时候,有很多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当然主观因素也很重要。你成功了固然有你努力的内部因素,但外部因素也同样重要。有的人就是比你聪明,生意做得比你好,但是他接二连三地碰到意外,那你还怎么搞呢?
《新民周刊》:要对人性有足够的估计,不是说你勤奋、努力了就一定能成功。哪怕你没做什么多大的事情,你没杀人放火,就一家人很辛苦勤俭地过下来,那也是一种成功。让所有人都成功,这在概率上算起来也不可能。
老罗:中国的家长整天叫嚣让孩子出人头地,可是你想出人头地比别人高一截,但是大家都伸着脖子出来了,你还得往上。
现在中国有钱人没有安全感,大家挣了多少钱都不够。在一个健康有保障的安定社会里,工薪阶层没有恐慌感。我们在国外经常接触这种家庭,他们家祖孙几代只开一个面馆,在东京一个小胡同,常年就这么些客人,他活在那儿,比上班强一些。他那个面呢,一百多年味道不变,他们自己很满意,他们邻居、消费者也很满意,他们觉得很快乐很幸福。在中国,这种就是很奢侈。如果我开面馆,今年赚了3万块钱,明年赚了10万块,后年我就必须赚三四十万块钱,要不然哪天一个拆迁令下来,我的面馆就消失了,那我哪来的安全感呢?所以穷人不安,中产阶层也不安,任何时刻都没有保障。
意见就是行动
《新民周刊》:王小峰说互联网1996年进入中国以来,真正在网络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三个人就包括你。是不是有了牛博网这样一个形式,或者你做其他工作,让您跟趣味相投的人,不是老流于埋怨和指责,能够因为互联网聚集在一起想做点事情?
老罗:这个观点很流行,但是我是非常不同意这个观点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些人认为批评和抱怨不是在做实事,批评是做实事,这个社会的分工是不同的,在任何一个哪怕高度发达、健康完善的社会里,批评家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社会角色。
你看美国已经是很发达的国家,批评家没有消失。对现状的永远不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无论我们现在变得多好,我们仍然应该对它不满,因为它还可以更好。
你做批评就是做实事,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一个文人你不希望他批评,难道希望他从政吗?从政他不是那块料。有的人去做了他那块事儿,有的人因为他擅长并且知道怎么批评,他就做了批评家,这个就是做实事。
我特别讨厌汶川赈灾的时候,好多媒体说以牛博网为平台,罗永浩也在将意见转换为行动。意见就是行动,我怎么就转化成行动了?我们在网站上发帖抱怨、批评,这全是实事不是空谈,批评是实事,我们去赈灾也是实事。
我特别不同意把我去赈灾这件实事拔高,然后把意见、批评看成不是实事,这种意见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原来擅长的就是那个,所以我们做了那些。小个子他可能打乒乓球合适,你为什么要让他打篮球?没有必要。如果你认为打篮球才是搞运动,打乒乓球就不是,这个我是不能同意的。批评家去做批评这个事情,从来都是做实事。
《新民周刊》:但你的这种反驳或者反批评,其实也在遵从这个世俗社会的一个不合理的逻辑,就是说你也在获得一个反批评的资格。
有一个类比,我觉得哪怕中国人全民学英语的成本很高昂但效果很差,从单个人来讲,我觉得你先把英语学得还算过得去,然后你再来批评这个事情,才会更有说服力。
老罗: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不会要求别人这样。我明白你的意思,有些人吃完了菜说不好吃,那另一个就说你他妈会不会炒菜。这个逻辑是不对的,我不会对别人那么要求,但是我认为如果你会炒菜又告诉说这个菜好吃不好吃,这不是必需的,但是更有说服力的。
体制内的英语教育显然是失败的,这个就能解释为什么民办的英语培训机构生意这么好。我觉得是这样,教育应该培养他们学英语的兴趣,然后學不学不应该强制。但咱们国家正好相反,他首先不培养也有没能力培养你的兴趣,先是来了一群讲课都特别八股的傻×老师给你上课,所以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来培养你学英语的兴趣,然后他会强制你必须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不光是英语,所有的科目都学不好,在中国不觉得有什么好,不就记住了一些公式吗?一个学化学的跑到美国去一看,自己会的公式比美国的学生会的多上百倍。还觉得自己基础教育学得很扎实,你去找一流的科学家看,他们也都背不下来那些公式,那个公式本来就不是让你背的,而是让你学完了用的时候拿出来查的,你背它干什么?这个就是很愚蠢的事情。咱们不光英语教学,所有的教学都是这样,部分老师做不到培养学生的兴趣,他能做的就是学校要求你考多少分你才能拿到毕业证。(钟宇飞对本文亦有贡献,谨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