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荒政的山西样本
黄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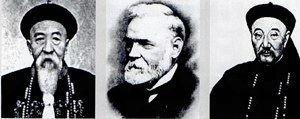
在洋务运动中期发生的山西大旱,给了后人一个观察晚清政府效能的窗口。在此之后,一个看上去早已摇摇欲坠的帝国居然还能支撑30余年,从山西大灾中也能窥出端倪。
民国以降,对晚清祸国殃民的罪恶列数汗牛充栋,然而,晚清历史也并非胜败双方描绘的那样非黑即白,在这当中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清代的荒政治理仍达到了专制社会下的一个高度。尤其在洋务运动(1861~1894)中期,“同治中兴”的成果犹在,晚清政府的中央及地方官员仍在为挽救腐败清王朝而付出种种努力,中外人士的交往也无多大阻滞,这时候发生的山西大旱就给了后人一个观察晚清政府效能的窗口。
被疑忌的外来慈善家
古有“荒政”,设立粥厂、平粜、放赈、组织慈善捐助、免饷减税,这都是一个正常的政府面对灾荒的既定动作。而学界公认,清代是“荒政”发展最为完备的时期。有清一代,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1876一1878)最为严重,涉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而其中尤以山西的灾情最为惨痛,并且在赈灾过程中涌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元素,即外来慈善家以一种大大出乎传统中国人意料的方式介入了救济事务。
面对山西大灾,清廷的反应速度不能算慢。1877年5月,刚刚到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即向朝廷提出把当年上半年的应解京饷50万两,拨出20万两作为赈灾,很快便得到允准。除了官方设粥、放赈救急外,山西民间救济活动也踊跃开展了起来。例如,榆次县巨富20余家,此次捐银14万两,但曾国荃仍嫌少,要求属下进一步加强民间募捐的力度。
尽管如此,赈灾仍然存在很多不如人意之处。有的是细节不善,如粥厂往往设于城中,“近者得食,远者不获一餐……使民奔走不遑”。当时媒体报道,“赴城领赈所须付出体力透支的代价,令乡人感到不值得作这尝试”。有的是历史遗留难题,如交通运输条件太差,使赈灾工作往往事倍而功半,曾氏感叹:“所有采买之粮,价值居其一,运费居其九,以故竭天下财力,皆销磨于脚运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参与山西赈灾并取得了成效,就显得难能可贵。李提摩太1870年来中国,在中国度过大半生,因其广交政坛和知识界精英,对晚清政局有相当的影响力。李提摩太于1878年初进入山西。他的回忆录《亲历晚清4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保存了一些当年的日记片断,读来触目惊心。
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赈灾,在两种文化相互打量、提防的背景下,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疑忌。当李提摩太对官方提出赴山西的要求时,军机大臣瞿鸿禨上了一道《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为此清廷特颁发谕旨给曾国荃,要曾对洋教士“婉为开导,设法劝阻”。朝廷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影响和制约曾国荃。据李提摩太回忆录所记,李提摩太初至太原拜访曾国荃即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曾的秘书告诉他,巡抚因为李提摩太的出现非常生气。李提摩太写道:“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2000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灾民,并且办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依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
然而曾国荃毕竟不是死读圣贤书的腐儒,当其意识到李提摩太一行并无恶意时,很快改变了态度。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说:“他立即派地方官员及其助理前来与我商谈。他们有那些村庄所有家庭的名册,并打算依此给每个家庭发放救济金。他们提议为我安排几个村庄去救济,并派官员和绅士帮助我,以便不受干扰地完成工作……在中国官员的完美配合下,救济工作开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结束。”1878年10月,当李提摩太离开山西去山东结婚时,曾国荃给其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词的信,在信中,“他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代表我曾帮助他们摆脱饥饿的山西千千万万民众,对我表示了感谢”。
而李提摩太被蒙在鼓里的,是曾国荃奉命调查他而上的一道奏疏,曾国荃说:“此次英国教士李提摩太等,携银来晋放赈,迭准直隶来咨,当即分委妥员会同办理,先在阳曲徐沟,诸称平顺。嗣该教士闻省南灾务尤重,愿赴平阳散放,亦经分饬照料办理,均极妥协,并无河南所奏情事。”从“并无河南所奏情事”一语中可以看出,当时同为灾区的河南的官员肯定对洋教士有不利报告,清廷才下令山西方面调查,而曾国荃对洋教士则给予了与同僚完全相反的评价。
曾国荃与洋教士的交往,对山西赈灾意义重大。李提摩太自带银两不多,但他通过日记等形式向海外通报灾情,海外募捐效果空前。据统计,经李提摩太等西方施赈者从饥馑线上挽救过来的家庭数目达到lO万户,得到救济的人员高达25万人。外洋赈款20余万两中,李提摩太及助手负责发放了12万两,领赈灾民超过15万人。李提摩太等人的赈灾取得效果,而这与曾国荃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大灾中的官商群像
李提摩太在回憶录中称赞由做过将军的曾国荃来当灾区的巡抚是一种“幸运”,“当发现一位政府官员侵吞救济金,中饱私囊时,他下令立即处决。这种果敢的行动震慑了其他官员,缘此他使政府官员免于腐败,也使乡村不至于失序”。
1878年3月,曾国荃向清廷上了《特参州县疏》,所参的地方官吏,包括吉州知州段鼎耀、代理荣河县知县王性存、试用县丞郭学海等等截留赈灾款的官员。最有意味的是,稷山县与和顺县的两个知县仅因在灾中修理知县衙门,也受到了曾国荃的严厉处分。除了“纪律处分”,有些贪黩官吏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山西阳曲县的仓书李林儒—一个管理放赈的小吏在承办粥厂放赈中,侵盗米粮50石,被曾国荃下令就地正法。
这些在大灾之中“玩视民瘼”、“忍心害理”甚至舞弊自肥的官吏,的确彰显了晚清吏治的一些漏洞,但考虑到灾区幅员的辽阔,赈灾中调动财物的数额之巨,这次赈灾中腐败官吏的比重和危害并不特别突出。而且,大灾面前,山西“州县等官多有饔飧莫继者,且有得力之员因办赈焦劳过甚,遂至一病不起无以为验者”,如李鸿章办洋务企业的干将朱其昂、原甘肃道员张树炎、知州陈世纶、知县刘祥翰等皆在救灾中病故。据曾国荃统计,灾情发生以来,“计候补及在任正佐各员物故者,已近80员”。官吏亡故如此之多,除了灾后疫情蔓延的因素外,的确也有部分救灾官员积劳成疾的成分。
而在山西省外,政府倡导的官商捐助活动也取得了很大成效。官方捐助虽近于摊派,但据曾国荃1878年7月之奏疏,外省官员捐款捐物数量不菲,山西省城赈捐局就先后收过10多万两银子、1500石粮食。而民间渠道的捐助活动多由有名望的绅商主持,“红顶商人”胡雪岩一人给山西、陕西、河南等各灾区捐银合计即高达10万两;另据《申报》,苏浙一批热心绅士亲历灾区,经其筹备的捐银前后超过66万两。如此种种,都证明作为国家符号,当时的清政府还是具备一定的动员能力,尽管多数时候,政府要向捐纳财物者颁授“虚衔”,即荣誉官职。
天降奇灾考验着宛如夕阳西沉的帝国,清廷可以说竭尽了所能。究其实,紧接“同治中兴”时代(1862~1874),元老重臣均在,朝野风气未坏,中央政府的威严尚存,法纪和儒家道德并未遭到普遍蔑视,这些都是山西赈灾取得一定成效的原因。在此之后,一个看上去早已摇摇欲坠的帝国居然还能支撑30余年,从山西大灾中也能窥出端倪。
当然,清政府负责的思维终究无法突破过渡时代的一些显著特征。李提摩太离开山西时,向曾国荃提出了包括向粮价低的地方大规模移民、修筑铁路等建议。根据曾的指示,一群官员讨论后给予了回复:“修筑铁路过于超前,并且必须引进大量外国人,这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从对山西是否最有利的角度看,最好不要修筑铁路。”
——基于文献研究的风险评估原理、方法与研究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