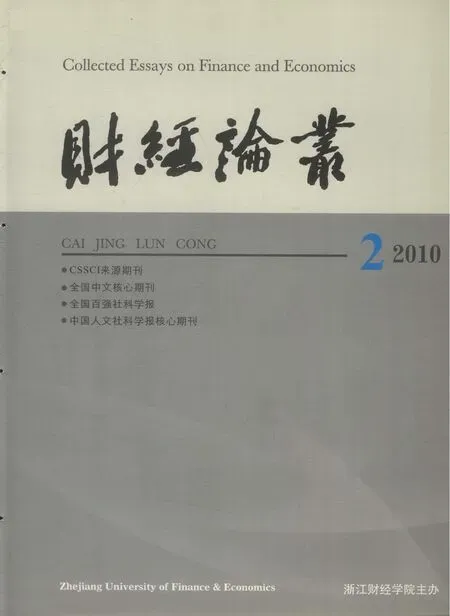“后京都”时代的集体行动问题——基于共用资源理论的视角
盛 军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一、问题的提出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仍未出现全面复苏,但从2008年以来出现的各种极端天气事件在不断地提醒世界,人类还有一个更加严峻的挑战——气候危机。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聚集了全世界192个国家首脑共同讨论 《京都议定书》于2012年终止之后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安排①该议定书是迄今为止明确提出了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减排数额的国际性条约。。世界各国对大会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在2009年7月召开了一次能化解各国原则性分歧的预备会议,争取进入到技术性问题的讨论环节。但从各国的表态和实际情况来看,在哥本哈根达成一项综合性的减排协议的可能性几乎为零②联合国气候变化首席代表德波尔悲观地表示,在发达国家没有给予发展中国家必要的财政扶持之前,达成此类协议是不可能的。。
“后京都”时代如何形成更加完善的机制,以替代现有的 “京都”体制,是世界各国必须解决的问题。但现实情况却难以令人乐观的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人们能找到合适的办法真正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曾被世界各国寄予厚望的 《京都议定书》,迄今为止已告失败了。

表1 《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和达成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减排义务并未得到切实履行。尽管发达国家在使用再生能源、推广碳交易等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但相对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实际需要,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承担减排的义务,但其迅猛增加的排放量也为承担减排义务提供了理由。
从理论研究的视角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一个多成员的n次博弈过程,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促成多成员的集体行动。考虑到成员的异质性 (如发展水平不同)、成员之间的沟通机制 (如国际政治的互信问题)、国际间惩罚机制 (如履行条约的外部约束),这个集体行动问题极端复杂。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迄今还未找到合适的理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些学者的研究工作已成为开拓相关理论的基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艾利诺◦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就是这些学者中的杰出代表。她的主要贡献是研究如何解决共用资源 (Common Pool Resources,CPRs)使用和管理的问题,目的是促成使用者达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以更加有效地使用资源①如何翻译 “Common Pool Resources” 仍存有争议,有的学者(如毛寿龙等)译为 “公共池塘资源”。本文将其译为 “共用资源”,一方面不同于公共资源,另一方面也与公有资源相区别。。这一研究为应对气候危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共用资源理论述评
共用资源是指可以创造一定收益的自然形成的或人为的资源系统,其重要特质就是要支付较高的成本,以排他性地使用并获益[1]。因此,共用资源的使用者不止一人,但每个人的消费将会减少其他人可获取的资源,显著的例子如渔业储量、草原、森林以及饮用水和灌溉水等。在更大的范围内来看,空气和海洋都属于共用资源。
如何协调各个行为人对共用资源的使用情况和条件并达成一定的合作状态,以促进行为人福利水平的提高,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Fehr(1998)指出:“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是以一定群体性为特征的,因而群体合作是普遍现象,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2]。Sen(1996)也认为,人类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合作和妥协的[3]。
(一)共用资源有效管理的可能性——对悲观论的反思
Gordon(1954)和Scott(1955)的研究工作开启了对共用资源理论的探讨[4]。他们假定在行为人具有充分信息、行为人是同质的且不与他人沟通的条件下,从博弈论的分析结果看,各个行为人的最佳策略就是欺骗,而最终导致集体不合作。Olson(1965)在 《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强调,当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存在矛盾时,自利行为将排除合作;除非群体中的个体数足够小,或者存在某种强迫或特殊机制导致个人会为了集体共同利益而行动,理性、自利的个人将不会为达成集体共同利益而行动。这个理论很快变成了熟知的 “集体行动悖论”[5]。随后,Hardin(1971,1982)的n人囚徒困境博弈也显示了理性行为人在一定场景下将不会合作,尽管这些合作行为将会有助于共同福利的提高。实际上,囚徒困境博弈以及其他社会困境都变成了集体行动的标准解[6]。
这类观点的基本模型便是ui=ui[(E-xi)+α◦P(∑xi)]。其中,ui是行为人i的个人效用,E是个体资产禀赋,xi是个体为实现公共品而支付的成本,α是公共品分配给个体行为人的方式,P是生产函数。在线性的公共物品函数中,α被视为1/N且0<1/N<P<1(N为行为人数)。同时,在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中,上述条件是会发生改变的。显然,只要P小于1,理性行为人便会选择“搭便车”策略。
总之,以Olson的观点为代表的传统理论认为,由于 “搭便车”行为的存在,集体行动难以形成。尽管Olson受到其他观点的影响对其理论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但总体而言,Olson的理论给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即达成集体行动是非常困难的。依此结论出发,协调世界各国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将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是不是人类就无法解决威胁我们的巨大危机呢?
Ostrom教授的研究为我们解决共用资源管理问题提供了另一条思路。与传统理论不同,Ostrom认为应当继续保留资源的共用状态,并允许使用者创造管理体制,发挥自我管理作用。在 《集体行动的制度演化》中,她反对先验地认定共用资源缺乏清晰的产权制度时 “公地悲剧”必然会出现,并提出共用资源管理的有效途径。
(二)共用资源管理理论的主要观点
Olson(1965)在理性自利人假设基础上推演出当缺乏 “选择性激励”时,集体行动将无法达成,且认为大集团肯定要比小集团更难形成集体行动。Hardin(1968)认为,要解决 “公地悲剧”,就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无尽索取;另一个是人们如何组织使用者去获取自然资源。Hardin(1968)认为,当行为人陷入囚徒困境时,外部干预就是必要的措施,它可以引导社会形成最优选择。总体而言,在Olson等人的理论中,集体合作问题就是一个囚徒困境,尤其是存在多轮博弈时,其结果便是集体行动不会产生。
Ostrom通过对上千个案例的研究,指出使用者之间的合作是广泛存在的,并提出了影响集体行动达成的因素,包括沟通机制、惩罚背弃者、监督资源使用的能力、冲突解决机制等 (Ostrom,1990)。
1.行为人沟通机制
以往的集体行动理论都忽视了集团成员沟通和协调的能力 (Berkers,1989;McCay and Acheson,1987;Bromley,1992)。从田野调查结果来看,当存在有效沟通情况时,即便没有外界规则,使用者仍会遵守承诺。实验结果也证明,沟通或面对面的交流有巨大的影响力促成合作和集体行动的达成 (Ostrom,1997)。其原因便是沟通会提高他人对已存在的承诺的信任程度,沟通的重要性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Ostrom,1998)。这种行为人之间的信任机制其实就是社会资本影响行为人的途径,它暗示了违反承诺者将会在下一阶段博弈中遭受惩罚。此结论也被行为经济学的成果所证明[7]。
2.自发的冲突解决机制
良好的冲突解决机制是达成共用资源有效管理的条件之一。当存在由资源使用者共同制定规则时,人们可以自发管理好共用资源 (Ostrom,1990)。她从大量田野调查获取的经验显示,政府的政策将会阻碍而不是利于个人支付成本以达成集体行动。这是由于政府颁布的管理制度需要较高的监管成本,并且不能被当地资源使用者接受和理解①例如,在研究印度灌溉系统的案例中,当地的农民就非常反对由地方精英单方面制定的资源使用规则。。同时,这些规则可能会违背长期以来社区形成的公平观念。而公平的管理制度将有助于建立信任关系,促使更多的个体遵守这些规则。由社区成员自发设立冲突解决机制既是公平观念的应用,也是维系信任关系的纽带。
3.资源使用情况
共用资源的特性包括稳定的数量、合适的边界和可预测的资源使用情况,而这些是影响管理体制发挥效力的重要因素 (Ostrom,1999)。与Olson的观点相似,田野调查的结果也确认了 “搭便车”是妨碍公共物品提供的一大难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许多案例都强调了能以低成本计量行为人的资源使用量的重要性。集体成员清晰地掌握了资源使用情况,就可以促进行为人形成下一阶段的偏好函数,并对未来的收益做出修正。在稳定的预期条件下,集体行动更容易达成。同时,根据案例分析的结果,较小规模的使用者往往能比较顺利地获悉资源使用的情况。反之,在更大范围的资源系统中,获取这类信息更为困难,需要支付较高成本。
4.适当的惩罚行为
在传统理论中,改变博弈规则或惩罚不合作者并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Ostrom,1997)。因为“搭便车”行为的存在,Olson等人认为将没有人会支付成本去惩罚那些不合作者,但这一观点却在很多调查中被证伪了。在许多已存在了数代的共用资源管理体系中,使用者会投入一定的资源用来监管和制裁违约者,以便减少出现 “搭便车”的可能性 (Ostrom,1990)。传统理论无法解释此机制存在的原因。同时,Ostrom也认为有效的惩罚机制应该是给予初次违反者以温和的惩罚,其后的惩罚水平逐渐升高。
(三)理论有待完善之处
深入的田野调查表明,现实中的确存在大量成功管理共用资源的案例,这些案例挑战了传统理论,即缺乏外部干预的自发集体行动将不会发生的结论。但从现有的理论成果来看,还存在不足之处。
1.理论系统化不足
Ostrom的共用资源理论是一个高度依赖于实证研究的模型,其主要的研究途径是田野调查或实验室模拟测试,场景的不同会导致结论大相径庭,因此有必要将经验进一步抽象并形成体系。Ruttan(2002)指出,对于解释共享资源的成功治理,目前还没有一个连贯一致的理论,过分抽象理论将无法解释现实的 “田野”调查成果[8]。Ostrom(1997)也认为,案例经验还不能合成在一起成为一个可共同接受、修正后的集体行动理论。
2.大范围的共用资源管理问题
Ostrom的研究成果主要通过案例分析所得,观察对象基本上是小范围的共用资源使用和管理。能否将这些结论过渡到大范围的共用资源管理,则存在变数。Ostrom(2000)认为,共用资源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评估资源使用者的数量、各种特质的变化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迄今尚未能完全理解[9]。例如,在小规模的集体行动中,声誉和惩罚机制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但在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中则很少存在[10];成员人数多寡是如何影响集体行动达成的机制尚未有清晰的结论,合作水平高低与集团大小的逻辑关系还未理顺,仍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Ostrom,1999);成员异质性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变量,它与其他因素的互动关系研究也还处于初级阶段[11]。
总体而言,共用资源管理的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尚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过,Ostrom的成果对改变传统思维和观念极具理论价值。同时,以她的理论为基础,将有助于进一步探究温室气体排放或海洋资源联合管理等大范围共用资源管理的现实问题。
三、共用资源理论于减排集体行动的适用分析
正如Ostrom所言,研究气候变化需要建立跨学科、多层次的研究框架,其中较为基础的就是形成一个涵盖多国的集体行动理论 (Ostrom,2003)。近年来,她本人也关注能否将实验结论推展至更大范围的资源系统[12]。尽管现有的共用资源理论是来自于大量的实验结论和田野调查经验,但我们认为其中仍不乏具有基础性意义的研究结论。因此,在解决减排集体行动问题时,可以借鉴现有的理论成果。基于此,本文结合国际减排行动的发展趋势,提出几项达成减排集体行动的举措。
(一)监督资源总量和使用情况
共用资源的总量以及每位使用者索取的数量是影响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在减排实践中,世界各国都有义务提供真实、准确的数据,以反映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其快速增长的经济总量以及不断攀升的碳排放总量经常成为发达国家拒绝执行 “共同但又区别”原则的借口,因此充分地披露排放数据是应对国际压力、促成国际减排集体行动达成的关键。真实反映碳排放量不仅可以加深各国之间的信任水平,坚定各国减排的决心,也能监督各国政府减排措施的执行情况。从现实情况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都已建立了国内减排行动的具体监测和考核体系,这为达成国际减排集体行动创造了条件。
(二)确定的资源使用数量
确定每个或每类国家资源禀赋的总量,是明确各国权利边界的前提。只有确认了资源使用数量,才能将某些交易工具引入减排实践中,降低减排成本。例如,《京都议定书》中的清洁发展机制 (CDM)就规定了发达国家具体的减排数量,限定了其碳排放的上限水平。人为的 “稀缺性”导致碳产权的出现,由此衍生的碳交易大大降低了减排的边际成本。现阶段的温室效应绝大多数是由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造成的,所以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历史责任,在 “后京都”时代仍然要坚持发达国家的排放上限。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化阶段,对其设立排放上限无疑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因此,如何解决 “限制”与 “反限制”的争执,进而确立合理的资源使用数量,则是考验各国智慧的重大问题。
(三)保持良好的沟通
在小范围的共用资源管理体系中,行为人经常面对面地沟通能加深理解,提高达成集体行动的意愿。同样地,为了形成减排的集体行动,世界各国也应保持良性沟通,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更应该保持有效的沟通。因此,不仅需要全球性的气候多边谈判,也应当设立地区间的沟通机制。通过全球性的气候谈判,明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减排义务,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协议;通过地区间的沟通途径促成小范围的减排合作。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应该进一步沟通和协调立场,并有意识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逐步降低碳排放量。
(四)设立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机制
一定程度的监督和惩罚机制是促成集体行动的条件之一。在国际合作中,世界各国应该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对没能履行承诺的国家施以惩罚。从实践情况看,缺乏有效的惩罚机制也是 《京都议定书》失败的原因之一。在 “后京都”时代,各国一定要汲取此经验并借鉴某些成功的仲裁机制,设立具有强制性的监督体系和惩罚机制,促成世界各国履行国际义务。对于拒绝履行义务的国家,不仅要在道义上予以谴责,也应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施以惩罚。否则,在缺乏有效惩罚和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达成的减排协议也只是流于纸面,其结局就是另一个 “《京都议定书》”。
(五)促成子集团合作
Ostrom(2000)认为,形成子集团可以促进大规模集体行动的达成[13]。因此,在达成全球性减排协议之前,世界各国可以进一步尝试在小范围内形成减排集体行为。从地缘合作的角度出发,邻国之间可以互相协调并达成减排行动。例如,美国东北各州与加拿大部分地区自发设立碳交易市场,协调地区性减排立场。从政治现实需要出发,可鼓励国家集团达成减排协议。例如,欧盟内部协调成员国的排放行为,并力争达成较为统一的减排政策。从经济利益出发,继续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碳减排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利用好清洁发展机制,降低减排边际成本。上述合作措施都将有力地推动国际间减排行为的达成,希望在 “后京都”时代能够得以延续和扩展。
四、结 论
在Olson之前,基于古典主义分析框架可以得出,当存在潜在收益时,集体行动能自动达成的结论称为乐观的集体行动理论。Olson的理论则认为,无论是一轮或是多轮博弈,集体行动最终的结果就是囚徒困境,我们称之为悲观的集体行动理论。Ostrom通过对多个成功的共用资源管理案例的分析也提出了集体行动理论,她的研究大大丰富了人们对集体行动问题的理解。
同时,现实的需要也给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如何解决大规模的共用资源管理 (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促成世界各国达成减排的集体行动)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巨大挑战。在此研究领域中,尽管Ostrom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要真正解决该问题尚有许多工作待完成。
[1]Elinor Ostrom.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2]Fehr E.and S.Gachter.Reciprocity and Economics: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Homoreciprocal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8,Vol.42,pp.845-859.
[3]Sen A..Rational Fools,A Critique of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J].Philosophyand Public Affairs,1977,6(4),pp.77-96.
[4]Katharina Holzinger.The Problems of Collective Action:A New Approach[R].Bonn January,2003.
[5][美]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Elinor Ostrom.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Norm[J].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2000,Vol.14,Number 3-summer,pp.137-158.
[7]Gintis,Bowles.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J].Economic Journal,2002,Vol.(112,483),November,pp.419-436.
[8]Ruttan A..Book Review of‘A Rice Village Saga:Three Decadesof Green Revolution in The Philippines,by Yujiro Hayami and Masao Kikuchi'[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002,Vol.2,pp.460-463.
[9]Elinor Ostrom.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Norm[J].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2000,Vol.14,Number 3-summer,pp.137-158.
[10]Ostrom E..Governing the Common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1]Oriana Bandiera,Iwan Barankay,Imran Rasul.Cooperation in Collective Action[R].April,2005.
[12]Elinor Ostrom,JamesM.Walker.Heterogeneous Preferences and Collective Action[J].Public Choice,2003,Vol.117,pp.295-324.
[13]Elinor Ostrom.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Norm[J].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2000,Vol.14,Number 3-summer,pp.137-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