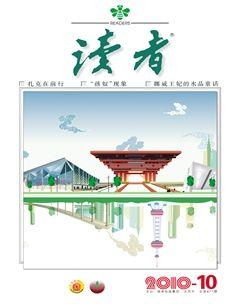知音
余显斌
雪很大,夜很静。一把火,从他房后烧起,一眨眼间,席卷了整个茅屋。他跑出来,只带了一把二胡。
他没有回头,即使回头,也看不见什么,因为他是瞎子。风吹来,浑身很冷。在风里,他一步步走着,最终,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天边。
从此,他漂泊异乡。
陪伴他的,是一把破旧的二胡,小镇、村庄,一路行来。二胡声,在他走过的地方流泻,如一声声低低的诉说,细细的,蛛丝一样。
夜里,他歇宿在破庙里的草堆后,静静地坐着,一双盲眼一动不动,望着虚空。手指颤动,一缕月光水色,从琴弦上淌出,闪着波纹,扩散着,荡漾着。
他在走过的地方要一点剩饭,或者两个冷馒头。
一般,他只吃一半,另一半放在自己歇宿的地方,草堆旁,或者是破庙里。第二天走时,留在那儿。
大家都说,这瞎子,穷讲究,不吃隔夜东西。
他也不说什么,摇头叹息。要饭时,仍多要些,拿回歇宿的地方,剩下一些,放在那儿。有时,要少了,他不吃,把要来的东西都放那儿。
这日,一个雪天,他头晕眼花,倒了下去。醒来时,一个女孩的声音清脆地响起:“醒了,你终于醒了!”
他点头,慢慢坐起来,很是感激。无物感谢,就拿起二胡,闭着眼,手指颤动,一支乐曲婉约流淌。
曲子停止了,一切都静静的。
过了很久,女孩醒悟过来,赞叹:“你的二胡拉得真好啊!我去告诉师傅,你就跟着我们杂技团吧。”说完,女孩一阵风似的跑了。
不一会儿,女孩进来了,坐下。
他一笑,道:“不收瞎子吧?”是啊,一个杂技团要一个拉破二胡的瞎子干啥啊?
“你别急,我再求求师娘。”女孩说。
他笑笑,在女孩离开后悄悄走了,一步一步,走向流浪的远方。二胡声仍如水,随他流淌,时间也在二胡声中流淌。
他在乞讨和流浪中,慢慢老去。
一日,在一个破庙里,他摸到有个人睡在那儿,奄奄一息,显然是饿的。他忙拿出讨来的馒头,喂他吃下。两个冷馒头下肚,那人有了些力气,坐了起来。那夜,没有旁人,只他俩。他坐在神案前,手指轻弹,两滴乐音溅下,闪着晶亮的光。然后,二胡声悠扬,在静静的夜空响起,一会儿如一缕花香,拂过人心,一会儿如一丝轻风,飘荡如纱。
那人静静听着,末了,哑着嗓子一声长叹:“是《月夜鸟鸣》吧,真是人间一绝!”
他笑笑,眨眨已盲的眼睛,和衣躺下,道:“睡吧,明天还要讨饭呢。”
那人也睡下。
以后,他拉二胡挣点小钱,养活两人,因为那人也是瞎子。夜里,坐在破庙里,他拉二胡,那人听。在奔波中,一天一天,他走向生命的尽头。那天,他吐了几口血,靠在一个草堆旁,对那人说:“你不是想得到《松风流水》的樂谱吗?今天,我给你拉。”
“你——怎么知道?”那人惊问。
“你是瞎子;你的右手食指有弦痕,是拉二胡的;在这个世界上,能欣赏我二胡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个女孩,另一个是我的弟子。”他道,脸上有一丝温馨。
“师父!”那人跪下,流着泪喊,不再哑着嗓子。
他点头,微微一笑:“你多次向我讨要《松风流水》的乐谱,又悄悄放火烧了我的茅屋,不就是想逼我带着乐谱逃走,你好在中途盗取吗?唉,世间最好的乐谱不在纸上,在心中。这些年,你跟在后面,我知道。没说破,是想让你跟着吃苦,时间长了,就能领会我当年的话了。”
“你留下的饭菜,也是给我的?”那人哽咽着问。
“你脸皮薄,不讨要,会饿死的。”他仍一脸平静。
说完,二胡声流出,始如蚊痕,继如流水,最后,如一地灿烂的春光。
音乐声越来越低,流入地下,渺无音痕。
二胡落下,他也倒下。
“你知道是我,为什么不恨我啊?”那人抱着他,号啕大哭。
“你是我的弟子,我的……知……音……”他说着,带着一丝笑,咽了气。
那人跪下,恭敬地叩下头去,然后,拿起二胡。月夜里,二胡声如水,波光闪闪,流泻一地。
(流星雨摘自《芒种》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