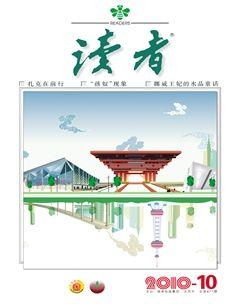因整容而毁容的故乡
王开岭
一
先讲个笑话。一人号啕大哭,问其究竟,答:把钱借给一个朋友,谁知他拿去整容了。
在《城市的世界》中,作者安东尼·奥罗姆说了一件事:帕特丽夏和儿时的邻居惊闻老房子即将被拆除,立即动身,千里迢迢去看一眼曾生活過的地方。他感叹道:“对我们这些局外人而言,那房子不过是一种有形的物体罢了,但对于他们,却是人生的一部分。”
这样的心急,这样的驰往,我深有体会。现代拆迁的效率太可怕了,一夜之间即灰飞烟灭。
大地震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将生活连根拔起,摧毁视觉记忆的全部基础。2006年,在做唐山大地震三十年纪念节目时,我们竟连一幅展现旧城容颜的图片都难觅。几年前,一位美国摄影家把1972年偶经此地时拍摄的照片送来展出,全唐山沸腾了。回顾往昔,许多老人泣不成声。
比地震更可怕的,是一场叫“现代化改造”的人工手术。有建设部官员愤愤地说:“中国,正在变成由一千个雷同城市组成的国家。”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能指认和珍藏一个故乡,且故乡的信息又是各自独立、不可混淆的,那么,面对千篇一律、形同神似的城市,我们还有使用“故乡”一词的勇气和依据吗?我们还有抒情的心灵基础吗?
二
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否则,一个游子何以与眼前的景象相认?何以肯定此即魂牵梦萦、藏有童年的地方?如果眼前的事物与记忆完全不符,往事的青苔被涂抹干净,没有一样东西提醒你自己曾经与之耳鬓厮磨……它还能让你激动吗?还有人生地点的意义吗?那不过是个供地图使用、供言语消费的地址而已。
地址或许和地点重合,比如“前门大街”,但它本身不等同于地点,只象征方位、坐标和地理路线。而地点是个生活空间,是个有根、有物象、有丰富内涵的信息体,它繁殖记忆与情感,承载着人生活动和岁月的内容。比如你说什刹海、南锣鼓巷、鲁迅故居,即活生生的地点,去了便会收获你想要的。再比如传说中的香格里拉,是个被精神命名的地点,而非地址——即使你永远无法抵达,只能“精神消费”,也不影响其诗意地存在和成立。
地址是死的,地点是活的;地址仅仅被用以指示,地点则用来生活。
其实,故乡的全部含义,都将落实在地点和它养育的内容上。简言之,故乡的文化任务,即演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之逻辑,即探究一个人的身世和成长,即追溯他那些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基因之来源。若抛开此任务,故乡将虚脱成一个空词、一记口水。
当一位长辈说自己是北京人时,脑海中浮现的一定是由老胡同、四合院、五月槐花、前门吆喝、六必居酱菜、小肠陈卤煮、王致和臭豆腐……组合成的整套记忆,或者说,是京城喂养出的那套热气腾腾的生活体系和价值观。而今天,当一个青年自称北京人时,他指的多半是户籍,联想的也不外乎房屋、产权、住址等信息。
三
空间的本能是变幻和扩张,它有喜新厌旧的倾向;地点的秉性是沉静和忠诚,无形中它支持保守与稳定。二者的遭遇折射在城市的变迁中,即城区以大为能、建筑以新为尚。而熟悉的地点和传统街区,正承受着垃圾一般的命运。其实,任何更新太快和丧失边界的事物,都是可怕的,都有失去本位的危险,都是对地点的伤害。像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一个人再把它唤做故乡,恐怕已有启齿之羞——
一方面,大城市的欲望无边无际,使得任何人都只能消费其极小的一部分,没人再能从整体上把握和参与它,没人再能如数家珍地描述和盘点它,没人再能成为其名副其实的“老人”和“地主”。
另一方面,由于它极不稳定,容颜时时被更新,结构任意被涂改,无相对牢固和永久的元素供人体味,一切皆是暂时、偶然的,沉淀不下故事——于是你记不住它,产生不了依赖和深厚的情怀。总之,它不再承载光阴的纪念性,不再对你的成长记忆负责,不再有记录你身世的功能。
吹灯拔蜡式的扫荡、删除,无边无际的大城宏图,千篇一律的整容模板……
无数地点在失守,被改弦更张。
无数故乡在沦陷,被连根拔起。
不只是城市,中国的乡村也在沦陷,且以更惊人的速度,因为它更弱,更没有重心和屏障,更缺乏自持力和防护力。我甚至怀疑:中国还有真正的乡村和乡村精神吗?央视“魅力小镇”的评选,不过是一台走秀,是在给“遗墟”颁奖。那些古村名镇只是没来得及脱下旗袍、马褂,里头早已是现代内衣或空空荡荡。在它们身上,我似乎没觉出小镇该有的灵魂、脚步和炊烟——那种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美学和心灵秩序……
天下小镇,都在演出,都在伪装。
真正的乡村精神——那种骨子里的安详和宁静,是装不出来的。
四
自然之子叶赛宁说:“我回到故乡即胜利。”
沈从文说:“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
他们是幸运的,那个时代,故乡是不死的——至少尚无要死的征兆和迹象,游子不必担心故乡会死去。
是的,丧钟响了——是告别的时候了。
每个人都应赶紧回故乡看看,赶在它整容、毁容或下葬之前。
当然还有个选择:永远不回故乡,不去目睹它的死。
我后悔了。我去晚了。我不该去。
由于几乎没在祖籍生活过,多年来,我一直把20世纪70年代随父母流落到的小村子视为故乡。那天整理旧物,竟翻出一本自己的初中作文,开篇就是《回忆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那是一个群山环抱、山清水秀的村庄,有哗哗的小溪,神秘的山洞,漫山遍野的金银花……傍晚时分,往芦苇塘里扔一块石头,扑棱棱,会惊起几百只大雁和野鸭……盛夏降临,那是我最快乐的季节。踩着火辣辣的沙地,顶着荷叶跑向水的乐园。村北有一道宽宽的水坡,像一张床,长满了碧绿的青苔。坡下是一汪深潭,水中趴着圆圆的巨石,滑滑的,像一只只大乌龟露出的背……”
坦率地说,这些描写一点没掺假。多年后,我遇到一位美术系教授,他告诉我,三十年前,他多次带学生去胶东半岛和沂蒙山区写生,还路过这个村子。真的美啊,他一口咬定。其实,按美学标准,那个年代的村子皆可入画,皆配得上陶渊明的那首诗:“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几年前,金银花盛开的初夏,我带夫人回故乡,那亦是我三十年来的首次回访。
一路上,我不停地为她描绘将要看到的一切,讲得她目眩神迷,我也沉浸在“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想象与感动中。可随着刹车声,眼前的景象让我大惊失色——不见了,全不见了!找不到那条河、那苇塘,找不到虾戏鱼嬉的水坡,找不到那一群群龟背……取而代之的是采石场,是冒烟的砖窑,还有路边歪斜的广告牌:欢迎来到大理石之乡。
五
没有故乡,没有身世,人何以确认自己是谁、属于谁?
没有地点,没有路标,人如何再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个时代,不变的东西太少了,慢的东西太少了,我们头也不回地急行,而身后的脚印、村庄、影子,早已消散无踪。
我们唱了一路的歌,却发现无词、无曲。
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了为何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