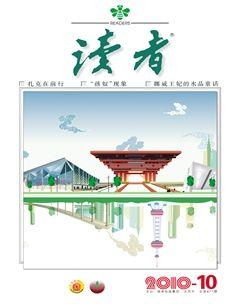我想念你
张曼娟
一直以为,仍有机会在沉沉的夜里,手执听筒聆听你的话语,感觉好近。可是,全部的人都在传说你最后的消息,我渐渐相信(起初一直感觉传闻是不正确的,结果是不实在的),再也不能够了,三毛姐。
于是大街小巷都在谈论,报纸均在头版大篇幅报道,揣测、流言漫天飞舞——反正,你也不能再争辩解说了。现代文学课程上,我向学生们宣布,下学期我们要做有关三毛的专题讨论,那是你走后的第四天。我只是想,当这片热潮过去,提起你的名字便欢呼或落泪或不以为然的反应稍稍平息以后,应该有人在你的浪漫传奇之外,发掘你在文学艺术上的价值。
这一直是你所在意的,不是吗?
你曾和我讨论过,在一篇散文中,我用“原来如此”四个字作结的方式,令你惊奇。方才知道,我是讲究字句的,当然,你也是的。又说起你的一篇散文,实在写得用心而特别,许多人却说:你在写什么呀,三毛!
他们看不懂。你的声音里透着沮丧。
但你是在突破自己,尝试做别人不熟悉的三毛呀。我说。
我因此知道,你其实是急切的,并不真的气定神闲。
你已经把自己缚锁给大众了。
你说:不管我的心情好不好,不管我有没有病痛,只要站在演讲台上,看见挤得水泄不通的读者,在明亮的灯光下,我的生命力就来了,所有的痛苦都忘光啦!
几年前,在一次演讲结束后,人们一拥而上,忽然,有个年轻女孩崩溃地哭起来,吓坏了旁人。只听她断断续续地说:
我……摸……到三毛了!
这类故事盛传着,为你增添了神奇的色彩。
可是,三毛姐,我不喜欢演讲,只要站在台上,我就觉得生命力大量流失,想要奔逃。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写作和生活。
那夜,你说了一句我当时并不明白的话。你说:那么,你是自由的。
在你走后的第二天,我到南部去演讲。飞机上人人都在阅读刊载着你的消息的报纸,只有我闭目养神,不忍再度碰触。天气寒冷阴沉,连南部也见不到阳光。到达演讲现场时,忽然有人问我对三毛此事的看法,并且疾言厉色地说:“她这样做,是不是太对不起读者了?”
刹那间,我有一股暴烈的、欲哭的悲痛情绪。
于是,才知道,你不是自由的。
人们对于公众人物总是严苛得近乎残酷,连他们曾经痴心爱恋过的也不例外。
许多人都曾从你笔下的世界里获取安慰与感动,你给他们温暖,为他们编织梦想。当你自己承受着肉体上或精神上可以言说或不能吐露的尖锐痛楚时,你仍然扮演着万能的智慧者,替旁人解答人生问题。
然而,生命于你,也有难以负荷的重量,或是繁华成灰的虚空。当你急需一些支撑的真实力量时,这些接受过你抚慰的人们,又能给你什么?
你曾在信中对我说:有时候,我们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这是你当有的善待自己的智慧。
你给我的信,都是用九宫格毛笔书法练习纸写的,黑色钢笔水浸渗着,酣畅淋漓。
很久以来,一直想跟你说,妹妹,这条路,我们都在走,旁人如果批评我们,你得分析一下他们的心态,就不会再默默忍耐、委屈,甚而感到孤單。
三毛姐,我几乎为这封信而堕泪,尽管我们很不同,却有过一些相似的经历。自从无意间变成畅销书作者,一些人提起我的名字,突然愤世嫉俗,忍不住寻找诸多罪状,加以口诛笔伐,恨不得连根拔除而后快。开始的时候,我是惊惶的,后来慢慢地就平静了,因为知道这些事其实并不能真正伤害我。而这些都是你经历过的,摸索过的,你完全懂得,看着我走来,担心我禁不住,就忍不住轻轻地说:不要怕,慢慢走……听见这样的声音,我知道自己并非全然孤单。
我们的交往,其实只有一点点,但我知道,你一直努力做着令人感激的事,甚至对许多从未谋面的人也尽心尽力。
演讲结束后,我飞回台北。飞机降落时正是黄昏与黑夜的交界,天空是浓郁的灰蓝色,跑道上一排排晶亮的灯光,一直流泻到视线深处,好美好美。这样的景象,你曾经是看惯的吧?怎么竟舍得放下?我因此又想起你的邀约:江南水乡,是你至深的留恋,你曾约我同游,说找一群朋友,请当地建筑学者为我们介绍、讲解,乘一叶小舟,沿运河行走。那些黑瓦白墙,倒映在盈盈水光间。
也去不成了,或者你不需要伴儿,自己去了。真的,有时候我愿意这样想,就当你像往常一样又去旅行了(你不是说要去西班牙吗),只是这次你去的地方,是我们无法揣想的陌生之所。这一次,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心,三毛姐。
我想念你。
(聂勇摘自春风文艺出版社《人间烟火》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