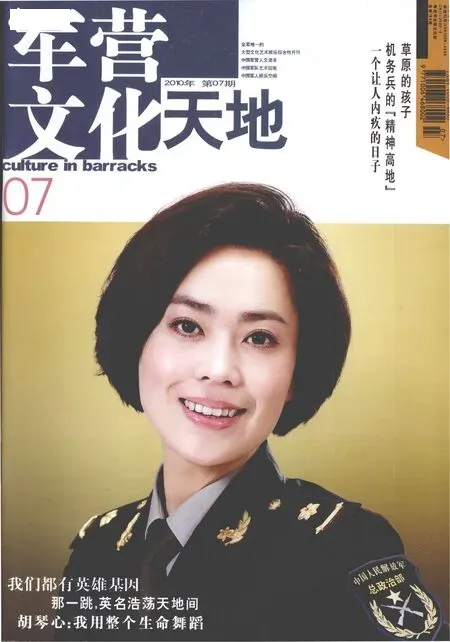瞧,这对欢乐使者
文/图 姜海涛 吴曌 郑学利
“杨光,尖嘴猴腮让观众忍俊不禁;黑旭,肥头大耳令屠宰场难以下刀。”这两句台词在黄金部队中广为流传,虽有些艺术的丑化夸张,但让官兵们牢牢记住了这两位“笑星”。
杨光、黑旭是一对说相声的搭档。杨光,人如其名,灿烂、机智、幽默,满嘴调侃的俏皮话跟连珠炮似的,黑旭则显得憨厚老实、内秀,但从他的憨上你却会发现他富有内涵和底蕴,是文艺创作的一把好手。他们师出同门,入伍前曾一起在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潜修相声,那里的老师都是些有着丰富从艺经验的老师傅,在那里拜师学艺的经历,为他们活跃舞台,服务官兵奠定了深厚的艺术基础。这对“兄弟”一起拜师学艺,一起参军入伍,同吃同住同训练,两人在工作中是战友,生活中是兄弟,舞台上是搭档。
2006年底,因为专业技艺出众,杨光、黑旭被特招入伍。怀着对绿色警营的向往,他俩来到了冰城哈尔滨,如愿以偿,都成了武警黄金总队政治部演出队的文艺兵,依然从事着相声表演事业。
在黄金部队表演相声,观众是常年扎根基层一线、常年在野外施工的武警官兵们。他们的生活单调、枯燥,每年能为他们演上几场节目,送去欢乐,是部队文艺工作者最大的心愿。

他们的第一个作品诞生在新兵连。当排长得知他俩学过相声后,就给他们三天的时间,要他们创作出一个反映新兵连生活的相声。这可难坏了当时的小哥俩,学习表演相声是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说到相声的创作,还从来没有尝试过。但军令如山,两人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活。创作是很难的,创作喜剧就更难了。相声就是一门喜剧艺术,怎么能让观众发笑,还要笑得合理,笑得恰当,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声还是一门语言艺术,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研究相声就等于在研究中国的语言。现在回想起来,压力就是动力,他们绞尽脑汁从身边寻找作品的原型,以贴近新兵的生活,终于如期完成了任务。就这样,他们的第一个作品《懒小子当兵》“问世”了。从登上新兵连的周末舞台,到表演结束,始终掌声如潮。两人想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处女作”竟然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和好评。至今这段相声还在部队流传,令官兵们念念不忘,回味无穷。
好的作品取材于生活,选定题材就是找准相声创作的切入点。为创作更多贴近官兵的作品,杨光、黑旭常去部队一线体验生活,感受普通的黄金兵最质朴的生活。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他们去位于牡丹江的一支队某野外矿区,采风摄取创作素材。从山下到山上没有一条完整的路,在偏远山区里连收音机信号都接收不到。杨光、黑旭和战士们一起,在这样的环境中施工、生活。工作中遇到技术难题就用小本子记下来,生活中看到新鲜有趣的事也细心地记下来,他们说这些都是创作财富,像储蓄一样先存起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在那种几乎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他们深切感受到野外官兵的业余文化活动太少了,一到周末除了足球就是象棋、扑克,从来就没换过样。他们更为基层官兵日复一日、默默奉献的精神所打动。内心深处立志要多为这些生活在矿区的官兵创作一些作品,来反映他们的生活,尽可能地为寂寞的他们多送去欢乐,让欢乐飘向寻金战场的每个角落。
作为文艺兵,工作性质是特殊的。平时扛不了枪、站不上岗,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的机会都比较少。从小就向往警营的黑旭满怀壮志,曾经也为此苦闷了一回,但有一次去一线慰问演出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想法。那次是去野外矿区慰问,矿点很远,看似一条羊肠小道,其实是杂草丛生,根本看不清路,他们就一路上自己“开辟”道路前行,一不小心就会被两边的柳枝松蒿划伤,还经常受山上“巨型”蚊虫的气,光徒步走山路就走了近两个小时。大家千辛万苦来到矿点时体力都透支得差不多了,发现驻守矿点的只有四五个战士,他们像盼亲人一样盼来了演出队,眼睛里闪烁的是激动的泪光。当黑旭看见那些和自己同龄的战士因为矿区条件有限,加上工程作业艰苦,身上那件被汗水和泥水浸透的军装早已磨破,而陪伴他们的仅有一条护矿狗时,心里一酸,眼睛湿润了……那次演出黑旭、杨光格外卖力,表演完原定的节目后,又给战士们加演了好几段。当他们的真情表演让战士们笑得合不拢嘴时,黑旭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他说,工作分工不同,但意义是一样的。只要我的工作能给战友们带去欢乐,让他们得到片刻的放松,就算我们是“武艺”练精了,也算个合格兵。离开矿点那一刻,官兵们一一道别,其中有个三期士官走上来,急切地要和杨光、黑旭握手。当他那粗糙的双手和杨光紧紧相握的瞬间,杨光心里一惊,随即就被这双布满老茧的大手所传递过来的热情和真挚所感动。就是这样一位朴实的老兵,一次难忘的握手,让杨光再次立志为战友们创作更多的相声作品,给他们的工作带去轻松与快乐。
润物无声,他们的作品和表演深深地感染着官兵们。这更鼓舞着杨光、黑旭不断探索创作新的相声作品。在部队文艺作品特有的模式下,两人将地方上具有时代气息的元素融入作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每次去基层演出他们都觉得很痛快。他们总是说,在给自己的兄弟姐妹们表演,怎么能不卖力?“演的每个段子不论表演了多少次,都要当成是第一次在演,全身心地投入。”
说起搭档,他们从同门师兄弟到成为好战友,不论是舞台上还是生活中都相当默契。而这种默契正是用时间积淀出来的,在舞台上经过无数次的锻炼磨砺出来的。他们说一对搭档就像是一对夫妻过日子一样,既要配合好又要各自努力,这样两人的表演才能融为一体。关于默契,杨光、黑旭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从前有对相声搭档,一个叫捧哏,一个叫逗哏,合作多年,可捧哏居然是个聋子,但他只要看逗哏的表情和眼神就能知道他说到哪了,该接什么词了。也许这就是搭档间配合的最高境界。杨光和黑旭他们也在一直这样努力着。平日里对词时他们会把对方的词也背会,这样就不怕舞台上忘词,谁忘词对方都能接得上、圆回来,能让表演更自然。一次演出,黑旭忘词漏说了一段台词,虽说观众们没听出来,但是如果这段词不说就引不出相声的底(结尾)。杨光心里暗暗着急,他给黑旭一个眼神,黑旭马上就意识到了,然后他就在杨光话语的牵引下,两人又配合着把那段词天衣无缝地补了回来,演出获得了成功。在平日里学习业务时,不论是谁看到了一段好的文字,都要和对方分享,两人再细细品味、深入琢磨。生活上他俩也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对方。这对在生活中从未红过脸的好兄弟,却常为创作争执得面红耳赤。要如何设计出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包袱,如何把握表演形式,怎样才能取得最佳的艺术效果,他俩都要细细研讨一番。有时两人意见不统一,无法达成共识,那只有在舞台上见分晓了。每次演出之后他们会对着录像资料再细细地总结分析,他们觉得每次演出都会带着遗憾,但正因为有这种遗憾才使他们在相声文化领域中不断提高作品的时代感、趣味性、欣赏性。
眼下,杨光和黑旭在黄金部队早已小有名气,不少人问杨光要他的剧本,他都会无私地奉献出来。他说,相声不是私有的,一种文化与大家共享才是财富。入伍四年的杨光和黑旭创作出了十几个在本地堪称上等佳作的相声,曾两年参加哈尔滨市双拥晚会的相声作品获得过市文联的最佳创作奖和表演奖,这些成果惠及了广大基层官兵和各界群众,成为更多观众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精神食粮。让相声文化在部队流传,融入官兵的生活更是这对好搭档的最大心愿。“我们热爱相声,看到观众、看到基层官兵因此而欢声笑语时,我们也无比快乐。”这对欢乐使者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