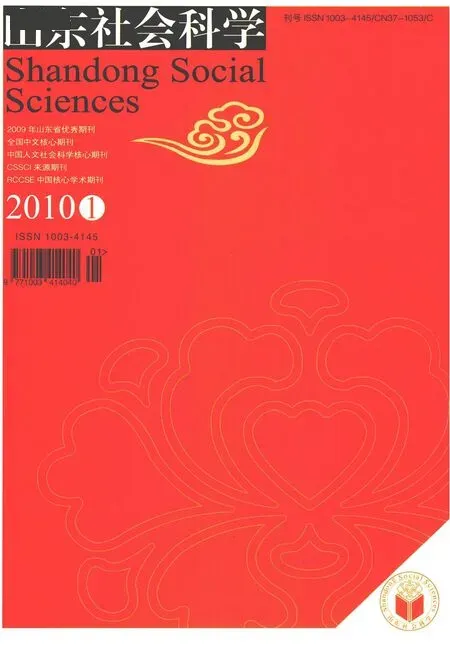论顾炎武的史学思想①
赵 旸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北京 100275)
论顾炎武的史学思想①
赵 旸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北京 100275)
顾炎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批判专制皇朝对儒家思想的摧残,但他的历史观没有摆脱儒家道德伦理决定论的人性历史观和英雄史观。他认为史学的价值和主要作用在于阐明儒家精神指导下的治乱兴衰的道理,其史学思想没有脱离儒家思想体系的范畴。
顾炎武;儒家思想;英雄史观;伦理道德;历史撰述
作为众所周知的实学家,顾炎武被梁启超称为“清学开山之祖”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年版,第 59页。。长久以来,学术界对顾炎武的著作《日知录》是不是一部著作,是不是具有完整严密的体系,存在着争论。如章学诚认为,《日知录》只是展现了顾炎武学术的功力,“不可为著作”②章学诚说:“为学者计,札录之功,必不可少,即顾氏所为《日知》,义本于子夏氏教,然存为功力,而不可以为著作。”(《与林秀才书》,《章氏遗书》卷九,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而周予同则称《日知录》是一部“读书笔记”③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78页。。正因为对《日知录》本身的著述体系存在着争议,因此对顾炎武是不是一位具有严密思想体系的思想家也存在着争论。今天学者对于“顾炎武的史学思想”已有论述,但多是个别观点的描述或者串联,还缺乏对顾炎武思想的整体逻辑体系的把握。本文结合相关的研究成果,拟从顾炎武的历史观、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史料观等方面,对顾炎武的史学思想进行全面地审视和评判。
一、顾炎武的历史观
历史观的主要基本问题包括:历史的本质与构成、历史发展的形式、历史动力和历史创造者的基本问题。顾炎武通过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论述体现了他对于历史观问题的看法。顾炎武认为历史是由人构成的,而不是空洞的形式,但是他的“人”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讲的物质属性的“人”是不同的。顾炎武认为的人是道德属性的“人”,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所在。这是顾炎武对于传统儒学关于道德与人关系的继承与发展。他认为蛮夷与中原人的差异在于是否有文化。他把明朝为清朝所灭亡这一历史事件解释为“仁义充塞,以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的历史阶段,这就是顾炎武所讲的“亡天下”,而所谓“亡天下”“系指社会道德沦亡”。所谓的“天下”不妨说是“道德的宇宙”⑤何贻焜:《顾亭林的社会历史观》,《师大月刊》1935年第 22期。。
顾炎武的观点反映了“封建正统意识和民族主义的观念”⑥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 58页。。但其论述主旨在于论述明朝灭亡这一历史剧变及其产生的原因。顾炎武认为,造成明朝灭亡这一历史剧变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结果,表面上看涉及到了财政、政体、文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的道德。他所说的道德不是今天人们所认为的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而是包含着事功的道德。顾炎武道德的最主要的内涵和突出的特点即在于此,即道德是协调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这里既包含了原则性的内容,也包括了如何具体实践的内容。顾炎武认为传统儒学不过是“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①《日知录 》,卷十八,《内典 》条。儒家哲学是关系人的社会生活实际的行为准则,是有利于人的社会生活的。而这个准则即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与国人交止于信”②《日知录》,卷七,《上天之载》条。。他认为“下学”即“上达”。他指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达道也。”③《日知录 》,卷七,《忠恕 》条。行“忠恕”之事,便是实现上达之法。顾炎武的这种理念是对中国传统儒学伦理思想的一种丰富和具体阐释,对于专制皇朝企图以伦理道德束缚人们的思想是一种突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具有道德属性的人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顾炎武所讲的道德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而是具有一定实践性和客观性的道德,所以他与西方学者休谟所讲的“人性论”存在着一定的差别。顾氏的道德不是教条式的规范,而是一种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设想,其价值是不应被低估的。
顾炎武认为历史创造者是人,尤其是有政治影响力的人。虽然顾炎武说过,“亡天下”是每个人的责任,“匹夫之贱,与有责焉”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这其中包含了承认民众力量的因素,但是顾炎武“亡天下”思想的论述表达了他对君主不履行责任造成社会危机的愤慨,因为只有到了“亡天下”局面出现时,社会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不得已才需要民众的力量。实际上,顾炎武仍然是封建时代唯心英雄史观的拥护者。他提出了著名的“寓封建于郡县”,表明了他的英雄史观。有的学者将这一思想看作是民主启蒙思想,反对君主专制的“地方分权论”⑤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第 163页。。然实质还是协调君臣关系,提高官员工作效率的体制,虽不是维护“君主专制”,但却是维护“专制君主”。⑥周可真:《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73页。“寓封建于郡县”语出顾炎武的《郡县论》。顾炎武的九篇《郡县论》主要论述的中心思想是如何协调好君臣之间的关系,“使一班有官守的人,不得托故卸责,不得推诿他人,非竭尽才力,勉为好官不可。”⑦缪镇藩:《顾炎武的经世思想 》,《经世 》第 1卷 第 9期 1937年 5月。寓封建于郡县”体制说明了顾炎武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寓封建于郡县”是顾炎武重要主张的一部分。《日知录》中的政治主张能否得到实现,顾炎武仍然是寄希望“抚世宰物者”⑧《先生初刻〈日知录〉自序》,《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版。,而非普通民众的民主意识的觉醒。由此可见,顾炎武的历史观仍然是一种英雄史观。
顾炎武认为君主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影响在于君主能否引导民众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够协调好这个关系,那么建立于其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内容都可得到解决。梁启超认为顾炎武一生贯穿着两个主线:“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他认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⑨《顾亭林诗文集》,《与人书九》,中华书局 1983年版。,即道德教化的原则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他认为永乐皇帝颁布《四书五经大全》以及明代的八股取士制度,使得士人“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往之君子欲扫而更之,亦难乎其为力矣”⑩日知录》卷十八,《四书五经大全》条。,其危害有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他认为,学风的好坏不是某个人能够决定的,它决定于具有权威的专制君主。有的学者认为,顾炎武主张“清议”说明顾炎武主张如果民间有好的风气,那么即使是坏的政治,仍然会有好的效果,这是对顾炎武阐述《清议》条本意的误解。《清议》条是对专制君主破坏士人言论自由的一种批判,“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民不犯。”⑪《日知录 》卷十三,《清议 》条。明代专制体制下的“风纪之官但以刑名为事,而于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关,无惑乎江河之日下已”。这说明即使能否实现清议也取决于专制君主。
顾炎武认为历史是不断地变化发展的。英雄人物的活动会在日后的历史中不断产生其作用,这种作用就如同惯性一样,影响不断地扩大。他认为“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⑫《日知录 》卷十八,《书传会选 》条。培养了士人们不学无术,而这就为有人倡导心学创造了条件。顾炎武认为王阳明能够产生影响,即在于学术空疏盛行的时代,他说:“《姑苏志》言姚崇国著书一卷,名曰《道余录》,专诋程、朱。少师亡后,其友张洪谓人曰:‘少师于我厚,今死矣,无以报之,但每见《道余录》辄为焚弃。’少师之才不下于文成,而不能行其说者,少师当道德一、风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说又作之时也。”①《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条。而随着社会不学无术士人数量的逐渐壮大,人们越来越远离经学,心学的盛行是必然的。中国社会自古已经存在了空疏学风的基因,“自老庄之学行于战国之时,而外义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庄子也。于是高明之士厌薄诗书,以为此先王所从治天下之糟粕”②《日知录》卷十八,《内典》条。。而这种空洞学问能否产生作用,正在于这一空疏学风的基因能否适应社会的普遍心理。而明代的专制统治正是创造了这样的条件,科举制度的主旨是让人们不学无术,主考官“首开宗门”③《日知录》卷十八,《举业》条。以心学为题,选拔心学者入朝为官,形成了一种学术导向,最终导致了王阳明的“良知”“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⑤《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条。。
综合来看,顾炎武的历史观是一个一元一因论。他认为历史是变化的,但又不是机械地,一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或者向坏的方向发展。历史的发展与否取决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决定能够协调好人与人之间关系,则取决于封建专制君主的作为。顾炎武的历史观仍然没有脱离古代英雄史观的特点。
二、顾炎武的史学认识论与史学价值观
顾炎武以考据学著称于世。清代乾嘉考据学尊奉顾炎武为清代学术鼻祖。顾炎武注重对历史现实的揭示,但是他揭示历史真相和考订史料的目的并不是为求真而求真,而是要揭示历史成败兴坏之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⑥《先生初刻〈日知录〉自序》,《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版。,为后世“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⑦《又与人书二十五》,《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 1983年版。提供借鉴作用。
顾炎武的历史认识思想的主要特点在于体现了“实用”的效用和价值。他主张学术应该与实际相结合,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知识或思想的效用与价值,把一种知识是否用于人与社会的实际生活作为评判其真与假的标准。顾炎武强调学术的实用,这与实用主义哲学有相似之处。他的“实”是如何才能有利于人的道德建立,以扭转人心风俗。他说:“亲亲,治之始也。”⑧《日知录 》,卷二,《九族 》条。顾炎武认为史学的作用在于“劝善惩恶,亚于六经”⑨《日知录 》,卷十六,《史学 》条。,史学可以使人成为“通达政体之士”。他所谓的史学的主要目的和价值就在于阐释人的治乱兴衰的根由,“揣摩古今风俗,整齐教化根本,原始要终,长辔远驭者”⑩《日知录 》,卷十六,《经体文字 》条。。其史学目的在于扭转不良的风俗。顾炎武通过自战国一直到宋代的历史说明了如果君主尊崇儒学,那么形成的风俗就是好的,王朝就是强盛的。他说:东汉光武帝“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未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⑪《日知录 》,卷十三,《两汉风俗 》条。。而这一思想也确有“充分发挥道德舆论对于官员的监督作用”⑫许苏民:《论顾炎武政治思想的三大理论特色》,《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 8期。的意味。
顾炎武认为史学价值在于阐释古今成败兴坏之理,在于说明儒家的传统道德是如何被丢弃的,儒家的道德伦理的实用价值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指出儒家思想是决定历史盛衰的关键所在。顾炎武的史学思想是在阐述其“经学即理学”的思想。顾炎武认为通过史学可以知道经学是如何废弛的,也只有通过史学才能恢复起经学的正统地位,使人们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才能切实地使经学成为人们普遍尊崇的学说。顾炎武尊崇《史记》的“于序事中寓论断”⑬《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寓序事于论断之中》条。的书法。他通过历史叙事说明了“明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官方提倡的抄袭成书的办法”⑭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50页。与明末空疏学风之间的关系。顾炎武通过历史叙事说明了是否尊崇儒学决定了社会的治乱兴衰,决定了风俗的好与坏。东汉尊崇儒学,所以才使“风俗”无“尚于东京者”⑮《日知录 》,卷十三,《两汉风俗 》条。;魏晋时期崇尚玄学,以至于形成了“仁义充塞,率兽食人”的“亡天下”的局面;明代君主为了维护专制统治,以至于“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①《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条。,导致了明代空疏学风,以至于“亡国”和“亡天下”。顾炎武强调切实贯彻儒学对社会治乱有着重要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顾炎武重视儒家伦理与他重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是不矛盾的。儒家的“上长长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②《大学》,《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年版。、“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弗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等等思想,说明人做事情符合大道,那么对国家的财富的积累和使用,促进经济发展也是有益处的。“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君主好仁,那么在下位者一定好义,“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在原始儒家看来,仁义不仅仅局限于精神层面,它是一种人际关系,是关系到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并非是一种与事功对立的问题。顾炎武通过史学阐述儒学的重要性,也是在说明史学对于人们实际生活的重要意义,说明儒学与现实生活的重要意义。
顾炎武认为史学的本意就在于阐释儒家经典的含义,但由于儒家经典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他说:“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③《先生初刻〈日知录〉自序》,《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 1983年版。他主张“立言不为一时”。他说:“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用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④《日知录》,卷十九,《立言不为一时》条。这反映了顾炎武对于史书价值深远的看法。
综上所述,顾炎武的史学的主要作用和价值在于阐明历史兴坏之理,在于体现经世致用的实用精神,而这种实用精神又是有限定条件的,那就是儒家思想精神指导和影响下的“经世致用”,它的实用在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历史兴衰成败之理又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容。所以历史的价值是深远而且不断地发展变化的。
三、顾炎武的史学研究法和史学撰述方法
顾炎武的史学研究之法基本上符合刘知幾在《史通》中所讲的“才、学、识”之法,这是其进行史学研究和进行史书撰述所应具备的基本方法。
顾炎武认为,史家撰述历史要具备“史德”,才能进行历史撰述。他说:“有王莽之篡弑,则必有扬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禅代,则必有潘勖之《九锡》。是故乱之所由生也,犯上者为之魁,巧言者为之辅。”他认为,学者在做文章之前,“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继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侧媚之习。使一言一动皆出于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后可以修身而治国矣。”⑤《日知录 》,卷十九,《巧言 》条。这是对文人做文章而说的,但是也可以看作他对于作史者应具备的道德的看法。在古代文史不分的时代,顾炎武的这番论述表明了他对于“史德”的看法。
顾炎武认为,史家撰述历史要具备史“学”。史书的作用在于有资于“治道”,能够起到经世致用的作用,且为了力求真实,阐发历史发展脉络的前因后果,因此需要将对社会发展有用的内容都进行系统地阐述。这需要历史学家对各方面知识都有比较深刻地了解。他以司马迁为榜样,说道:“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书兵事地理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⑥《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通鉴兵事》条。顾炎武注重对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等有关人的考察。顾炎武著述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表明顾炎武不仅仅是主张学习司马迁,而且是切实地践行司马迁《史记》的特点。
顾炎武重视对历史事实的考察,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经验主义”⑦赵俪生:《顾炎武新传》,《赵俪生文集》第三册,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他以经学为指导,用史学作为揭示经学内涵的方法与途径,有意识地组织材料和搜集材料。史学是他阐释经学内涵的方法和途径,与经学原则密不可分,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特点所在。顾炎武撰述《日知录》,不仅是要说明历史是什么,而且还要阐述他的观点。他通过从战国时代至宋朝末年社会风俗变化历史的撰述,阐明君主在对风俗产生的决定影响,又通过对明代科举制度的历史,说明专制君主动摇了儒家经义的实质地位,造成了明代空疏学风。
顾炎武的史学研究法模仿了《春秋经》的特点。关于《春秋》笔法,顾炎武做出过明确的论述,他以《春秋》的精髓在于“辞达而已矣”为依据批判《新唐书》机械摹仿《春秋》文词,“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寥而不明”①《日知录》,卷十九,《文章繁简》条。。《新唐书》摹仿《春秋》笔法是摹仿文词,是“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②《日知录》,卷十九,《文人摹仿之病》条。。他主张模仿孔子作《春秋》,寓论断于叙事,对封建君主破坏仁义礼智信的行为进行鞭挞。《日知录》卷十三整卷是在讲君主对风俗的影响,“卷十三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清议、名教、廉耻、流品、重厚、耿介、乡愿之十七条,实前后照应,共明一义,剪裁组织,煞费苦心”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年版,第 69页。指明了明代君主应该对“《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④《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条。,这一士人风气变化负主要责任。有的学者认为“炎武对于晚明学风,首施猛烈之攻击,而归罪于王守仁。”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5页。,这显然是违背了顾炎武的本意。顾炎武主要在做格物致知的功夫,他与理学本无二致。他并非反对追求哲学思想,只是针对不同情况,有所侧重阐发。顾炎武以儒家经典来论述和阐释历史发展的脉络,而他阐释风俗演化的历史,选择论述对象,都是有他阐释儒家思想精神为目的。顾炎武主张辞能达意,“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并认为这才是《春秋经》以及其他儒家经典的精髓所在,模仿《春秋经》是应该的,而模仿的是它精髓。
顾炎武主张史书的语言应该用比较朴实的语言,而不应该华而不实。顾炎武说:有的人心术不正用美妙的言辞来掩饰自己的不足,甚至以此为荣。这是两种不仁之人的其中一种,一为好犯上、好作乱之人,一为巧言令色的人。巧言令色的人没有骨气,患得患失,“无所不至”。他说:“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文辞是否有深度表现了史家的思想性,“其旨远,其辞文”⑥《日知录》,卷十九,《文章繁简》条。。文章的文笔应该出于自然,而顾炎武的《日知录》也基本上体现了这一特点,它的文笔都没有让人感觉刻意雕琢,而是非常平和,在叙述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所要表达的观点展现了出来。
顾炎武的史学研究方法与撰述方法仍未脱离儒家思想蓝本。他词能达意的主张都有他的理论依据和客观标准,即如何才能做到词能达意。他不仅论述了词能达意的问题,而且还论述了如何词能达意的问题。
四、顾炎武史学思想的性质概述
顾炎武的史学思想仍然没有脱离儒家思想体系的范畴。他代表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特点,但这不是主动地而是被动地。如同西欧资产阶级借助文艺复兴运动恢复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艺术来为现实服务一样,顾炎武学说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艺术”,为辛亥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提供了思想解放的武器,而不应将顾炎武看作推动资本主义改革的思想启蒙者。顾炎武的反专制思想来源于他对于专制体制的憎恶,来源于明代文化高压,而这种文化专制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顾炎武对于明代的不满情绪由来已久,而明朝灭亡一方面刺激着顾炎武思考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另一方面也为他批判专制统治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条件,使他可以表达反封建思想。但是他的反封建思想仍然停留在先秦儒家早已强调的君主为政治的主导地位。先秦儒学与专制统治的不同点在于专制统治不受约束,而传统儒学则认为君主还是要受道德约束,《大学》认为君主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⑦《大学》,《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年版。。顾炎武的对专制统治批判的史学思想既不赞同于专制皇帝的封建专制主义,也未提出资本主义民主思想,资本主义民主思想主张的是自下而上对君主的约束,所以顾炎武的批判专制统治的主张,是不能等同于主张资本主义民主启蒙思想的。且其以“寓封建于郡县”为代表的学说其逻辑出发点不在于谈专制还是民主,而是要说明如何才能让官员履行教化民众之责,故顾炎武的“寓封建于郡县”可以称之为“地方分权论”,但此分权论非西方意义上的地方分权论。西方意义上的地方分权论与顾炎武在《郡县论》中主观上论述的重点并不相同,这是顾炎武谈如何工作效率这个主题下阐述的内容所产生的客观效果。
总之,顾炎武思想来源于传统儒学的影响,来源于明朝为清朝所推翻的历史巨变的刺激,来源于明末专制统治对思想控制的松弛。在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还未形成普遍的社会效应,顾炎武的思想只是具备了有利于资本主义改革的特点,但这只是当代人以当代的理念对顾炎武思想的一种升华理解,正如儒学中的优秀思想对今天人们的现实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启示意义并促进了世界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一样,却不能说中国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思潮。
K092
A
]1003—4145[2010]01—0059—05
2009-08-24
赵 旸,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蒋海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