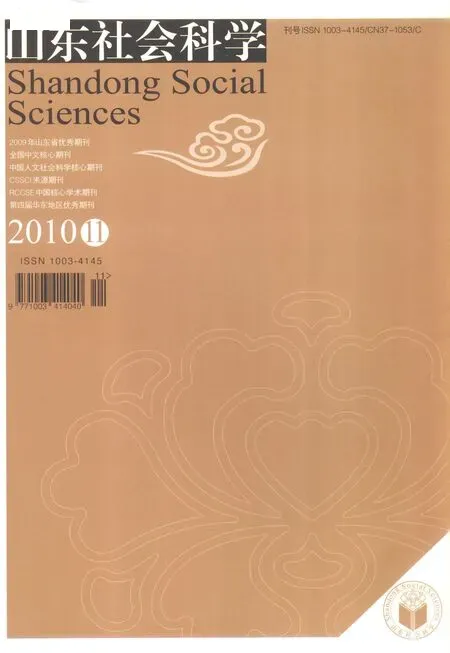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互动的文献综述及逻辑辨析
刘冠军 刘 刚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日照 276826)
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互动的文献综述及逻辑辨析
刘冠军 刘 刚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日照 276826)
纵观虚拟经济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我们发现,虚拟经济是中国具备自主性和创新性的研究课题。以实物经济作为虚拟经济的对立面,以对全部经济活动重新划分为逻辑起点,准确定义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内涵与外延。就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进行基本的逻辑辨析,有助于澄清虚拟经济研究领域的概念模糊和逻辑混乱。虚拟经济研究的出路在于保留其作为中国经济学特色理论的创新性和独立性,回避与“实体经济”对立所形成的概念模糊和逻辑混乱,放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提法,尤其不宜重新定义业已成熟的实体经济概念,而是遵循虚拟经济概念的创新性,作为一个新概念的对立面,重新理性地选择一个作为虚拟经济对立面的新的经济学范畴。
虚拟经济;实物经济;实体经济;金融经济
随着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研究的不断深入,虚拟经济以及与之发生互动关系的新范畴(如实际经济、实体经济、实物经济等)正逐渐或已经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纵观虚拟经济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我们发现,虚拟经济是中国具备自主性和创新性的研究课题。因此,笔者建议以实物经济作为虚拟经济的对立面,以对全部经济活动重新划分为逻辑起点,准确定义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内涵与外延。就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进行基本的逻辑辨析,有助于澄清虚拟经济研究领域的概念模糊和逻辑混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导虚拟经济研究,以期获得虚拟经济研究的自主性和创新性。
一、虚拟经济的源起:一个源自马克思的中国经济学概念
虚拟经济是一个源自马克思的中国经济学概念,是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中国经济学特色的新范畴。刘骏民指出,“虚拟经济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研究,它不是追踪国外研究的结果,而是中国学者从实际出发,以‘问题导向’的方式提出的研究课题。如果经济理论的研究课题有知识产权的话,虚拟经济课题的‘产权’是中国人自己的,具有自主性和创新性”。①在中国,受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影响,虚拟经济范畴明显区别西方经济理论。这一点,成思危结合虚拟经济的英译文做过这样的区分,“虚拟经济……大体上有三种范畴:一是指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Fic2 titious Economy);二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所进行的经济活动(Virtual Economy);三是指以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Visual Economy)”。①成思危:《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管理科学学报》1999年第1期。他认为,“尽管国内有些学者主张采用Virtual Economy作为虚拟经济的英文译名,但笔者还是主张采用Fictitious Economy一词,这样不仅在学术上比较严谨,而且还可以与马克思所提出的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概念一脉相承”。②成思危:《虚拟经济的基本理论及研究方法》,《管理评论》1999年第1期。在国内,虚拟经济研究基本上采用了成思危教授所指的第一种范畴,即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具有相承关系的虚拟经济范畴,而非信息和可视化技术下的虚拟化(Visual)经济。既然是一个由中国学者提出并逐步形成的中国经济学概念,我们有必要简要梳理一下虚拟经济概念的形成过程,探索虚拟经济的理论范畴,并明确与虚拟经济相互动的经济形态应概括为何种范畴。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虚拟经济概念在我国出现。在国内发表的期刊论文中,最早明确使用“虚拟经济”范畴的是程极明,他于1989年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发表的《略论“象征”经济与“实际”经济》一文中指出,“经过战后40年来的发展,世界经济、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即‘象征’经济(又称‘虚拟’经济,指资本流动、汇率和信贷流动)”占了很大份额,“‘实际’经济(又称‘实物’经济,指货物和劳务)与‘象征’经济相比,占了较小的份额”。③程极明:《略论“象征”经济与“实际”经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6期。此后,朱立南认为,“日本的国民资产中包括两个以价格形式存在、但其价格或资产总额并不真实反映所代表资产价值的虚拟成分。其一是能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虚拟资本,即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卷。……其二是土地资产。……虚拟经济虽然产生和依存于实体经济即实际生产活动,但是它的扩张和收缩却并不总是与实体经济的动态保持一致,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后者,故有‘汽泡’经济之称”。可见,在最初的研究中,学者们基本抓住了虚拟经济的主要特征,将虚拟作为一种与金融投机相关联的其价格可能大幅度脱离真实价值的经济形态。同时也意识到,这种经济形态在理论范畴上与“实际经济”相对立。
最初研究虚拟经济的学者的这种判断与后来比较成熟的虚拟经济概念基本一致。但其不足和模糊之处也非常明显,比较典型的有:在注意到“虚拟经济”的虚拟性和不稳定性的同时,又把“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汽泡经济)”、“虚假经济”混为一谈;虽然把与“虚拟经济”相对立的范畴视为“实际经济”,但是没有具体详细界定这种“实际经济”,以致于把“实际经济”、“实物经济”和“实体经济”混为一谈。这也给后来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如在这一时期,李现实就认为,“虚拟经济也称泡沫经济或气泡经济,是指基础产业不发展,实质部分不强盛。而投机活动却异常活跃的虚拟繁荣现象”。④李现实:《宏观调控与虚拟经济》,《上海企业》1993年第9期。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国内虚拟经济的研究,原先比较模糊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已经不能满足进一步的研究。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国内学者们开始规范“虚拟经济”范畴,构建相对严谨、系统的理论体系。1988年刘骏民出版了《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一书,他认为,“广义虚拟经济是除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有关的一切劳务以外的所有的经济活动”,“狭义的虚拟经济仅指所有的金融活动和房地产业”。⑤刘骏民:《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自此,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出发规范和指导虚拟经济范畴,成为这一领域的主导。前面提到成思危教授结合英译文“三种范畴”划分,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虚拟经济研究领域的指导意义。此后,王国刚的《虚拟经济并非虚假经济》和张宗新、吕日的《试析虚拟经济认识上的五个误区》,将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虚假经济的关系基本厘清。当然,即便如此,对虚拟经济的理解也有不同观点。成思危将“我国虚拟经济研究”概括为三种观点:“虚拟经济是一个虚拟的价值系统”、“虚拟经济本身就是金融”以及成思危自己提出的观点“虚拟经济是经济中的软件”,并认为当前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应鼓励不同观点相互补充。
总体而言,以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作为理论来源的研究路线是我国虚拟经济研究的主导方向,这一方向的代表人物刘骏民教授在总结十余年理论研究积淀的基础上,对虚拟经济的界定具有代表性:“虚拟经济并不是虚假经济,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中的实体,既有资源投入又有许多人就业,他们也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并被计入当年的GDP。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区别仅仅在于其运行的方式不同,一个是在生产成本的基础上形成其价格,并靠其生产技术及生产成本来支撑的价格系统;另一个是在人们心理预期的基础上形成其价格,由人们的观念或心理来支撑的价格系统”。⑥刘骏民:《虚拟经济的研究及其理论意义》,《东南学术》2004年第1期。我们认为,这一理论界定体现了我国虚拟经济研究的原创性和自主性。具体缘由应结合虚拟经济与“实际经济”的互动来分析。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互动研究及所面临的“三难境地”
概括而言,虚拟经济概念的混乱和模糊之处,主要是将“虚拟经济”、“虚假经济”与“泡沫经济”混为一谈,并将与之对立、互动的“实际经济”、“实物经济”和“实体经济”混为一谈。不难理解,“虚拟经济”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对经济系统的一个划分,明确了虚拟经济范畴的内涵与范围,作为其对立面的“实际经济”范畴也就相应的得到了确定。可能正是在这一思路的影响下,学者们将概念界定的主要精力集中于“虚拟经济”范畴,对于与之对立的“实际经济”则相对比较随意。如最早使用“虚拟经济”范畴的程极明教授,将与虚拟经济相对应的“实际经济”称之为“实物经济”,而朱立南教授则将与虚拟经济相对应的“实际经济”称之为“实体经济”。
国内最早系统论述“虚拟经济”与其对立面互动关系的文章,应属陈文玲的《论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①陈文玲:《论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世界经济》1998年第3期。只是陈文玲在此和其后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虚拟经济”概念都相对较宽,她认为,“在社会化大流通中,跨越有形国界的无形商品、无形资产、无形货币和无形市场,共同组成了流通的新空间,这空间跳跃着符号,流动着信息,无形货币、虚拟资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把独立运行的那部分以‘无形’为特征的经济形态统称为虚拟经济,而把以实物运动为特征的经济形态称为实物经济”。前面介绍过,随着刘骏民、成思危、王国刚等学者的努力,虚拟经济研究开始回归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相应的,这种以“无形”为特征的“虚拟经济”概念则逐步淡出。可能是为了对应“虚拟经济”范畴这种更加规范、成熟的变化,上述三位学者均使用“实体经济”范畴作为虚拟经济的对立面,讨论两者的互动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成熟,尽管在这一时期仍有学者继续使用“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的提法,②姜琰、陈柳钦:《虚拟经济、实物经济与金融危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3期。但这种提法已经不是学界的主流用法了。相应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提法,已经成为虚拟经济研究领域的主导范畴。尤其重要的是,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明确提出“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③《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5页。更加进一步强化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这对范畴体系。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按照成思危结合英译文的分析方法,秉承虚拟经济范畴作为中国经济学特色理论范畴的自主性和创新性,我们会发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提法,即将“实体经济”范畴作为虚拟经济的对立面,也有其不妥之处。虽然在“实际经济”、“实体经济”和“实物经济”三者混为一谈的时候,三者都曾被译为“Real Economy”,但是,从概念本身的内涵而言,实体经济一直被译为“Real Economy”,而“实物经济”则被译为“Physical Economy”。我们之所以不赞同将“实体经济”作为“虚拟经济”范畴的对立面,正是因为“Real Economy”范畴恐怕难以与“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范畴相对立、相并列。与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不同,“实体经济”——“Real Economy”,并不是一个中国经济学概念,而是一个成熟的西方经济学概念,这一概念及其对立面先于我国“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理论。在这种条件下,选择以“实体经济”(Real Economy)作为我国“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的对立面,必然会造成不必要的概念和逻辑混乱,甚至影响理论的发展方向。实际上,近些年来这种影响一直存在,尤其是明显地影响了我国“虚拟经济”研究的自主性与创新性。
作为“Real Economy”,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实体经济范畴源自“实际变量”(Real Variables),与其对应的是范畴明确的“名义变量”(Nominal Economy)。两者的差别在于是否包括物价变动,是否受货币总量的影响。人们熟知的“实际价格”(Real Price)与“名义价格”(Nominal Price)、“实际GDP”(Real GDP)与“名义GDP”(Nominal GDP)等概念范畴对立,都是以是否包括“货币价格波动”为核心的。在这方面,围绕“货币中性”与否的讨论,成为了货币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核心论题。相应的,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实体经济(Real Economy)”也与“名义经济(Nominal Economy)”、“货币经济(Monetary Economy)”以及“金融经济(Financial Economy)”相对应。“实体经济”与这些经济形态的区分往往是以“计入GDP”作为基本界限。如彼得·德鲁克就把“实体经济(Real Economy)”看作“产品和服务的流通”,④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前沿》,许斌译,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并将他自己提出的与实体经济相对立、并列的“符号经济”(Symbol Economy)看作是“资本的运动,外汇率以及信用流通”; Viviana Zelizer在其《实体经济(The Real Economy)》一文中认为,实体经济(Real Economy)“以企业和市场、法定货币、政府管制、税收和国民核算账户为特征”。①Viviana Zelizer.The Real Economy.Qual Sociol(2008)31:189-193,Published online:5 March 2008.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要杂志《每月评论》编辑部也曾以《实体经济和泡沫经济(The Real Economy&the Bubble Economy)》为题刊文回复Ted Trainer的读者来信:“您所提出的问题,只能通过区分经济学家们所指的与GDP直接相关的‘实体经济(Real Economy)’,以及与资产竞价(the bidding up of asset prices)或纸式债权(paper clai ms)有关的投机或金融经济(speculative or financial economy)来回答”。②Trainer,Ted.,Monthly Review.The Real Economy&the Bubble Economy.Nov2009,Vol.61 Issue 6,p62.
可见,虽然在“虚拟经济”研究领域,作为“虚拟经济”对立面的“实体经济”是一个从属性的范畴,但是作为一个科学的范畴体系“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必须满足一个基本的方法论要求:“实体经济(Real Econo2 my)”必须是一个具备独立概念内涵的理论范畴。作为虚拟经济的对立面,这个理论范畴的独立性、创新性和自主性,直接影响着虚拟经济研究的创新性和自主性。选择“实体经济”(Real Economy)作为“虚拟经济”的对立面,我们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尴尬局面:作为西方经济学的成熟范畴实体经济(Real Economy)有着明确的概念内涵与理论外延,作为实体经济对立面的理论范畴是“货币经济(Monetary Economy)”、“金融经济(Financial Economy)”、“名义经济(Nominal Economy)”和“符号经济(Symbol Economy)”。这些概念范畴是先于我国经济学界的“虚拟经济”范畴成熟的理论范畴。这样一来,就导致我国的虚拟经济研究面临着一种“三难境地”:
——如果为保证“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范畴的创新性和自主性,重新定义在西方经济学界业已成熟的“实体经济(Real Economy)”,难免会形成概念模糊与逻辑混乱。甚至使得Fictitious Economy与Real Economy相对立的范畴体系,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中,显得不伦不类。更进一步,将业已成熟的、甚至已经成为基本共识的基础概念进行与原概念相差较大的“重新定义”,恐有“指鹿为马”之虞,为科学研究所不取。
——如果保留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实体经济(Real Economy)的成熟的范畴界定,并把它作为虚拟经济的对立面,那么,作为实体经济对立面的虚拟经济,其范畴将与早已成熟的“金融经济”、“符号经济”、“货币经济”相重合,从而失去其创新性。实际上,这也正是国内虚拟经济研究的最大误区——作为“金融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同义词,虚拟经济研究最后沦为一种多余的“概念炒作”。
——保留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实体经济(Real Economy)的成熟的范畴界定,同时不再严格要求“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对立面,也难以避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范畴体系出现逻辑矛盾。很明显,作为一个具备自主性和创新性的“虚拟经济”范畴,“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中的实体,既有资源投入又有许多人就业,他们也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并被计入当年的GDP”(刘骏民)。作为经济实体,其劳务计入GDP,这自然构成了实体经济的一部分。按这种处理,虚拟经济即使不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也必然要与实体经济范畴形成概念的重叠。这样一来,“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研究,就不可避免地要包含甚至演变为“实体经济与实体经济一部分之间的互动”。显然,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逻辑悖误。当然,我们不能为了回避这种逻辑悖误而放弃刘骏民教授关于“虚拟经济包含计入实体经济的经济实体、就业和劳务”的基本判断!在我们看来,这一判断,不仅不是虚拟经济概念的错失,反而正是虚拟经济区别于名义经济、货币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创新之处,也是虚拟经济研究的立足点。
三、实物经济:虚拟经济之互动范畴的理性选择
综合上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互动”研究及所面临的“三难境地”,我们认为,虚拟经济研究的出路在于保留其作为中国经济学特色理论的创新性和独立性,回避与“实体经济”对立所形成的概念模糊和逻辑混乱,放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提法,尤其不宜重新定义业已成熟的实体经济概念,而是遵循虚拟经济概念的创新性,作为一个新概念的对立面,重新理性地选择一个作为虚拟经济对立面的新的经济学范畴。这一新的经济学范畴,我们建议选用“实物经济”(Physical Economy)。理由如下:
首先,实物经济(Physical Economy)源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物质生产”概念,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物质生产基础上所形成的一个经济范畴。这如同虚拟经济“与马克思所提出的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概念一脉相承”的关系一样,实体经济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研究的物质生产范畴具有直接相承的关系。这也就是说,理性地选择实物经济作为虚拟经济的互动范畴,将实物经济和虚拟经济视为经济学领域的一对辨证的范畴,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确立的,这样也就避免了不同理论框架中不同范畴的交叉、重叠、模糊和逻辑混乱。
其次,无论是在西方经济学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实物经济概念都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论概念,尤其没有作为基本共识成为经济学的基础概念。例如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有的学者以实物经济代指以物易物的计划经济,①克里茨曼:《无产阶级实物经济的无政府状态》,蔡恺民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第5期。也有学者以此代指纸币形成之前的以商品货币为中介的经济形态。②李翀:《论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到金融经济的转型与异化现象》,《学术研究》2002年第6期。实际上,由于围绕其理论源头“物质生产”和“生产性劳动”的争论从未停止,“实物经济”的范畴也一直处于持续演变的过程之中,如果能够在严谨的理论辨析中准确定义这一概念,也有助于学术的创新和讨论的深入。
再次,“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提法,在虚拟经济范畴提出之时就已经存在,在理论尚未成熟之时又被逐步弃用,重新启用这一提法,既不会显得“怪异”也不至于同成熟的概念体系之间形成概念的混乱和逻辑的不自恰。在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重新定义这一概念,使之不违背“实物经济”原有的概念属性,同时又能够成为虚拟经济的对立面,进而使二者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一对能够互动的辨证范畴。
四、“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互动的概念界定和逻辑辨析
要更为科学地界定虚拟经济以及作为其对立面的实物经济的概念,我们有必要确立一个严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逻辑,将整个经济系统做一个“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划分,通过这种划分,同时给出准确定义虚拟经济和实物经济的内涵与外延,从而彻底解决长期困扰虚拟经济的概念模糊和逻辑混乱。我们认为,这种概念的模糊与混乱状态,主要是原有的概念界定低估虚拟经济概念所涉及的理论深度和难度,并且将不同理论框架中的不同概念“生硬地”拉在一起(虚拟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中的新概念,实体经济是西方经济学中成熟的概念)作为一对辨证范畴来使之互动。实际上,要从人类全部经济系统中分离出虚拟经济,明确它与其对立面之间的概念差别与逻辑关系,需要从定义人类的全部经济行为入手。
(一)以生产和消费的划分为起点确定“实物经济”
我们在此将确定实物经济的逻辑起点确定为: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会构成对生产要素、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其他劳务的消耗,可将所有的经济活动视为消耗行为。所有经济活动即消耗行为,视其消耗目的的不同,可分为消费行为以及其对立面生产行为。前者是指消耗完成之后不再用于售买,不追求价值和价值增值的消耗行为;后者则是指以最终要将这些物品售卖以追求价值和价值增值的消耗行为。人类的全部交易行为,也是消耗要素、产品和劳务的消耗行为,分为售卖行为和购买行为,全部售卖行为均归于生产行为的标签之下;以最终消费为目的的购买行为归为消费行为的标签之下,如果最终要将购买到的物品再售卖出去,以追求价值和价值增值,这种购买行为则应归于生产行为的标签之下。这种看似低级的逻辑划分,对于确定虚拟经济和实物经济的概念与逻辑至关重要。按照上述划分,所有最终被消费掉的要素、产品和劳务构成“实物消费品”,生产这些“实物消费品”所直接消耗的全部要素、中间产品和中间劳务构成“实物生产品”,生产这些“实物生产品”所直接消耗掉的全部要素、中间产品和中间劳务也属于“实物生产品”,依此类推形成循环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构成实物经济系统。所有实物产品的生产、消费和以这些实物产品为标的物的交易活动,作为整体的经济形态即为实物经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要素的交易,尤其是资本的交易,即借贷行为,无论是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货币借贷还是以延期支付形成的商业信贷,均应视为一种“要素交易”,由于交易的标的物与其他中间产品一样是生产中所消耗掉的要素,因此这种交易也属于实物经济范畴。
(二)实物经济的二级市场派生虚拟经济
上述所讲的实物经济系统,不是人类经济系统的全部,它的交易行为派生出虚拟经济系统。被归于上述实物经济的交易行为是以“实物产品”为标的物的交易行为。①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这种交易在现象层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所有权关系的变更与转让,其本质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产权关系和经济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人们的交易过程应视为人与人之间以“实物产品”为标的物,达成交易合同,并执行这些合同的过程。期间如果人们将这些交易合同再实行转让,就会派生出以实物经济的交易市场为“一级市场”的“二级市场”。在这种“二级市场”上充当标的物的“交易合同”,即为虚拟经济系统的“虚拟产品”。人们对虚拟产品的购买不是以最终消耗为目的,而是以追求价值和价值增值为目的的,因此这种“虚拟产品”不同于“实物消费品”,设计、发行以及交易这些“虚拟产品”所消耗的要素、产品和劳务,不同于生产“实物产品”及其中间产品所消耗的产品,不构成实物经济系统的成本和价值总量,而归于虚拟经济系统。相应的,这些虚拟产品的设计、发行和交易行为,作为整体的经济形态构成虚拟经济系统。
(三)从实物经济到虚拟经济的“单维派生性”及实物经济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区别
虚拟经济由实物经济派生,但是虚拟经济所派生的经济实体、就业和劳务均不被视为实体经济,即虚拟经济所派生的所有经济活动均归于虚拟经济范畴,不构成“实物经济”。但是,虚拟经济所派生的经济活动与实物经济一样,会形成对要素、产品和劳物的消耗,甚至在整个经济系统所消耗的要素、产品和劳务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些被虚拟经济派生的经济活动所消耗的要素、产品和劳务,由于不再用于生产最终消费品,因而不再是“实物产品”——套用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思想,资源配置和消耗方面,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这种单维的派生关系与前面提到的虚拟经济范畴和实物经济范畴相一致,从而实现了逻辑关系的内恰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范畴体系与“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范畴体系之间的差别。为此,我们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将“实物经济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金融经济”加以区别开来。
1.关于实物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区别。
西方经济学确定“实体经济”范畴的核心是“是否被购买”,只要最终被购买,其产品和劳务应归于实体经济范畴,计入GDP。如果虚拟经济市场繁荣,更多的人参与虚拟市场的证券、期货交易,就必须更多的向“证券交易所”等实体部分委托业务,购买这些虚拟经济从业人员的劳务,相应的,由于已经被购买,这些劳务也就被归于“实体经济”范畴,计入GDP。但是,在我们的概念体系中,由于这些虚拟经济从业人员的劳务未用于生产最终供消费者消费的“实物消费品”,相应的,这些经济价值属于“实物经济”范畴。
2.关于虚拟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区别。
需要强调的是,在我们的界定中,所有以“实物产品”为标的物的交易行为所派生的,以这些“实物产品”的交易合同为标的物的“二级市场”均属于虚拟经济范畴。这些归属于虚拟经济的“二级市场”,其范畴不仅包括要素中以资本交易为一级市场的股票、债券等金融市场,而且包括了以粮食等物质产品的交易为一级市场期货、期权市场。而且由这些市场所派生的经济实体、就业和劳务均从属于人们在这些二级市场上所进行的交易行为,从而均属于我们所指定的虚拟经济范畴。这明显区别于西方经济学中以“货币量”和“货币价格波动”为核心内容的金融经济。实际上,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都具有虚拟化、证券化的特征,西方金融学研究一直将这些市场归于同一类,只是如果从理论本源上分析,作为“实体经济”对立面的“金融经济”恐怕很难准确囊括这一研究范围。在我们提出的虚拟经济范畴中,这一范围却是非常明确的。因此我们可以预见,随着标准化合同的逐步普及,这种虚拟经济的范围还将更为宽泛。
(责任编辑:栾晓平E-mail:luanxiaoping@163.com)
F062.5
A
1003—4145[2010]11—0064—06
2010-08-02
刘冠军(1963-),男,博士,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 刚(1979-),男,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本文为山东省科学技术发展计划(软科学部分)项目“山东省实物与虚拟经济互动机制和产业升级战略研究”(编号: 2009RKA301)和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研究生问题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研究”(编号:SDYY09063)
的阶段性成果。
①刘骏民:《虚拟经济探索的可喜成果——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一书》,《现代财经》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