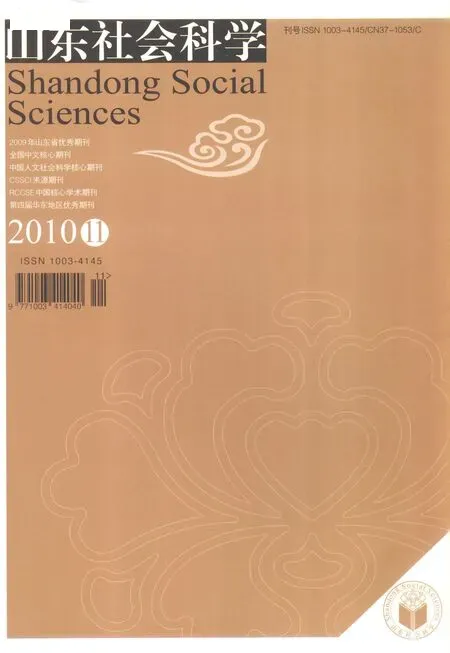论《颜氏家训》的民俗学价值
庄庭兰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
论《颜氏家训》的民俗学价值
庄庭兰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
《颜氏家训》是颜之推以一生的生活实践为指导,为后世子孙留下的一部垂诫之书,平实的语言,谆谆的教导,力显一位老者对后世的殷切希望。但是由于颜之推特殊的生活时代以及特别的生活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南北不同地域的不同民间风俗,在《颜氏家训》中以南北不同风俗为载体教育子孙为人之法、处世之道,成为颇有特色的家训,爬梳其中的南北风俗对于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民俗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颜氏家训》;颜之推;魏晋南北朝;民俗学;传统文化
《颜氏家训》是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为“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精心之作。颜之推,字介,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是颜回第三十五代嫡孙。颜之推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跋涉南北,历尽艰辛,丰富的生活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南北文化和风俗,成为他写《颜氏家训》的基础。纵观整部《颜氏家训》,其内容包罗广泛,学术价值远远超出了普通家训的范围,可作为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对待,故而在历史上不仅家训以此为祖,整个学术界也对其广为推重,其影响之大,可谓开唐代儒学之先河。《颜氏家训》中对于南北朝社会民俗的论述,其细致精辟且学术价值之高,是此一时期流传下来的著作中绝无而仅有的,为研究南北朝的民俗提供了有益的价值。
一、关于宗族家庭
宗族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三纲六纪”的行为规范成为人们交际的准则,但历史发展到南北朝时期,门阀氏族制度的发展为宗族势力的扩大提供肥沃的土壤,“战争频仍,人民流徙,社会秩序混乱,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组织与保障能力减弱,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面对连续不断的兵匪、天灾、疾病、饥饿困扰,只有建立血缘关系上的家族和宗族,稍可发挥组织与保障功能”。①张国刚:《中国家庭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6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宗族势力得到强盛,宗族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在《颜氏家训》中有详备的论述。
1.关于宗族
魏晋南北朝时南方政权基本控制在名门大族和豪强地主手中,为了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侨姓氏族和吴姓氏族纷纷以扩大自己的宗族势力为依靠,这就势必造成宗族的繁殖及其内部的紧密联系。
在宗族成员身处险境,遭遇官司,需要解决困难时,“子孙弟侄,皆诣阙三日,露跣陈谢;子孙有官,自陈解职。子则草屩粗衣,蓬头垢面,周章道路,要候执事,叩头流血,申诉冤枉。若配徒隶,诸子并立草庵于所署门,不敢宁宅,动经旬日,官司驱遣,然后始退”。(《风操》)依靠宗族子孙弟侄解困除忧已成为必须的力量。
宗族的荣誉亦是子孙的荣耀,可以流传百世,这其实凸显了南北朝时期的世袭制度,“祖考之嘉名美誉,亦子孙之冕服墙宇也,自古及今,获其庇荫者亦众矣”。(《名实》)由于所处的时代,战乱频繁,宗族内部的成员不免会加入战争,“父祖伯叔,若在军阵”则“贬损自居,不宜奏乐宴会及婚冠吉庆事也。若居围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饰玩,常为临深履薄之状焉”。(《风操》)一荣俱荣,宗族之间相互帮助,相互依赖,相互发展,成为南北朝宗族发展的主要动力。
宗族势力扩大发展的趋势就是党派之争,这一社会现象在《颜氏家训》中也有明显的记载“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文章》)不可否认,朋党是宗族势力扩大的必然趋势,为唐代严重的地方割据势力埋下伏笔,颜之推的论述为我们讨论朋党的势力范围予以沉重的反思与考量。
同时由于南北文化积淀的不同,北人对于“四海之人,结为兄弟”表现的是“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观貌,不择是非”,南人不同,对于昆季的结拜尤为慎重,认为北人那样会“至有结父为兄,托子为弟者”。(《风操》)这进一步反映了南方人的谨慎与北方人的豪爽。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与南方的生存条件有着很大的差异,北方需要更多的帮助来提高生活本领,所以与志同道合者结为兄弟,成为普遍,而南方相对来说生活较平稳,他们普遍有较高的文化追求和鲜明的礼仪制度,对于宗族势力的发展有着严格的血缘规定,以至会出现较大的南北差异。
2.关于家庭
家庭是宗族的基本组成单位,其实就是它的一个缩影,《颜氏家训》中所记录的有关家庭的民俗事象给我们展示了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以及南北之不同。
在兄弟关系中,存在苛严的礼仪规范,例如“沛国刘琎,尝与兄瓛连栋隔壁,瓛呼之数声不应,良久方答;瓛怪问之,乃曰:‘向来未着衣帽故也’”。(《兄弟》)弟弟在没有穿好衣服、戴好帽子的情况下是不能衣衫不整地见哥哥的,长兄如父,严格地执行着家庭制度。
南北朝世家大族的家庭生活豪奢豪华,一夫一妻多妾成为主流,但妻妾关系往往很难处理,矛盾重重,成为那个时代家庭生活的关注点,颜之推这样形容妻妾:“仆妾之为雀鼠,妻子之为风雨。”(《兄弟》)由于过多的纳妾,势必在家庭中形成矛盾,“雀鼠之不恤,风雨之不防,壁陷楹沦,无可救矣”,(《兄弟》)他告诫子孙要避免这样的家庭关系出现,不然无可挽救,造成家庭的不幸。
与此同时,伴随着家庭观念的强化,父子兄弟分则析居的情况大量出现,争论也不断,“娣姒者,多争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归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伫日月之相望也”。(《兄弟》)可见,当时大家族中由于人口众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也成为南北朝家庭中难以处理的重要问题之一。
家庭观念中最重要的是孝,也就是尊重家长制的权威,随之就会出现婆媳关系的僵化及对立,“为子娶妇,恨其生资不足,倚作舅姑之尊,蛇虺其性,毒口加诬,不识忌讳,骂辱妇之父母,却成教妇不孝己身,不顾他恨”。(《归心》)可以看出《颜氏家训》记载了兄弟关系、妻妾关系、婆媳关系的诸多时代社会现象和问题,虽然时在千年前,但其中的谆谆教导和处事原则对于我们现在的家庭生活仍有非同寻常的借鉴意义。
南北在家庭观念中表现得不同是很明显的,在嫡庶之分上,南方不如北方严格。江东人相对较轻歧视妾媵所生的孩子,即“江左不讳庶孽”,而且,妻子去世之后,大多让妾媵来主持家务,“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而河北人则很鄙视妾媵所生的孩子,“河北鄙于侧出,不预人流”,因此妻子去世之后必定再娶,“至于三四”,有时后母的年龄甚至小于前妻所生的孩子。后妻所生的孩子与前妻所生的孩子从衣服饮食到婚姻仕宦,其待遇竟至于有如士庶贵贱之别,而“俗以为常”。(《后娶》)江东思想较开放而河北观念较保守,这与江南轻名教而河北重传统的风气有关。《魏书·崔道固传》载:“道固贱出,嫡母兄攸之、目连等轻侮之……略无兄弟之礼。”①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28页。唐人褚遂良《请千牛不简嫡庶表》云:“永嘉以来,王途不竞。在于河北,风俗顿乖。以嫡待庶而若奴,妻遇妾而如婢。废情亏礼,转相因习。搆怨于室,取笑于朝。莫能自悛,死而无悔。”②董浩:《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62页。这些记载可与《颜氏家训》所言相参照。
在女性的自由及开放程度上,南方远逊于北方。“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因此,“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齐整;家人妻子,不免饥寒”。而北方的妇女则承担着家庭的社会任务和官场事务,夫妻之间的尊卑表现很淡。“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河北人事,多由内政,”因此,“绮罗金翠,不可废阙”,至于家中的“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夫妇之间的“倡和之礼”已代以“尔汝”贱简的态度了。(《治家》)“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受儒家礼教的束缚较轻,北方社会由于受少数民族风气的影响,女性更加开放,较多的社会交际自由”。③张国刚:《中国家庭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6页。
二、关于禁忌习俗
禁忌作为一种信仰,它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心态,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人们对于自己的命运难以把握,于是他们求助于一些神灵,行为上作出一些禁忌,以免触动心灵的信奉,从而得到慰藉。《颜氏家训》的写作目的是教育子孙,以戒后世,它所阐明的禁忌主要是避讳和称谓,以期以正确的称谓得到祖先的庇佑。
1.关于避讳
当时风俗特别崇尚孝道,“言及先人,理当感慕”,但是由于过于强调家族的兴盛与崇拜,对祖先与过世长辈的避讳出现了过分或矫揉造作的现象,“梁世谢举,甚有声誉,闻讳必哭,为世所讥。又有臧逢世,臧严之子也,笃学修行,不坠门风……书有称‘严寒’者,必对之流涕,不省取记,多废公事”。颜之推认为“此并过事也”。“近在扬都(今南京)有一士人讳‘审’,而与沈氏交结周厚,沈与其书,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因为“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换之”,例如以“国”代“邦”、以“满”代“盈”、以“常”代“恒”、以“开”代“启”等等,而沈氏写信避讳同音字,故非人情。另外,由此亦可见,古人对外署名以署全姓名为常规。至于“或有讳‘云’者,呼‘纷纭’为‘纷烟’;有讳‘桐’者,呼‘梧桐树’为‘白铁树’,便似戏笑耳”。(《风操》)江南人很少有当面谈论自己的家世的,若不得以而必须说,则“必以文翰,罕有面论者”。门阀士族的信仰和对家世的崇拜,使得“今人避讳,更急于古”,“今世讳避,触途急切”以至“而江东士庶,痛则称祢。祢是父之庙号,父在无容称庙,父殁何容辄呼”? (《风操》)过分的避讳与盲目的崇拜既有对家世的延续与肯定也有对现时的趋利与避害,成为人们信仰的重心。
2.关于称谓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严格区分等级的时代,称谓的规范便是这一制度的体现。颜之推告诫子孙“凡与人言,言己世父,以次第称之,不云家者,以尊于父,不敢家也”,“凡与人言,称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长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以下,则加贤字,尊卑之差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则以夫氏称之;在室,则以次第称之”,“言礼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孙不得称家者,轻略之也”。(《风操》)要使用正确的称谓,这才是真正士族子弟的表现,没有规范的礼仪不能显示家族的优越,颜之推语重心长的话语中折射了一位长者殷切的希望。
南北由于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在称谓上也有很大的区别。“兄弟之子已孤,与他人言,对孤者前,呼为兄子弟子,颇为不忍;北土人多呼为侄”,“江南风俗,自兹已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风操》)南方的兄子弟子即是北方的侄子,南方的族人即是北方的从伯从叔。“江南轻重,各有谓号,具诸《书仪》;北人多称名者,乃古之遗风,吾善其称名焉”,江南风俗,如果必须谈及去世的家人,则祖父、父亲称“大门中”,伯父、叔父称“从兄弟门中”,兄弟称亡者子“某门中”,“各以其尊卑轻重为容色之节,皆变于常。若与君言,虽变于色,犹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北土风俗,都不行此”,士人多有不知此者。(《风操》)详细地记载了南北方称谓上的大不同,实则反映了亲疏不同的人际关系与地域性格,为研究地域文化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三、关于社会礼仪
礼乐文化既是人们的行为规范,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是社会对每个人地位的认可,也是文化对人格的塑造。庶族和士族成为南北朝人们社会地位的代名词,它们划分严格,等级森严,门阀观念浓重,需要一套礼乐制度来维护,所以仪礼凸现。“这一时期的礼学特别发达,这与当时门阀士族重视礼法家规的家庭生活实际相呼应,代代相继,累世不竭。”①张国刚:《中国家庭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6页。《颜氏家训》论述了几种南北的不同礼仪,从仪礼中解读文化的差异,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
1.关于诞生礼
“魏晋南北朝时,战争杀戮,生灵涂炭,人口规模减少,农业之国,增加人口,生儿育女成为关注的问题。”②张承宗、魏向东:《中国风俗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刚出生的婴儿,家人对其寄予美好的祝福,期望他能够健康成长,成为家族的荣耀。《颜氏家训》对“抓周”这一现在还流行于世的风俗作了详细的记载:“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
婴儿出生后,家长都抱有很大的希望,在名字上给与寄托,但北方生存条件恶劣,为了使婴儿能够顺利地成长,往往给其取些动物的名字,因为他们认为动物容易养活,于是就出现了“北土多有名儿为驴驹、豚子者”,(《风操》)但是,对于生女儿却有着不同的对待,“太公曰:‘养女太多,一费也。’陈蕃曰:‘盗不过五女之门。’女之为累,亦以深矣”。往往一旦生下女儿即行杀之,“世人多不举女,贼行骨肉”,颜之推对此非常痛心。“岂当如此而望福于天乎”?他以自己的亲戚为例以说明这种习俗的惨无人道:“吾有疏亲,家饶妓媵,诞育将及,便遣阍竖守之……若生女者,辄持将去;母随号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闻也”!(《治家》)这种习俗自古有之,而乱世则尤甚。晋傅玄《苦相篇豫章行》言:“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长大逃深室,藏头羞见人。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与《颜氏家训》所言相参照,更可说明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对生男和生女的心理以及对待有明显的差别。“生女不举”、“盗不过五女之门”等言论深层次地反映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以及人们生活的困苦,只有男丁才可以立门掌户,才可以在纷繁的战乱中使家族拥有一丝的安全感。
2.关于葬礼
佛、道两教在南北朝时被竞相推崇,所宣扬的灵魂不灭、成佛成仙之说,时人普遍认同且成为一种观念所接受,人们坚信人有来世,世有鬼神。葬礼便是此观念最好的诠释,然而对此南北两方也有很大的差异。
“南人冬至岁首,不诣丧家;若不修书,则过节束带以申慰。北人至岁之日,重行吊礼”也就是说南方人在冬至和岁首这两个重要的节日不到办丧事的家里去,如果没有修书以表吊唁,则等到过了冬至或岁首节日之后束带前去申慰,而北方人则恰好相反,在冬至或岁首这两个重要的节日里特重行吊唁之礼。“江南丧哭,时有哀诉之言耳;山东重丧,则唯呼苍天,期功以下,则唯呼痛深,便是号而不哭”,“江南凡遭重丧,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吊则绝之;除丧,虽相遇则避之,怨其不己悯也。有故及道遥者,致书可也;无书亦如之。北俗则不尔。江南凡吊者,主人之外,不识者不执手;识轻服而不识主人,则不于会所而吊,他日修名诣其家”。南方丧葬礼节重于北方,北方风俗对别人的吊慰要求得不像南方那样严格。
四、关于游戏娱乐
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的悠闲和清谈之风迅速发展了游戏娱乐。南北的融合更丰富了娱乐内容,战争促使兵射技能的提高,玄学促成清雅游戏的发展,作为民间的游戏娱乐活动在世家大族之间相互效仿,相互游弋,成为一种生活时尚,琴、棋、书、画成为名士生活的乐趣所在。兵刃相交的社会中,士族以游戏作为生活的寄托,空虚的精神状态却是对现实生活的无奈与默默的反抗,但正是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使得南北朝的游戏娱乐印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表现出生活的原生态。
颜之推作为世家大族的一员,认为名士应该精晓琴棋书画,这一观念早已根深蒂固,也成为南北朝时期盛行的统一认识。他认为“画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礼》曰:‘君子无故不彻琴瑟。’古来名士,多所爱好”。但毕竟生活于乱世,高雅的游戏娱乐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洎于梁初,衣冠子孙,不知琴者,号有所阙;大同以末,斯风顿尽”。(《杂艺》)出现这样的情况,颜之推只能深深地感叹世道的艰辛和酸苦。
晋、宋时,书法普遍为人所重。“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但在“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许多文人雅士竞相改变书法字体,出现了“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的局面,颜之推对此颇为不满,记录下来希望后世不要像他们这样随便更改书法字体,以免与书法艺术的发展背道而驰。同时,他对南北朝的书法情况也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杂艺》)这一民俗资料的保存对研究南北书法的发展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战乱时代,骑射技术必然有长足的发展,作为民间的游戏娱乐项目之一,射击技艺在南北显现出极大的不同,“江南谓世之常射,以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习此……河北文士,率晓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宴集,常縻荣赐”, (《杂艺》)又一次鲜明地显现了南方重文和北方重武的不同趋向。江南鱼米之乡,物产富足,而北方深受少数民族的侵扰,必须很好地掌握骑射技术,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
还有一种民间的娱乐项目即投壶,也就是现在的弹棋,在南北朝也是很受欢迎的游戏方式。“投壶之礼,近世愈精。古者,实以小豆,为其矢之跃也。今则唯欲其骁,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莲花骁”,(《杂艺》)这些民间娱乐方式及其盛行状况在《颜氏家训》中有着详尽的记载。
世家大族的服饰也成为那个时期特有的标志性事物,“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勉学》)“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涉务》)富丽的衣着显示了颓废的灵魂,奢华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奢靡的一代,埋下了朝代软弱的祸根,丰富的游戏娱乐中则充满着自欺欺人的热情与乐观,这就是南北朝时代上层社会生活的写照。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南北在服饰上也有很大的区别,《晋书·五行志上》曰:“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舆台成俗。”①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26页。自晋至南朝,“峨冠博带,风流相放”,是士大夫穿着追求的形象。“而在北方,流行骑射的裤褶服,并随着南北民俗的交流,上衣下裤的服装款式也传到了南方。”②张承宗、魏向东:《中国风俗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五、关于民间语言
民间语言是民俗事象的一大门类,它是广大民众思想的载体和文化的传承,是集体的智慧和大众的经验总结,传达着民众感情和习俗。民间语言的质朴化和生活化区别于上层社会,通俗易懂,轻松活泼,作为“风俗化石”的语言,其民间的语言系统本身就是民俗,而且记载和传达着其它的民俗事象。这些语言往往通俗易懂,却包含着大量的生活经验,往往琅琅上口,却隐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颜氏家训》中也给我们记录了一些俗语,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中的民俗活动。例如,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教子》)有谚云:“落索阿姑餐。”(《治家》)这表现的是民众的生活经验;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勉学》)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勉学》)则语涉南北朝贵游子弟的不学无术,民众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嘲讽;时云:“丁君十纸,不敌王褒数字。”(《慕贤》)“江南语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逊及思澄、子朗也。”(《文章》)展示了王褒和何子朗的文学造诣在民间的威信;鄴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勉学》)用通俗的表达方式说出了当时的学风;“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杂艺》)表现了尺牍之学在南方的兴盛。
对于南北方言,颜之推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也作了论述,他说:“《三辅决录》云:‘前队大夫范仲公,盐豉蒜果共一筒。’‘果’当作魏颗之‘颗’。北土通呼物一凷,改为一颗,蒜颗是俗间常语耳……江南但呼为‘蒜符’,不知谓为‘颗’,学士相承,读为裹结之‘裹’,言盐与蒜共一苞裹,内筒中耳。《正史削繁》音义又音蒜颗为‘苦戈反,皆失也。’”(《书证》)可见,颜氏入北之后,以其所闻见纠南学之谬甚勇。
与此相关,颜之推对于南方的读音也有记载,并且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南方学者的读音不合于古,且表示不满:“江南学士读《左传》,口相传述,自为凡例,军自败曰败(蒲迈反),打破人军曰败(补败反)。诸记传未见补败反,徐仙民读《左传》,唯一处有此音,又不言自败、败人之别,此为穿凿耳。”(《音辞》)汉魏以前,“败”之读音应无此分别。颜之推博览群书,客观求实,融会古今,贯通南北,故而学识超人,深谙南北音韵的学术功底成就了其在古音韵学史上的地位。
在北齐统治政权当中,鲜卑族统治集团始终占主导地位,因此鲜卑礼俗被普遍崇尚,以至于成为士人晋身的阶梯。同时鲜卑语也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时尚,“近世有两人,……鲜卑语、胡书,煎胡桃油,炼锡为银,如此之类,略得梗概,皆不通熟”。(《省事》)北齐有一士大夫,曾对颜之推说:“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教子》)以会鲜卑语作为骄傲的砝码,以不熟悉鲜卑语为羞耻。颜之推对这种现象大不以为然:“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教子》)反映了坚持中原传统文化以立身与逢迎鲜卑习俗以求仕进的两种不同文化态度。终北齐一朝,统治阶级内部的中原传统的统治文化与鲜卑贵族的风俗习惯之间的冲突始终没有停止。
六、关于学术文化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南北民族融合,佛教、道教争先恐后,崇尚文化的自由开放,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玄学兴盛,“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弘正奉赞大猷,化行都邑,学徒千馀,实为盛美”。(《勉学》)传统儒家严谨的治学之风受到一定的冲击,出现了“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惰裁衣”(《勉学》)的束书不观而希图投机取巧的学术风气,这成为南北朝文化氛围的一大特点。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这在《颜氏家训》的《归心》篇有充分地表现,颜之推对于佛教也是非常尊崇的,他说:佛教之“辩才智慧,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推崇之高,无以复加。但是,颜之推认为佛学与儒学是相通的,而且以儒释佛,即其是以通儒的立场来接受和理解佛教的,“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归心》)这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士人对佛教的态度,也成为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言论,深刻地留下时代的烙印。至于寺院的泛滥,颜之推认为“皆由为政不能节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穑,无业之僧空国赋算,非大觉之本旨也”(《归心》),这样的认识是很清醒的。
此时浮躁的学风就像浮华的乱世一样,文化已经成为士人们争相追求的仕宦手段,“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勉学》)这样的文化发展事态势必形成了浮夸的文化氛围,即如颜之推所说的:“世人多蔽,贵耳贱目,重遥轻近。少长周旋,如有贤哲,每相狎侮,不加礼敬;他乡异县,微藉风声,延颈企踵,甚于饥渴。校其长短,覈其精粗,或彼不能如此矣。”(《慕贤》)“人见邻里亲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学之,不知使学古人,何其蔽也哉?”(《勉学》)“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问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棁竖也;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由是乎!”(《勉学》)多数学人只能纸上谈兵,不能身体力行,成为南北朝时期文化的一大缺憾。以至颜之推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文章》)
传统文化和学术在南北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对于经书的江南本和河北本,颜之推有这样的论述。《诗经·唐风·杕杜》“有杕之杜”,“杕”,“江南本并‘木’傍施‘大’……《韵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为夷狄之‘狄’,读亦如字,此大误也”。(《书证》)颜之推在这里是江南本而非河北本。《诗经·王风·丘中有麻》“将其来施施”,“施施”,“河北《毛诗》皆云‘施施’。江南旧本悉单为‘施’,俗遂是之,恐为少误”。(《书证》)他在这里则是河北本而非江南本,不株守其一。经书之外的书,北方版本亦有较江南版本为善之处,例如,“《汉书》:‘田肎贺上。’江南本皆作‘宵’字……吾至江北,见本为‘肎’。”(《书证》),再如,“《汉书》云:‘中外禔福。’……河北学士皆云如此。而江南书本,多误从手,属文者对耦,并为提挈之意,恐为误也。”(《书证》)又如,“《后汉书》:‘……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学士因循,迷而不寤”。(《书证》)可以看出,北学朴质而传统,南学华丽和时尚,而相较之下,北学往往较为实在和稳妥。颜之推对南北文化的精熟,反映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南北两方在政权上的对立抵挡不住中华文化在软环境中的配合与交融,南北朝就是这样一个多样性与统一性并存的朝代。
以上从六个方面梳理了《颜氏家训》中有关魏晋南北朝礼俗的记录,其中既有风土人情,又有生活习惯,尽显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风与士风。纵观整个魏晋南北朝,它是我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以来的又一大变革时期,思想文化的碰撞必然影响到人民世代传承的生活习惯,南北风俗的某些截然不同是各自文化传统的体现,然而融合则是历史的大趋势。从不同的风俗习惯中我们读到了社会文化的调整与趋向,社会的大发展就是在曲折中前进,在融汇中贯通。《颜氏家训》作为魏晋南北朝学术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在平实的语言中蕴含着厚重的民俗价值,杷疏其中的礼俗事项,使我们看到了一幅特殊历史时期活生生的民俗画卷,使我们具有了进一步深入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民俗的宝贵学术凭藉。
(责任编辑:红星)
K890
A
1003—4145[2010]11—0039—05
2010-10-15
庄庭兰,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