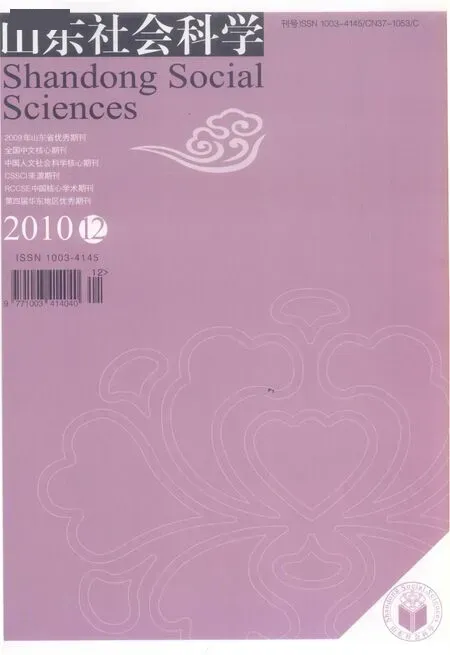中西诗歌中物我关系的对比研究①
——以柳宗元和弗罗斯特为例
刘金侠
(临沂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临沂 276005)
中西诗歌中物我关系的对比研究①
——以柳宗元和弗罗斯特为例
刘金侠
(临沂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临沂 276005)
中西诗歌创作中的物我关系,近年来已成为诗歌创作所普遍涉及的又一深刻理论问题。从物我关系角度分析中西诗歌,可阐明诗歌创作中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特点,并揭示中西诗歌境界之分别和共同规律,即,诗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大凡诗歌皆可依此分类,中西皆然。
物我关系;主观;客观;有我之境;无我之境
近年来,中西诗歌创作中的物我关系或主客观关系,已渐渐成为诗歌创作中所普遍涉及的又一深刻理论问题。对于诗歌应当反映客观,人们毫无疑义。但对诗歌可否“言我”,能否以“我”为主要表达对象,以及诗人的“我”对他或她的创作活动有什么关系,则颇有争论。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写“我”不仅易将文学引向脱离实际、逃避现实、怀疑现实的歧途,且易助长自我中心、孤芳自赏、无病呻吟等消极世界观;而持赞同观点者则认为,诗人最了解、最熟悉的仍然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通过内省自己的心灵才能写出真实、动人的作品。本文试图跳出物我割裂的看法,尝试立足于二者的内在联系,以柳宗元和弗罗斯特的诗歌为例来分析中西诗歌创作中物我之间的关系及地位和作用。
一、“物 ”与“我”的内在联系
作为表达的对象和对创作的影响,物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我”的形成由空白到充满思想感情是由于“物”的影响,“物”或客观世界的存在也经常由于“我”对它的改造、干扰、影响而发展变化。因此,在“物”中有“我”的思想感情,在“我”中有“物”的力量和影响。纯我、纯物是不存在的,主客观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二者相矛盾又相依存。
20世纪之前的文学,由于诗人在观察和表达时有所侧重,产生过重客观描写和重主观陈述两种基本倾向。但在中国,这一现象似乎并不明显。从 20世纪初,西方新诗开始强调物我结合,这体现在意象的创造中。一般说来,现实主义诗人虽不排斥写“我”,但更多写物,写客观,所以“隐我显物”;浪漫主义诗人,更多地写“我”的情怀,因此“显我隐物”。人类的认识规律都是在主观的意识里反映客观,因此在任何一种创作活动中,“我”都起着决定性作用。
二、中国诗歌中的“物”与“我”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到湖南永州做司马,因为当时的遭遇,其诗文浸透着消极悲怆的心情。《江雪》即是此时所作。该诗既是吟咏江乡雪景,又是寄寓自己顽强不屈、孤寂苦闷的思想感情。全诗白话入诗、语言浅近,但意蕴丰厚、耐人玩味。
江 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此诗中既有诗的意境,又有禅的意境;既有诗人的主观精神,又有禅家的“无我之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是写自然景观,写客观:寒冬之际,万物凋零,丛山之中看不见一点绿色,听不见一声鸟鸣,白雪覆盖的山路上,没有一丝人行的足迹。这是一幅全然静止的画面。然而末句笔锋一转,写道:“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动态的景物便呈现于这幅原本静止的画面之中,浑然融为一体。“钓”虽是动作,但在一片山雪之中,独坐孤舟之上,默默钓鱼的蓑笠翁却成为这幅静态画面中的一部分。此诗虽短,但内涵丰厚。正如蘅塘退士所评:“二十字可作二十层,却是一片,故奇。”收到了以奇写正、以浅表深的艺术效果。
诗人把主观心灵与整个宇宙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个主观精神与宇宙精神共存的广阔境界。这正是禅境与艺术境界高度统一的范例。禅境中的“境”是指诗人意识中的景象、环境,佛教中的境就是感觉的所在,故境由心生,禅宗“梵我合一”的世界观与直觉体验的思维方式,在柳宗元的这首《江雪》中得到了完美的艺术体现。正如王国维先生在他的《人间词话》中所言:“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浅谈至此,不得不谈诗之意境之说。“意境”,出自佛经,是指某种悟道之境界。而对于诗之意境,古往今来众说纷纭。一般可以理解为诗人的思想感情和客观事物相契合,所创造出来的神形兼备的艺术境界,是“意”和“境”的和谐统一。对于意境,陆机在《文赋》中从“情思”与“物境”的角度谈及;刘勰的“神与物游”,王昌龄的“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王夫之的“情景”等等,都是从主观和客观的完美契合论及;而王国维则认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王国维先生的观点与古人基本一致,认为意境是情和景的交融渗透、结晶,是心灵的肉身化。
诗之最高层次应是“妙悟”之境,如石涛论画作说:“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浊里放出光明。”此乃人格、个性、气质在诗形象中的含蕴,是一种虚中之实、实中之虚,是一种内在的旋律和节奏,是思想感情的个性化、肉体化,是大千世界独具特色的形形色色,是“我代山川而言,山川与我神遇”。
诗人创作之时的心境亦不可避而不谈。“心境”自然和人格、涵养有关,又被称之为“入定”的忘我心境。这种“忘我”,应是“我”的解放,是一种自由,是心灵的飞跃,是一种无烟火之气的炉火纯青,是“忘我万虑,与碧虚寥廓同其流”,是诗人与万物的合而为一,是动中的极静、静中的极动,使诗之境界空灵动荡而又深沉幽渺,是矛盾之统一与和谐。
诗人总是通过情感和心灵与这个世界沟通,而不是通过理性的概念、逻辑和世界沟通。诗人更多的是依靠原始的自然感知,就像最高的层次有时和最低的层次有某种意义上的相像一样。诗人的审美,有时是依靠直觉的,尽管这种直觉属于较为低级的感觉。
三、西方诗歌中的“物”与“我”
《雪夜林边小驻》是美国诗人弗罗斯特 (Robert Frost)最著名的一首短诗。诗歌以平淡质朴的语言和音律和畅的节奏描绘了新英格兰冬日大雪覆盖、神秘幽暗的树林,展现了大雪中停马伫立的旅行者内心的孤寂和困惑。
雪夜林畔小驻
(余光中译)
想来我认识这座森林,
林主的庄宅就在邻村,
却不会见我在此驻马,
看他林中积雪的美景。
我的小马一定颇惊讶,
四望不见有什么农家,
偏是一年最暗的黄昏,
寒林和冰湖之间停下。
它摇一摇身上的串铃,
问我这地方该不该停。
此外只有轻风拂雪片,
再也听不见其他声音。
森林又暗又深真可羡,
但我还要守一些诺言,
还要赶多少路才安眠,
还要赶多少路才安眠。
诗中,诗人独立伫立于自然和人类世界之间,观赏大雪覆盖的树林:周围没有房子和村落,就连那匹马也不知道主人是否应该在这“一年最暗的黄昏”在这样的地方停息。然而,树林的无穷魅力驱除了他心中的畏惧感,他不顾一切地停下马,欣赏那伸展于轻柔的微风和飘落的大雪中的林子。那迷人的树林最终平息了他的激情,使他在平静的心境中想起自己的诺言,并最终摆脱了树林的诱惑,继续前行,去完成诗中提及的使命。
这位大诗人素以其诗歌的意象丰富和寓意深长而著称,而“树林”意象在其诗歌中频频出现。许多批评家认为,“树林”象征既具挑战性又富有魅力的大自然,它始终迫使诗人离开纷繁的世事,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得以怡然解脱;也有评价认为,“树林”是诗人既不熟悉却又必须面对的潜伏危险的景物,而诗人却依然冒险走进树林,以寻找创作灵感;还有批评家认为,弗罗斯特的创作土壤便是那一片树林,随着时间的流逝,树林的色彩变得越来越浓郁。透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树林”对于弗罗斯特有着难以抗拒的魔力,甚至可以使他丢下日常事务,走进树林,去寻找创作灵感。树林的神秘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诗人希望逃离文明,回归大自然的传统倾向。
四、结语
不难看出,中西方在诗歌创作中都十分重视“我”与“物”即主客观的关系问题,并且都会有意无意地创设某种意境,来表现或升华诗人自己胸中的某种情感体验。诗歌创作中的物我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联系。倘若诗人一味地向自己的内心寻找一切,越深入就会感到越狭窄,如同钻进一个自我迷宫,将自己的潜意识的一切都当做钟乳石岩洞来探讨,到头来却成了自己的俘虏,是不会写出深刻真切且有意义的作品的。但反之,以为要拥抱广大的天地就应当抛弃“我”,也是一个幼稚的想法。创作诗歌与认识世界一样,“我”是媒介,没有“我”也就无法感受外界。“物”(外界)也只有通过“我”才能将诗人对宇宙万物的理解自然地呈现于眼前。“身体化的自我”与“非身体化的自我”之间的交流即“神思”与“物”之间的交流,在这种创设的意境中悄然地进行着:“神”要能深入“物”的核心,概括它的本质,而“物”要能“沿耳目”进入主观。简言之,心灵的宝座要建立在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重叠之处。
I052
A
1003—4145[2010]12—0094—02
2010-10-12
刘金侠,临沂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