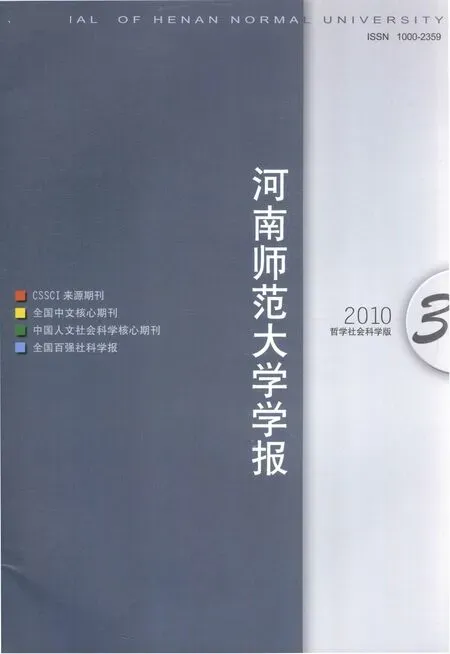政治哲学视域下融入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模式分析
刘笑言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政治哲学视域下融入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模式分析
刘笑言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在政治哲学视域下,融入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存在着以分配为核心的政策模式和以承认为核心的政策模式。在以分配为核心的政策模式中,公共政策的核心在于对一个社会进行权威性的价值分配,但是它没有合理地解决女性作为一个身份群体在文化上的承认问题,甚至忽视了女性主体地位与主体选择的结果。以承认为核心的政策模式是在承认社会中女性群体与男性价值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的差异基础上进行的,但它往往强化了两性的差异,从而将女性限制在现有的性别分工之中。所以,对性别平等真正有利的政策模式将是以分配为核心的政策模式和以承认为核心的政策模式相结合,形成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的政策格局。
性别视角;公共政策;性别平等;分配;承认
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为解决公共问题所制定的方案,是社会群体利益关系的集中表达,也是规范、协调、平衡、调整重大利益矛盾的政治机制。性别视角是从社会性别的角度观察和分析男女两性在社会资源和机会等方面的获得情况,是女性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融入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注重在制度层面保障女性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两性的和谐共同发展。当前,在政治哲学的分析范式下,融入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存在着以分配为核心的政策模式和以承认为核心的政策模式。本文将在分析两种政策模式各自优缺点的基础上寻求一种新的政策模式,试图在公共政策层面对性别平等进行更好的阐释。
一、以分配为核心的政策模式对性别平等的理解
争取平等对待,是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以分配为核心的政策模式中,公共政策被定义为是对社会进行的权威性价值的分配,“其实质在于通过那项政策不让一部分人享有某些东西而允许另一部分人占有它们。换句话说……一项政策包含着一系列分配价值的决定和行动”[1]。在这种政策模式下,对性别平等的理解在于将男性享有的政治经济权利向女性转移。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通过在公共政策中融入性别视角,人们发现了女性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滞后性。女性在政治领域代表权的匮乏,在经济领域“历史性的贫困”,促使以分配为导向的公共政策模式在不触动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在既有的框架内通过在政治上赋权、在经济上缩小差距等资源转移的方式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
(一)家庭政策——使女性走出家庭
家庭,在追求性别平等的运动中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位置上。早期女权运动对性别平等的理解是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其背后的理论依据在于长期存在的将家庭归为私人领域的公私领域划分使女性与公共生活脱离。进入本世纪以来,女性的劳动就业已经非常普遍,传统的男性养家的家庭结构也随之逐渐瓦解。但是,就业中的女性并没有摆脱家庭工作的传统责任,而是在就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下艰难生存。
在以分配为核心的政策模式中,一些具有性别意识的公共政策制定者试图将过去属于公共领域的价值原则引入家庭,并针对家庭模式多元化的社会发展现状制定相应政策措施,避免女性的“历史性贫困”,为女性投入劳动就业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这要求我们对传统上属于家庭的工作重新进行制度规范,如增加托儿所的日托服务,完善老年人生活护理的政策体系和设备场所,对生育抚育工作提供经济补偿,对家务劳动计酬使其社会化等,这对于女性走向劳动就业领域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妇女们的时间是以职业生活与家庭生活两者之间的连续性为其特征的”[2],将这些原本属于家庭的工作推向社会,可以使女性与男性一样更为轻松地投入劳动就业等公共生活中。但是,这种以分配为导向的公共政策模式似乎存在一种价值预设:与劳动就业相比,家庭工作是对女性的一种牵绊,而劳动就业是对女性价值的提升,所以其在价值层面优于家庭工作。这种预设根源于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将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差异”理解为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差距”,对女性赋权的同时构成了对女性无可替代的生物特征——如生育抚育行为——的系统贬低。
这样,以分配为核心的政策模式下,融入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的制定遇到了两难的局面:一方面,以分配为导向的公共政策模式重视资源、权利和机会的公平分配,使女性参与到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劳动就业空间可以拉平男女两性在公共生活中的“差距”,有助于体现性别平等;另一方面,一部分女性往往重视家庭生活而非劳动就业的职业生涯,盲目地将“差异”理解为“差距”可能严重干预了女性作为理性个体的自由和自主。所以,在融入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建构方面,以分配为核心的政策模式不能触动政治经济被性别化的更深层面,甚至可能导致忽视女性主体地位与主体选择的后果。
(二)公共参与中的代表问题
在公共领域的社会参与活动中,以分配为核心的政策模式往往注重活动中女性代表数量多少的问题。在每一次民主会议和政策决定过程中,都会要求保证一定数量的女性代表的参加,一些国家甚至规定了男女比例。一些女性学者认为,保证“从量上增加女决策人的比重”,同时“从质上提升女决策人在决策核心层的地位”[3],有利于促进公共政策的性别意识主流化。
然而,单纯依靠增加女性参政者数量和比重的方式对于保障女性权益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并非如此乐观。“在1997年,英国下议院的女性代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工党在增加女性候选人名额的方面所采取的积极行动。但是,那些进步的女性代表在关于她们被期望可能会发挥重要作用的第一个议题——一种为单亲家庭取消过高保险费的提案——上没有任何一位新当选的女性工党党员准备投票反对该党的路线”[4]76。也许,正如安妮·菲利普斯所说,“它(女性参政代表)的主要成就更多的时候在于打破了政治是男性的世界的假设”[4]68。而事实上,女性代表的增加对于女性地位的改变依然停留在一个非确定性的意义上。其中包含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男性话语体系规定了政治活动的运行规则和政治代表的素质要求,增加女性的参政人数,是将女性代表拉入到一个男性主导的政治世界中并按照其规范行事,男性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具有的与他人对抗式的自我观念以及为捍卫权利而进行的争论成为女性应当具备的“标准的”公民素质规范(代表权问题);另一方面,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阶级阶层划分。
二、以承认为核心的政策模式对性别平等的诠释
女性从属地位的改变,需要政府的推动作用。以分配为导向的公共政策模式在两性平等问题上的局限性促使一部分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将关注点转向以承认为核心的政策模式。所谓“承认”,在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融合了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概念,它的含义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认可、认同或确认”[5]。专注于承认的政治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崛起而普及,它在齐一性思维主导的现代社会中无疑是一种颠覆性的理念。从拉康高呼“女性并不存在”之后,对于女性在文化表征方面作为主体而非他者的承认就成为一种适时的政策导向。以承认为核心的公共政策模式在性别问题上对传统的以分配为导向的公共政策模式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反思和颠覆,防止“文化性别主义(cultural sexism)”对人们思维的固化影响,在争取女性“可见”的同时保证了女性主体的完整性。
(一)家庭政策——使女性留在家庭
以分配为导向的政策模式在家庭政策方面通过使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方式达到使女性得以自由地进入劳动就业的公共生活的目的,但是它同时也否定了对家务劳动及生育抚育工作自身的价值,所以在提升女性地位促进两性平等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当整个社会没有形成对家务劳动和生育抚育行为价值的足够重视时,使家务劳动社会化或是为生育抚育工作提供经济补偿,其结果往往使女性成了弗雷泽意义上的“不应得慷慨的接收者”。所以,融入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在对家庭问题的处理方面不应当仅仅考虑将公共领域的价值原则引入家庭,更需要在制度层面对家庭的公共性价值重新进行规范,对“非工人”的地位给予应有的承认,并将家务劳动和生育抚育工作的价值提升到关乎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层面上来。
有别于以分配为核心的政策模式所倡导的为女性从家庭走入就业劳动提供一系列政策支持的措施,以承认为核心的政策模式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关注于如何提升家务劳动和生育抚育工作的社会价值,进而为留在家庭中的女性提供系统的政策保障。这需要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在制度层面保证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可以获得与就业劳动中的女性同等的经济收入和政治、文化权利,通过提高家务劳动的社会地位的方式使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不必通过投入就业劳动来供养自己的家庭和实现自身的价值,使家务劳动与就业劳动一样被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中;同时,承认生育抚育行为的社会价值,为怀孕中和负有照顾未成年子女责任的女性提供弹性的工作时间计划,“以便于照顾者能够在不丧失安全或资历的情况下退出和投入劳动就业”[6]。另外,政府在文化传播方面要重视媒体的文化导向作用,重新定义社会对于“成功”的概念理解,将生育和抚育行为纳入“成功”的范畴中;加大对基础教育的调控力度,严格控制存在贬低家庭工作及生育抚育行为的教学内容,从起点开始培养儿童对家庭、事业及成功的正确意识。
将家庭纳入公共政策体系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这不单单意味着制定若干保障女性权益的法律条款就可以解决长期存在的蔑视家务劳动及女性生育抚育行为的现象,它对政府提出了诸多诉求,需要政府拥有雄厚的财政储备以补贴家务劳动的价值提升,需要大量的政治文化变革以满足弹性工作时间的需求。从文化价值层面承认家务劳动及生育抚育行为的重要性并辅之以政策支持,是公共政策制定者始终保持性别意识敏感的关键,否则在将家庭纳入公共政策体系的过程中,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地位提升和价值承认将是一个空中楼阁。但是,这种以承认为导向的公共政策模式在对性别平等的诠释中仍然具有一些不可逾越的困境,这表现在承认家务劳动和生育抚育行为的社会价值并从政策层面对之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度保障,一方面可能在无形中使这些工作的女性化特质得以加强,同时导致了女性在就业劳动中被边缘化的局面,另一方面可能会增强女性对政策的依赖并将这种“平等”视为一种特权,名正言顺地成为就业劳动成果的“搭便车者”。
(二)关怀伦理与代表问题
在公共活动领域,以分配为核心的政策模式单纯关注女性代表在量上的增长而无视在其内部差异,对公民素质采用单一的男性化价值规范而无视其他维度的政治要求。以承认为导向的公共政策模式在女性代表问题上不再将女性视为具有同一性的整体,通过对关怀伦理政治意义的再认识为政治参与中的公民素质培养展开了新的维度,通过倡导倾听和包容的重要价值帮助人们发现不同公民群体内部的差异空间。
关怀伦理一直都被认为是属于女性话语体系中的德性伦理而归属于道德领域,所以,关怀伦理从产生开始一直被视为属于道德哲学领域的德性伦理而远离政治理论的探讨。道德哲学领域关注个体的德性发展,在公私领域的划分中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关怀伦理也同样作为私人领域的德性伦理而被认为不具有政治价值。随着女性主义理论对公私领域二元对立模式的超越,以承认为导向的公共政策模式关注从文化层面提升家务劳动及生育、抚育行为的重要价值,所以,传统上认为属于家庭这个私人领域的德性伦理——关怀伦理——其政治价值也应予以承认。崇顿从政治层面上将关怀伦理划分为关注、责任、能力和反映四个要素:关注意味着“关怀伦理学将把对他人的忽视看成一种道德罪恶”[7]170,责任意味着对他人的义务,能力意味着满足他人的关怀需要,反映意味着被关怀者对关怀者的依赖。
以分配为核心的政策模式关注维护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权利,根据人们生而平等的假定分配社会的政治、经济资源。“人们之间平等的假定忽视了人们生存的范围,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在依赖与独立、自主与脆弱之间变化。因此,倘若一种政治秩序只把独立和自主作为人类生活的本质,就会忽视人们生活中的许多体验”[7]172。关怀伦理关注个体依赖于他人的脆弱本性,将人类社会视为相互联系并彼此依赖的网络,提倡对“他者”的关怀和认同。以承认为核心的政策模式重视关怀的政治价值,关怀意味着倾听和包容,这正是参与民主协商的公民所应具备的重要德性。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制度的完善,更需要公民主体具备参与和协商的能力,“关怀描述了多元民主的社会的公民共同生活所必须具有的特性,而且也只有在一个公正、多元和民主的社会中,关怀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把关怀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可以导致对人性理解上的变化”[7]176。所以,在以承认为核心的政策模式下,融入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也应体现在将传统上源于家庭的“关怀”德性纳入对公共参与中公民的素质培养上来。政府应注重多角度全方位地重构社会价值取向,关注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依赖,引导人们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去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与他人具有怎么样的关系”,注重以“政治行为主体的关系为中心进行思考”[8]。依赖、包容和倾听是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民主参与理论对公民素质培养的关键内容,在以承认为导向的公共政策模式制定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将二者结合起来,共同促进性别平等的发展。
三、“分配”与“承认”的联合——迈向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模式
当前两性世界仍然是一个在分配上极不平等的社会,争取分配的正义是性别平等的长期目标。但是,“任何再分配的要求都会有一些承认的后果,无论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9]。以聋哑人为例,在以分配为核心的政策模式中,人们关注机会平等,聋哑人因为其表达方式的“非正常性”而得到了“正常”公民们无限的人道主义同情。由“正常”公民组成的政府通过社会福利的方式补偿他们因为先天原因造成的“非正常”生活,通过将财富和机会从正常人手中转移分配的方式为聋哑人提供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这种再分配的形式也许从经济上改变了聋哑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在文化层面,聋哑人需要的也许并不仅仅是各种形式的社会补偿和人道主义同情,更需要的是对“无声世界平等价值的承认”[10]。同样,在融入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建构过程中,以分配为导向的公共政策模式也可能在分配价值的同时导致女性制度化的文化屈从地位。正如弗雷泽所说,通过“一次又一次地在表层上进行调整。其结果不仅仅是强调性别划分。它将女性标记为有缺陷并且贪得无厌,总是要求越来越多。在那时,女性甚至可以表现为有特权的,特殊对待和不应得慷慨的接受者”[9]。
以承认为核心的政策模式关注突破主流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建构的影响,承认女性相对于男性的“特殊性”,并将其作为普遍的政治共识予以尊重和承认,而不是系统贬抑而提供补偿。在融入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构建中,政府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系统提升家务劳动和生育抚育行为的重要地位进而承认女性作为一个身份群体长久以来为人所忽视的文化价值,同时通过承认关怀伦理的政治意义为女性参与公共政治生活树立了良好的公民素质培养机制。但是,以承认为导向的公共政策模式也面临着一样的质疑:对女性相对于男性在家庭工作以及公共参与中的“特殊性”的不加区别的承认,是否固化了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差异进而巩固了女性在男权话语体系中的被压迫地位?
所以,在融入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建构中,对于性别平等真正有利的政策模式将是以分配为核心的政策模式和以承认为核心的政策模式的结合,形成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的政策格局。在家庭政策的制定中,需要在政策上免除女性进入就业劳动的后顾之忧的同时,为男性进入家庭提供文化和制度保障,提升家庭工作的重要价值的目的不是使女性留在家庭而是使男性走进家庭,“使女性当前的生活模式成为每个人的规范”[6]64,应当成为实现性别平等的终极价值追求。在公共活动参与中,具有性别意识的公共政策制定者不仅仅要关注在数量上保障女性代表人数的增加,也要注意女性群体内部差异所导致的不同利益需求和作为整体的公民素质要求的不同价值规范。面对当前社会始终存在两性差异的现实,决策者要注意区分哪些差异是应当承认的,哪些差异是男性话语体系建构的,这是一个较为艰难的课题,需要在以分配为核心的政策模式和以承认为核心的政策模式的结合中不断摸索。
[1]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23.
[2]安德烈·比尔基埃,等.家庭史:三——现代化的冲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720.
[3]刘莉,李慧英.公共政策决策和性别意识[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3).
[4]Anne Phillips.Democracy,Recognition and Power[G]//Fredrik Engelstad.Power and Democracy:Critical Interventions.Ashgate,2004.
[5]凯文·奥尔森.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M].高静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
[6]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59-64.
[7]肖薇.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8]罗蔚.政治的而非伦理的世界[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6).
[9]Nancy Fraser.From Redistribution to Recognition?Dilemmas of Justice in a Postsocialist Age[J].New Left Review,1995(July/August).
[10]Elizabeth S.Anderson.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J].Ethics,1999(2).
On the Models of Gender Perspective Public Polic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LIU Xiao-yan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olitical philosophy,there are two models of public policy,the one which is centered in the distribution and the other is centered in the recognization.In the model of policy which is centered in the distribution,the center of the public policy is to do a authoritative distribution for the society,but it cannot to resolve the problem that to recognize women as a whole status groups,and it neglected the status of women or the choice of women.The model of public policy which is centered in the recognization recognize the difference of the men and women,it affirmed the important value of household work and the unique identity and values of women,but it also strengthen the difference of the men and women,and therefore,it restricted women to be the existing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Therefore,for the gender equality,it is high time to make the two models of public policy to be one,mutual support of relative advantages.
gender perspective;public policy;gender equality;distribution;recognization
D035
A
1000-2359(2010)03-0060-04
刘笑言(1984-),女,吉林蛟河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女性主义政治学规范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 孙景峰]
2010-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