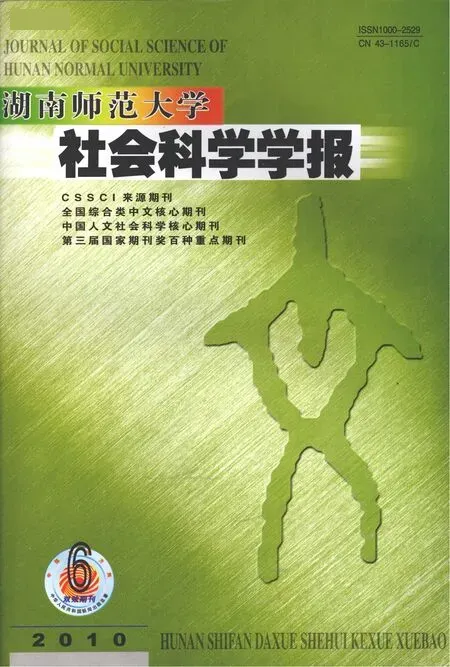骈文内涵的三个向度
吕双伟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骈文内涵的三个向度
吕双伟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骈文既独具中国特色,又内涵复杂,研究较少。从文体的原生性和发展性来看,骈赋、律赋和骈文为动态而不是静止关系,不同时代两者的关系不同;宋四六不能等同于骈文,但是四六则多被明清人视为骈文的别称;骈语是指文章的对偶句式,不能作为骈文的代称。正确理解这三者与骈文的关系,对骈文学和文体学的构建有重要意义。
骈赋;四六;骈语;骈文
由于汉字单音节特征适合对偶,又同义词丰富,加上古人阴阳对举的哲学观念异常强烈,导致“骈文”实体在魏晋就已经形成。经过六朝鼎盛、唐宋蜕变、元明衰落和清代复兴,“骈文”一直有自己的发展轨迹。然而,如此具有民族文化特色和曾经繁荣过的古代文体,因受到政治思潮和古今文学观念演变等影响,至今研究仍然薄弱。其中,赋与骈文关系、四六与骈文关系及骈语是否能代指骈文等也模糊不清,欲剪还乱。本文在前人较少研究的基础上,拟对此加以重新探讨。
一
古代文章,如颂赞铭箴、诔碑哀吊、章表奏启等文体都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各自的发展轨迹,故刘勰《文心雕龙》均对之“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如果这些文章以对偶句式为主,讲究隶事、声律和藻饰,清人就将之视为“骈体”或“骈文”。如陆《石阙铭》、薛道衡《老氏碑》、扬雄《十二州箴》、江淹《齐太祖诔》、沈约《上宋书表》、庾信《谢赵王赉丝布启》等李兆洛都收入了《骈体文钞》。曾燠《国朝骈体正宗》也收录了毛奇龄的《平滇颂》、《复沈九康成书》、《陆荩思新曲题词》,陈维崧的《刘沛元诗古文序》,胡天游的《拟一统志表》、《玉清宫碑》等文,各体兼备。可见,古人对于以对偶句式行文,讲究隶事、词藻甚至声律的文章,不管其文类如何,都将其归属为骈文。但是,对于同样讲究对偶、声律甚至隶事、藻饰的骈赋、律赋,古人随着时代不同而有不同看法,今人也聚讼纷纭。
骈文,或类似含义的骈体、俪体,在《全唐文》、《全宋文》中都没有作为别集、总集名称出现,也没有在其他现存唐宋文献中发现具有文体意义的骈体和骈文。①《樊南四六》甲乙集中收录的文章,其实就是清人视域中的骈文,但只收录了应酬交际性强的表启文章,没有收录赋。此后,宋代四六文别集较多,总集不乏,也是收录制诰表启等公牍性骈文,没有收录赋。可以说,在唐宋时代,尽管已经出现了清人视域中所认可的四六骈文,但赋,不管是古赋还是骈赋、律赋,都是被排除在四六骈文之外的。元代四六文衰微,对其范围延续宋人观点。明代前中期文宗秦汉或唐宋,六朝骈文和唐宋四六等之自郐。晚明出于对秦汉和唐宋文风的反拨,出于对骈文抒情写景的欣赏,文章转崇六朝。这导致了晚明四六选本和四六表启文创作的兴盛。在对前代四六选本的编撰中,逐渐倾向于将骈赋、律赋收入四六选本。晚明许之吉编选的《丽句集》虽为联句总集,但其实可视为四六选本的变体。该书多以各类文章中的对偶句入选,开篇就是骈赋、律赋中的四六联,如:“南冥王室之宫,爰皇是宅;西极金台之镇,上帝攸安。……三川之交,鹑火通其耀;七泽之国,翼轸寓其精。”(杨炯《浑天赋》)、“驱驭阴阳,裁成风雨。横斗枢以旋运;廓星汉之昭回。”(刘允济《天赋》)、“月既满而尤亏,日将中而如昃。掌握之内,安得容其九重;咫尺之中,岂能尽其五色。”(张仲素《管窥天赋》),等等。如果说晚明四六选本中,赋与骈文的关系还较为模糊,那么清代文人则打破前代惯例,开始在骈文集中收录赋体,如康熙间陈维崧的《陈迦陵俪体文集》开篇即为其律赋《璇玑玉衡赋》和骈赋《滕王阁赋》、《铜雀瓦赋》等。这种情况在乾嘉后更是屡见不鲜。嘉庆初年,吴的《八家四六文钞》也收录了骈赋,如吴锡麒的《星象赋》、《秋声赋》等。嘉庆二十二年刊刻的乐钧《青芝山馆集·骈体文集》卷上为《闻雁赋》、《忆梅赋》等。道光间胡敬《崇雅堂骈体文钞》四卷,开篇就为《阑干赋》、《水仙赋》等骈赋。道光十七年刊刻的胡承珙《求是堂文集》包括“骈体文”二卷,其开篇即为《棉花赋》。同治六年刊刻的钱振伦《示朴斋骈体文》卷一开头即为《述系赋》。骈文选本方面,姚燮《皇朝骈文类苑》、王先谦《骈文类纂》都收录赋体,将对偶的赋和表启序碑等视为骈文。这些充分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对骈文根本属性——对偶行文的认识深化,清人逐渐将骈赋、律赋视为骈体文的事实。当然,由于“骈文”之名到清代才通行,独立较晚;宋元明四六文主要用于公牍且没有收录赋体,加上赋为文学大宗且体裁独特,所以清人有的从骈体正宗的观点出发,没有将骈赋、律赋视为骈文而收录,如李兆洛的《骈体文钞》、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张鸣珂《国朝骈体正宗续编》等。
赋和骈文不是同一层次的文体概念,赋和颂箴铭赞等并列为体,而骈文其实是和散体文对举而生的。但赋和骈文在文学发展史上是相辅相成、彼此影响的。铺采文组纂宫商的汉赋为魏晋骈文的形成提供了形式上的要素,促使了骈文追求俪偶,崇尚藻饰的美文特征;而骈文形式的发展,特别南朝骈文的四六隔句对和结构特征,又反过来影响了赋体的骈化,因而形成了骈赋和后来的律赋。清代赋论家多从骈四俪六或对偶这一骈文的根本特征来解释骈赋特征。孙梅《四六丛话》中将赋视为其十八类四六文中的一体;又从隔句对等方面概括了骈赋和律赋的演变过程,指出了骈文和赋之间的紧密关系。追求对偶的赋体,加上其本身对词藻、隶事和声律的讲究,使得它与骈文在结构上、句式上基本相通。浦铣《复小斋赋话》论唐人律赋句法云:“律赋句法,不可但用四六,或六四,或七四,或四七。试取王辅文、黄文江滔、吴子华融、陆鲁望龟蒙诸家观之,思过半矣。”[1](P370)虽是对律赋句式的说明,但这些句式其实在骈文中更常见,从中也可见两者文体属性的趋同。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有云:“三国、两晋,征引俳词;宋、齐、粱、陈,加以四六,则古赋之变体矣。逮乎三唐,更限以律,四声八韵,专事骈偶,其法愈密,其体愈变。”[2](P8656)则更加明确从四六骈偶句式和声律调谐来探讨骈赋、律赋特征,可见其和骈文对偶特性的趋同性。除了音韵上要求比骈文严格外,律赋特征也和骈文一致。而四六隔句对在律赋中的大量运用,使得两者在文体属性上一致性更强。王瑶《徐庾与骈体》有云:“在文体的详细辨析上,骈赋多注重在雕纂,和碑版书记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属文时裁章句注重的形式美的条件,却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庾子山的各赋,就成为历代的骈文的典型了。”[3](P289-290)虽然只是用来说明骈赋和骈文的关系,但将之扩大到律赋和骈文的关系中也十分吻合。
现当代学者,受政治原因和文体本身限制,对赋和骈文的关系要么言之不详,要么知之不深,一般没有从不同时代两者的不同关系入手,厘清两者的动态关系和文体分类上的层次差异。其中,民国初年学者多认为赋可属于骈文。孙德谦云:“赋固骈文之一体。然为律赋者,局于官韵,引用成语,自不能不颠倒其字句,行之骈体,则不足取矣。”②肯定赋为骈文中的一类,虽然认为律赋写作方法和骈文不同。瞿兑之为《中国骈文史》作序则明确说骈文包括汉魏赋体、宋四六和近代似骈非骈的应用文字。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姜书阁《骈文史论》等也认为赋可以属于骈文。当代有些学者则反对将赋归属于骈文。简宗梧主张将赋和骈文区别对待:“赋和骈文这两种文类,它们的艺术特征和构成条件都是因时递变的,发展的轨辙是平行同向的,都随著时代的转变,开发新的艺术形式律则,引领风气。”[4](P4)虽看到了各自的发展轨迹和特征,但没有意识到骈文是从语言形式来划分,和散体文对举的大类文体,它可以包括赋颂箴铭等小类文体;虽看到了早期的平行发展,但没有看到清人已常常把赋归属于骈文的文学史现象。郭建勋《楚辞与中国古代韵文》中也从赋和骈文出现的先后顺序及句式特征来区分两者,认为以“赋”名则属于赋而不是骈文。但颂箴铭等文体的出现也早于骈文,它们可以属于骈文,为什么同种文类的赋却不可以属于骈文呢?马积高认为广义的骈文“包括骈赋及律赋”,狭义的骈文则“似指辞赋以外的俪体文”[5](P110-111),正是基于文学史上两者的动态关系而做出的正确判断,也体现了不同时期文人对赋和骈文关系的不同看法。
总之,文学史上,骈赋、律赋和骈文的关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是流动的而不是凝滞的。从古人视域来看,唐宋元到明中叶的文人没有将对偶的赋视为骈文,直到明末,特别是清代才有较多文人逐渐认为赋可以归属为骈文;从今人研究角度来看,认为骈赋、律赋属于骈文,并不是否定其赋体特征,也不是认为骈文早于赋体而形成,而只是根据骈文文体属性和清人对此问题的看法而加以当代判断的结果。
二
四六与骈文的关系也是莫衷一是而少见梳理。从骈文史来看,骈文在六朝被称为“今文”、“今体”,唐宋被称为“四六”,清代被称为“骈体”、“骈文”等。可以说随着“骈文”之实的演变,产生了“骈文”之名的代兴。六朝唐宋的“今体”、“四六”,到明清追溯四六文或骈文源流时,则多被笼统冠名为“四六”或者“四六之文”。那么,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是否可以认为文体学意义上的“四六”即骈文呢?两者是否异名同构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四六”,按字面理解,本意也是指一种句式。但自李商隐明确以“四六”来命名其文集后,晚唐和宋人多以四六来命名其骈体文集,因而成为事实上的骈体文名称。李商隐《樊南甲集序》云:“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唤曰《樊南四六》。”[6](P1713)《樊南乙集》也是将其讲究对偶声律的文章归类编撰,名为《四六乙》。这里的“四六”不仅和古文对举,具有“好对切事,声势物景”等特点,又代指其以四六对偶句式行文的公牍文章。所以,毫无疑问,从柳宗元的“骈四俪六,锦心绣口”中蜕变而来的“四六”在这里具备了文体的含义。而“四六”具备了文体含义后,其主要特点——文章主要以四六对偶句行文也比“骈俪”、“骈语”的单纯指向对偶句式的文体含义要明确得多。
随着晚唐五代骈体文的兴盛,加上李商隐四六文所取得的成就,“四六”逐渐成为当时对骈体文的通用称号。这种骈俪文风一直延续到北宋仁宗初年,公私文翰皆为骈体。到欧苏再次将古文运动推向高潮后,四六才被挤压到公牍应用文章领域。但四六成为骈体的代称,在宋代各种骈文别集、骈文话中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如今存王子俊的《格斋四六》、李廷忠的《橘山四六》、方大琮的《壶山四六》以及王的《四六话》、谢的《四六谈麈》等等。如果说李商隐的四六文专指公牍文体的话,那么五代宋初的四六文,则和六朝骈文一样,包含各类文体。当然在句式上,宋四六没有六朝骈文灵活多变,较多用四六对偶,且喜用长联俳偶,但这只是骈体文在不同时期形式上的差异,不是本质上的不同。如同宋四六被压缩到制诏表启等公牍应用文章领域后,散文笔法也被运用到四六中,形成新体四六,如苏轼、王安石的四六文,但两者本质上也一致。欧阳修《试笔》云:“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叙述,婉曲精尽,不减古人。”[7](P1893)已经将“四六”视为动态演变的文体名称,不同时期,不同作家表现出来的特征有所不同。南渡初年,宋四六再度繁荣,出现了汪藻、洪适、周必大、杨万里和陆游等四六名家。他们多用四六命名其骈体文章,这使得用“四六”代指骈文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宋元明清时代,不管是别集还是选本,多明确用四六指代骈体或骈文。
宋代较多以“四六”命名的文集和文话,如同以诗词命名的文集一样,当然强化了“四六”的文体意义,使其具备了独立性;同时,宋以后文人为了突出“四六”的文体性,多用“四六之文”、“四六文”来加强其文体属性。叶适论博学宏词曰:“宏词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偶对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2](P8656)杨慎为宋四六文作序感叹:“呜呼!四六之文,于文为末品也。”③黄始编选四六文时也说:“余持是以选四六之文,言之既祥,辨之至审。……四六之作,殆合理与情而兼致之欤?取二家之论,以究心于四六之文,夫亦知所要归矣。”④四库馆臣评《四六法海》“裨读者知四六之文,运意遣词,与古文不异。”[8](P1719)吴在《八家四六文钞》的各家题词中,多次用到“四六之文”:“余年廿有一,始从表兄汪存南先生学为四六之文。”“渊如早工四六之文。既壮,笃志经义,乃取少作弃之。”等等,都是用“四六之文”来指“四六”,从而强化其文体属性。可见,晚唐出现的“四六”,在之后的骈文批评史上,多被视为对偶之文,即清代所说的骈体文的代称。
当然,骈文之实体分别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应不同的文章特征,差别肯定有,即六朝今体、唐宋四六、清代骈体文有各自特征。但从文体本质属性上看,它们骈偶的主要特征相同;从文学批评和今天研究的角度来看,它们在骈文研究话语中可以等同。即唐宋四六不能等同于骈文,但是,“四六”却可以视为骈文的别称。南宋陈振孙评价四六文时有云:“四六偶俪之文,起于齐梁,历隋唐之世,表章诏诰多用之。然令狐楚、李商隐之流号为能者,殊不工也。本朝杨刘诸名公,犹未变唐体。至欧苏始以博学富文,为大篇长句,叙事达意,无艰难牵强之态,而王荆公尤深厚尔雅,俪语之工,昔所未有。”[9](P526)对齐梁、隋唐和宋代骈体文章特点加以点评,虽有褒贬倾向之分,但很明显视三者都为“四六偶俪之文”,即文体本质上相同。钱大昕则明确说“骈俪之文,宋人或谓之四六。”[10](P362)将两者视为相同而不是相异的同质文体。晚清朱一新更加清晰地把四六等同于骈文:“宋人名骈文曰‘四六’,其名亦起于义山。”[11](P90)来裕恂的《汉文典·文章典》中依次专列“骈文”和“四六文”。[2](P8677-8678)对于“骈文”,来裕恂从经典中追溯骈偶源流,对两汉、魏晋、六朝至中唐、宋代的骈体文作了简单梳理,其偏重点是“骈体”,没有从行文句式的角度来立论;对于“四六文”,来裕恂也偏重于骈偶,但更侧重的是其四六句式和“散联二句对”、“偶联隔句对”的行文方式;还对四六文从魏晋到南北朝、宋代的发展作了较为精要的归纳。对比之下可以发现,其侧重点都是骈体文的核心要素——骈偶,四六句和隔句对等都是骈偶的方式,因而两者文体本质相同;来氏叙述的“骈文”和“四六文”的发展历史也类似,两者构成了交叉关系。可见,作为文体意义上的骈体,“骈文”和“四六文”并没有本质差别。六朝骈文当然不同于唐宋四六,但是这不代表着骈文不能用四六来代称。“四六”批评史上,绝大部分时候它就作为骈文别名来代指此类文体。四库馆臣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不管是对于六朝骈文,还是对于唐宋四六,他们一律用“四六”来代替,反复将“四六”与“古文”对举,用四六代指骈体或骈文。如卷一九○《古文雅正》提要云:“独于文则古文、四六判若鸿沟,是亦不充其类矣。兼收俪偶,正世远明文章正变之故,又何足为是集累乎!”[8](P1732)卷一六四《秋崖集》提要云:“岳才锋凌厉,洪焱祖作《秋崖先生传》,谓其诗文、四六不用古律,以意为之,语或天出,可谓兼尽其得失。要其名言隽句,络绎奔赴,以骈体为尤工,可与刘克庄相为伯仲。”[8](P1404)
总之,作为不同时期的骈体文名称,“四六”和“骈体”、“骈文”有对偶形式和文风特征的差别;但作为文体,它们本质上都是相对于散体文而言的。六朝和唐代都没有“骈体”或“骈文”之名,都是后人根据其以整饬的骈偶句式为主而“追加”、“追封”的。六朝今体、唐代骈体和宋四六,为不同时期的骈体文称号因而不能等同,但这不能演绎为“四六与骈文有别”。“骈文”之名晚于“四六”,它的出现凸显了四六文以对偶为主但句式不一定多为四六的灵活性特征。这既是四六文发展成熟化、本位化的必然,也是作家和批评家在实践中对四六认识逐渐深入的结果。
三
1912年,36岁的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自序中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2](P3)其中,王国维用“骈语”作为“骈文”别名来赞扬六朝骈文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之和诗词曲等构成文以代兴的文体谱系。王国维不用前人反复使用的四六、骈体、骈文,却偏偏用了“骈语”来指代骈文。是不是“骈语”在古人的批评话语中总是用来指代“骈文”呢?
南宋刘克庄就已提到“骈语”:“世谓堆故事、参骈语起于唐,不知自西京邹、扬辈已然,至唐尤甚尔。及韩、柳出,而后天下知有古文,然韩、柳能变文字之体制,而不能变科举之程度。”[13](P216)其“骈语”明显是指骈偶,即对偶语言或对偶句式,没有文体上的指向。晚明游日章编《骈语雕龙》,全书分十七门、一百五十八子目,对每一子目都用骈语即对偶句式加以描绘铺陈,多类隶古事,组成文章片段,是典型的指导初学之作。这里的“骈语”也只是指对偶句段落而已。康熙年间,李绂主张古文辞禁用“骈语”:“一禁用四六骈语。凡古文皆直书其事,直论其理,而骈体则皆浮词,骈句又伤文体。欧公‘竹簟’、‘暑风’之语,犹有议者,不知公乃为两制序文,故兼一二骈语耳,他文则从不相犯也。或谓经传亦有骈语,然皆四字短句,气质古健,若骈丽长句,则断然无有矣。”[2](P4007-4009)其中几处用到“骈语”、“骈句”和“骈丽”,都很明显是指对偶句式,即对偶句;而其中的“骈体”则是与“古文”对举的文体学概念。两者区别非常明显。乾隆间,袁枚《与孙之秀才书》也从文体纯净和独立的角度出发,主张古文中不应有骈语:“奈数十年来,传诗者多,传文者少,传散文者尤少。所以然者,因此体最严,一切绮语、骈语、理学语、二氏语、尺牍词赋语、注疏考据语,俱不可以相侵。”[15](P642)强调古文中不能有“绮语、骈语、理学语”等,都是很明显的修辞学含义,“骈语”指对偶句式也一目了然。乾隆间陈廷会为陆繁四六文作序曰:“汉魏以来,扬雄、司马之属,孟坚、平子之流,缀而为赋,天下靡然向风,虽间有他作,皆错综骈语,遂有所谓辞人之文,此其变也。浸淫以至六季,而其风盛行。”④“错综骈语”也是指对偶句式的隔行悬合或宛转相承,不是指一种文体。嘉庆二十三年,周池辑录《骈语类鉴》,其序有云:“尔乃剪叶裁花,堆成美锦;熏香摘艳,选就青钱。”⑥所谓“剪叶裁花”、“熏香摘艳”就是选择对偶句式分门别类,为不同场合的骈文创作提供成句或獭祭材料。可见,书名中的“骈语”也是指对偶句式。
嘉道间刘开《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云:“夫经语皆朴,惟《诗》、《易》独华。《诗》之比物也杂,故辞婉而妍;《易》之造象也幽,故辞惊而创,骈语之采色于是乎出。《尚书》严重,而体势本方;《周官》整齐,而文法多比。《戴记》工累叠之语,《系辞》开属对之门。《尔雅》释天以下,句皆珠连;左氏叙事之中,言多绮合,骈语之体制于是乎生。”⑦在这封和王泽讨论骈体文的书信中,刘开提到“骈语之采色”、“骈语之体制”,单独的“骈语”都是指对偶句,和上下文合言之才可以指骈体文。又该文标题和刘开的文集分别用“骈体”和“骈体文”,而不用“骈语”,本身就可看出其含义的不同。嘉道间,包世臣读韩愈赠序文,有云:“《送李愿归盘谷》摹写情状,间入骈语,缓漫乏气势。”[2](P5237)此中的“骈语”,也毫无疑问是指对偶的语句,包世臣认为这种对偶句有损文气,造成文章气势不畅,缓无力。为胡天游文集作序,包世臣有云:“细绎机栝,在乎换成言,择字义,相类者更代以明新,于骈语习见者颠倒以示奇。”⑧其中的“骈语”也是指对偶句式,说胡天游在遣词造句上务去陈言,颠倒字句以见新奇。晚清陈衍有云“散文中杂以骈语,如阳湖派所为亦非体”[15](P43)及“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全是骈语,本不必论;惟此篇乃借灵运列传为题,统论周秦以下文人之荦荦大者”[2](P6721),其中的“骈语”都是指骈句,即对偶句式,即局部语言表达上的修辞特点;“全是骈语”才意味着该文为骈文,才具备文体上的含义。即“骈语”必须在特定的语言环境和上下文中,它才可代指“骈文”,但这种指代也很少见。其本身不具备独立的文体学含义。在古代,也没有以“骈语”命名的别集和文章选本,因而不具备“四六”因为句式而成为文体的类似环境。
“骈语”为对偶句式而不是文体,在古学渊深的现当代学者中使用更是十分明了。朱光潜在《诗论》中论述排偶文时,用到“骈语”:“汉人虽重词赋,而作者如司马相如、枚乘、扬雄都只在整齐而流畅的韵文中偶作骈语,亦不求其精巧,例如枚乘的《七发》。”在论述赋对于诗歌的影响时,也多次用到“骈语”:“汉人作赋,接连数十句用骈语,已是常事。”“六朝散文受辞赋的影响是很显然的。魏晋人在书牍里就已作工整的骈语,例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其中“骈语”意义很明显都是指对偶双行的句式,而不是文体意义上的骈文;是局部性的句子而不是篇章性的文体。钱钟书对骈文特征和流变有独到之见,对骈文、骈体文和骈偶、骈语的区别也十分清楚:前者为文体属性,后者为句式修辞特征。其《管锥编》云:“骈体文不必是,而骈偶语未可非。骈体文两大患:一者隶事,古事代今事,教星替月;二者骈语,两语当一语,叠屋堆床。……故于骈俪文体,过而废之可也;若骈语俪词,虽欲废之,乌得而废哉?”其中反复提到“骈语”,含义无一不是指向对偶句式,可见“骈语”代指骈文的现象十分罕见。台湾张仁青《骈文学》没有详细考索,简单地认为“骈文”别称有二十多种,包括“骈语”、“偶语”、“俪语”等,大陆绝大部分骈文研究者也沿袭此观点。这是值得商榷的。骈语、偶语、俪语等性质相似,绝大部分是指向对偶句式,特别是单独使用时,更是指对偶语句,不具备文体意义上的骈文概念。
综上所述,赋和骈文的关系具有动态性、流动性特征。对以对偶句式为主而行文的六代和唐宋文章,明清人除了用“四六”、“四六之文”等代指外,还有“骈体”、“骈体之文”、“骈文”等概念。而最具当代文体意义的“骈文”,无疑是对这种文章的最好冠名。到清代,随着文体意识的发展,更具有文体指向的“骈体”、“骈文”等才逐渐流行,特别是到晚清民国,“骈文”因为更加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文体含义,因而成为学术界广泛接受的骈体文章称号。王先谦《骈文类纂序目》曰“骈文之选,莫善于王闻修《法海》、李申耆《文钞》,倾沥液于群言,合炉冶于千载。”就明显地把《四六法海》收录的“四六”、《骈体文钞》收录的“骈体”都视为“骈文”,因为其立足点都是其以对偶句式为主的根本特点。骈文概念的核心,就是全篇主要以对偶句式行文,特别是以隔句对行文的文章,其他特征,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甚至不同作者的表现会有不同。古人极少用“骈语”来代指骈文,王国维“六代之骈语”使用不当。
注 释:
① 南宋孙奕《履斋示儿编·文说》“史重复”一目中有云:“《昭帝赞》言周成有‘管蔡四国流言之变’,夫举四国则管蔡已在其中矣,乃四字而骈文。”其中已经提到“骈文”,但其意为文意重复,不具备文体学意义。
② 孙德谦.六朝丽指[M].四益宦,1923.
③ 杨 慎.群公四六序,《升庵集》卷二,《四库全书》。
④ 黄 始.听嘤堂四六新书广集序[M].清康熙9年(1670)刊本.
⑥ 周池辑录.骈语类鉴[M].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光霁堂刻本。
⑦ 刘 开.刘孟涂集·骈体文:卷二[M].清道光六年(1826)姚氏山草堂刊本.
⑧ 胡天游.包世臣序.石笥山房集[M].清咸丰二年(1852)刻本。
[1]何新文,路成文.校证《历代赋话校证》附[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王水照.历代文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王 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4]简宗梧.赋与骈文[M].台北:台湾书店,1998.
[5]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 2版).
[6]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欧阳修,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9]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11]朱一新.吕鸿儒、张长法点校.无邪堂答问[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2]王国维.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三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3]刘克庄.徐先辈集[M].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六[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14]袁 枚.王英志校点.袁枚全集: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15]钱钟书.石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Abstrct:Parallel prose is a unique styl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ts content is very complicated and not yet studied.According to its nature and developmen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allel Fu,Lv Fu and Parallel prose is dynamic rather than static,that is different at different times;the parallel prose of Song Dynasty can not be equated to parallel prose,but siliu is considered to be another name for parallel prose;dual Language is the dual sentence of article,not parallel prose.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relationship is importa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arallel prose and stylistics.
Three Dimensions of Parallel Prose Content
LV Shuang-wei
(College of Literal Art,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parallel fu;siliu;dual Language;parallel prose
I106.2
A
1000-2529(2010)06-0120-05
(责任编校:谭容培)
2010-08-23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赋与骈文关系研究”(09YBB296);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骨干培养计划资助
吕双伟(1977-),男,湖南湘阴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