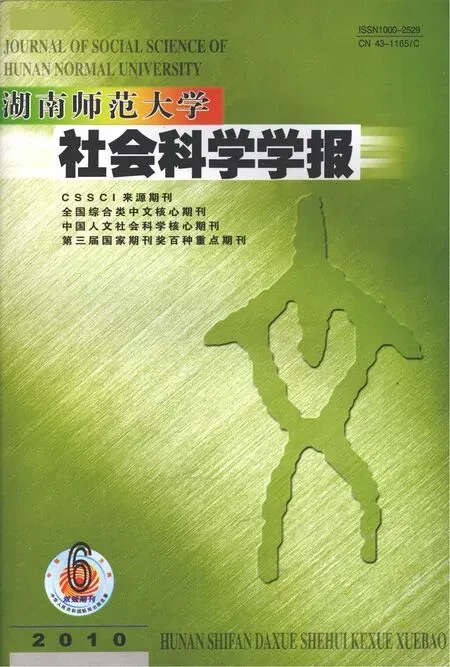从实践智慧到实践哲学——毛泽东实践哲学形成的历史背景、内在条件与思想理论来源
刘景钊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105)
从实践智慧到实践哲学
——毛泽东实践哲学形成的历史背景、内在条件与思想理论来源
刘景钊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105)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结晶之一,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实践智慧向实践哲学转化的过程。这种转化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个人的内在条件以及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促成的。毛泽东实践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阐述或解释理论概念而建构的哲学体系,而是始终着眼于对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
毛泽东实践哲学;实践智慧;历史背景;内在条件;思想理论来源
毛泽东实践哲学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重要的结晶之一,但其形成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从实践智慧向实践哲学转化的过程。如果说“实践智慧是一种有关实践或行为的明智考虑的理性能力”[1],那么毛泽东的实践智慧就集中体现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等重大实践问题上的理性判断与选择上。毛泽东实践智慧显然凝结着中国革命经验特别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经验,而毛泽东实践哲学则是在实践智慧基础上的总结、反思、提炼和升华所作出的哲学表达。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实践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阐述或解释理论概念而建构的哲学体系,而是始终着眼于对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而毛泽东实践智慧向实践哲学的转化和实践哲学最终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的延安,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深刻的历史背景、个人的内在条件以及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充分准备等多种条件促成的。
一、毛泽东实践智慧向实践哲学转化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既体现在理论创新上,又体现在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上,而且后者为前者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对错误路线的坚决斗争,不彻底清算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就不可能实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目的,因而也就不可能进行理论创新。集中表达毛泽东实践哲学的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同时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情况下还缺乏相应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过度依赖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因而在革命过程中连续出现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导致两次革命的失败。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于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与复杂的阶级关系缺乏了解,简单套用欧洲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解释中国社会状况,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从而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的严重错误则在于提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所谓主要敌人这一自相矛盾的观点,甚至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严格界限。这是他们脱离中国实际,教条式地搬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错误指示的结果。在民族危机愈益深重的情况下,教条主义的“左”右倾错误路线越显出其脱离中国革命的历史主题,背离中国革命的现实,如果不对这些错误路线进行彻底清算,就会对中国革命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因此,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首先在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上开展了清算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工作。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从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出发,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同时也向全党提醒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的危险。在报告中,毛泽东从中国当前形势的特点出发,紧紧抓住抗日救亡这一主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这是反对本本主义的继续,更是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是促使中国共产党从苏维埃革命向民族民主革命转变的一篇关键性政治文献[2](P130)。它为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也是后来毛泽东提出实践哲学的基础之一。“两论”正是在哲学上对这些思想的论证和总结。1936年12月,毛泽东又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彻底批判了脱离战争实际的军事冒险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错误。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更是构成“两论”的先导性重要文献。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无论从时间上来说(“两论”是八个月后完成的)还是从内容上来看,这篇文献都与“两论”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2](P131)。
然而必须看到,《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样充满哲学思想的文献,它们本身还不是“两论”这样具有普遍指导性的哲学著作,它们只是“两论”哲学思想的前导。从这些著作到“两论”,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一种哲学的升华[2](P133)。这种飞跃和升华也是毛泽东从其高超的政治军事智慧上升为实践哲学的过程。
毛泽东之所以首先在政治上与军事上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是因为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是中国革命的两个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而“左”右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最直接表现在这两个问题上。但是,光有对错误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批判,不可能彻底克服其影响。因为错误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是以其深层的错误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所以,清除错误的思想根源就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在毛泽东看来,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问题。他认为,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武装斗争(军事路线)和党的建设(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这三者是紧密相联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正确与否,体现了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反过来说,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3](P605)因此,毛泽东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之后,接着又着手批判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而“两论”的写作和发表,正是为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实践智慧向实践哲学的成功跃升。
二、毛泽东实践哲学形成的内在条件
如果说对错误路线的清算构成了毛泽东实践智慧向实践哲学转化的历史背景的话,那么毛泽东自身具备的深厚哲学素养和一生对哲学保持的浓厚兴趣,特别是毛泽东一开始选择哲学理论就表现出的强烈的实践倾向则构成了毛泽东实践哲学产生的内在条件。
“事实上,一个对哲学毫无兴趣或毫无哲学素养的人,即使现实的斗争如何需要某种哲学理论,也是很难写出有价值的哲学著作的。”[2](P125)的确如此!早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毛泽东就倾心于探讨大本大源的哲学研究,并立志要在理论上有建树。这同他就学于杨昌济门下,深受其影响很有关系。杨昌济先生一贯倡导圣贤精神,而圣贤超越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从而达到“闻道”的境界。杨昌济先生认为,“人不闻道,是为虚生”[4](P80)。而“闻道”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研究哲学[2](P126),因此,在杨昌济先生看来,“人不可无哲学思想”[4](P80)。杨昌济先生的这种思想给求学时期的毛泽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曾明确地表示过“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5](P86),并认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5](P85-86)为研究哲学,毛泽东还参加了杨昌济等人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从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即投身于社会实践活动中,也不再满足于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的“大本大原”,而是把注意力开始转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特别是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1920年6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5](P479)1921 年初,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介绍个人计划时称自己除了补足数学、物理、化学外,尤“喜研究哲学”[6](P32)。
而毛泽东哲学中鲜明的实践取向又同他早年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受学校湘学经世务实的文化熏陶分不开,特别是杨昌济先生在哲学、伦理学讲授中阐发的湘学传统中经世致用、注重实践和实事求是的精髓对青年毛泽东文化性格的塑造产生了重大影响[7]。在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投身革命,走南闯北、戎马倥偬,使他不可能做书斋里的理论家,也不允许他安静地在书斋里或在课堂上从容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且革命的实践和改造旧中国的使命感也决定了毛泽东不会再满足于做纯粹理论形态的哲学思考,但他却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逐步领会和运用了通过十月革命传入我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8](P49)。当年在延安崭露头角的青年哲学家和培元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的哲学讲座,迄今犹脍炙人口,他的讲授提纲——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之所以那么爽朗、生动、有力,这不仅由于他的文字流畅易读,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经验。这就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8](P56)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为什么能够同时成为一个哲学家。
沐浴过浓郁湘学经世致用文化传统的毛泽东,其哲学思想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实践性烙印。毛泽东在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前,也进行过多种理论的比较与选择,但最终以“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做不到”[9](P8)为由否定了其他种种主张而独取马克思主义一家。这意味着,“对他来说,‘事实上做不到’的理论,无论它本身是否说得通,无论它说得怎样动听,终究是没有意义的。这种以能否做得到,能否服务于实践来评判理论的价值的实践性性格,在毛泽东日后的思想理论中得到了更为透彻的阐述”[10](P528)。可以说,作为革命领袖的哲学家,毛泽东一生奉行的哲学都是以“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得到”为其价值标准,这就决定了毛泽东的哲学一定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
三、毛泽东实践哲学形成的思想资源
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形成既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资源的直接继承和在此基础上的创造,同时也是广泛吸取古今中外思想资源的综合创新。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12](P703)毛泽东实践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早在1920年就读了《共产党宣言》,并明确认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5](P162)。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尽管当时翻译过来的马列著作十分有限,但是,毛泽东还是反复精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延安的十年间,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包括《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资本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问题》、《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等等。在研读这些经典著作时,毛泽东写了数万字之多的心得、笔记和批注。有学者曾精确统计过,在《实践论》中一共引用了马列著作中的10条引文[13](P62)。其中直接引自马列著作的有9条,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引用1条,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引用3条,《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引用3条,还从列宁的《怎么办?》和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各引1条。毛泽东在论述中又对这些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发。《矛盾论》一共有25条引文,而直接引自马列经典著作的有16条。这些引文“主要是吸取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中的辩证法思想”[13](P65)。美国学者弗兰西斯·苏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列经典著作的渊源关系有过客观的评论,他指出:“就术语本身而言,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与其说是‘中国式’的,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可是,就其内容而言,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既是中国式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14](P143)在“两论”中对马列著作的引用都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这些引文的复述上,而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和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和发挥,从而使两论”成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的典范。
同时,毛泽东实践哲学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和科学总结的结晶。这与毛泽东从小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早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就读了诸子百家、《史记》、《汉书》、《唐书》等。而毛泽东一生都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历史、哲学和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他的书房中大量的书籍是中国传统典籍。生长在湖湘文化的环境中,更为其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经世致用的思想打下了基础。《实践论》就对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批判的继承、科学的总结和独到的发挥。从先秦到近代孙中山,我们历代哲学家在知行问题上虽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合理思想,但是,都没有抓住“行”的本质,都没有对“行”作出过科学的规定[13](P80)。他们或者把“行”归结为主观的活动,而否认“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否认“行”是“知”的来源;或者把“行”看作是按照封建道德标准化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和“伟人杰士”的冒险、探索和实验活动,都没有正确地理解知行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实践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哲学中的传统知行观在批判地继承、总结和革命地改造基础上,将其有机地融合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从而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知行观,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行观。所以,毛泽东后来在《实践论》重新发表时,亲自加上了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直接点明了《实践论》就是解决2000多年来中国传统哲学未解决的知行关系问题的。正如冯友兰在《〈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底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解决》一文中所道明的,《实践论》“正是发扬了自古以来的、认识论上的唯物论的传统,解决了中国哲学的知行关系问题”[13](P82)。
中国古代哲学中有着丰富的关于矛盾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哲学家已经提出了矛盾范畴,而且一直用矛盾范畴来表述客观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毛泽东则在批判地吸取我国传统哲学中有关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相互关系的合理思想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理,提出了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著名命题,创立了矛盾特殊性的原理,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理论。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实践哲学无疑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但这种继承是一种推陈出新的创造和发展,而不是简单地解读古人的学说或者套用传统哲学范畴来解释现代革命实践活动。
四、毛泽东实践哲学形成的中介环节
可以说,长征到达陕北后对哲学著作的集中研读是导致毛泽东由实践智慧向实践哲学升华的重要的学术动因。1937年初,到延安后,毛泽东挤出时间,“发愤读书”,不分昼夜地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阅读的哲学书籍主要是三十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其中主要是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和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在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上所写的批注约1.2万字,在米丁主编的《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所写的批注有2600字。
汪澍白先生在对《毛泽东哲学著作批注集》和西洛可夫《教程》(以下简称西氏本)和米丁的教科书(以下简称米氏本)进行认真的对勘研究后认为,毛泽东对《教程》和“教科书”的批注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是内容提要,第二是联系中国实际加以发挥,第三是摘录警句或引用成语典故来加深对哲学原理的理解,第四是总结概括,第五是对不同理论观点的批判[8](P112)。但无论采用了哪种方式,从整个哲学批注中,我们能够深深体会到毛泽东在阅读这些哲学著作时,关注的焦点始终是把教科书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也就是说他始终是带着问题来研读这些书的,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教科书的,我们从以下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印证这一点。
第一,结合对错误路线的批判来解读教科书阐述的辩证唯物论原理和矛盾关系。在读到西氏本中有关“列宁依照辩证唯物论的原则,不从一般的命题出发,而从客观的现实的运动出发,从客观的现实的一切方面的考察出发,从各阶级的地位与任务的分析出发……少数派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的命题出发,所以结果违背了唯物论的世界观之第一的而且根本的要求”这段话时,毛泽东批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15](P9)从这些批语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读苏联教科书时,会很自觉地同对当时党内的错误路线的批判相联系,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提炼升华自己的哲学思考。第二,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的研读。在读到西氏本关于列宁同孟什维克(西氏本当时译为少数派)的斗争中,批判少数派不结合具体现实、排除了特定阶级的革命行动并且不能提出关于斗争的正确口号时,毛泽东批注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具体的更好的推动各阶级的势力。”[15](P7)接着又写了这样的批语:“目前斗争的正确口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首先的问题是国内和平即国共合作。”[15](P7-8)第三,批注的理论焦点集中于对实践问题的阐发上,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在读到西氏本绪论中提到列宁关于“理论的思想(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这就是认识论的统一”旁边,毛泽东批注道:“机械论是服从盲目的自然,是理论与实践分离,是认识论上的分离。”[15](P5)对西氏本在第二章第二节中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实践的发展为基础而实现;人类如何认识周围世界的问题,在实践以外是不能解决的”这句话,毛泽东显然是多次反复阅读过,因为在这段话的下边先后用不同的5道线标示,并且批了提要和复述性的文字。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实践问题的深入关注和思考。第四,特别重视对矛盾问题的论述。据统计,在“西氏本”12000余字的批注中,涉及矛盾问题的即有6000余字;在“米丁本”2600多字的批语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批注文字也多达一半以上。由此可见毛泽东在阅读这些著作时的思考焦点所在。在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批语中,关于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事物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等问题又成为提要、概述和发挥的重中之重。把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所作的批语与原著对照,可以看出这些批语比原著的内容更明晰、更概括、更深刻,有的则发挥得更透彻。
通过《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毛泽东,他的实践哲学主要是来源于对实践活动的总结和实践性的思维方式。毛泽东对苏联教科书的研读,目的性和针对性很强,毛泽东对苏联教科书始终是带着问题边阅读边思考的,他的阅读兴奋点大多集中在与实践相关的问题上。这一点也可以从批注中的着重线看出来,每当读到西氏本中有关实践问题的段落时,下画线总是不止一道,显然这些段落是引起毛泽东格外关注而反复阅读的地方。毛泽东对实践问题的关注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来,在对西氏本的批语中,“实践”这个词出现了多达28次,语言学分析知识告诉我们,一个词在一篇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能够反映出这篇文献的关注点,批注中“实践”这个词的高频率出现也体现了毛泽东阅读西氏本时的思维兴奋点所在。
毋庸讳言,毛泽东在批读《教程》等哲学著作时,的确从苏联三十年代的哲学研究成果中撷趣了丰富的观点和材料。客观地说,西氏本和米氏本是“两论”产生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可以说,毛泽东对这两部哲学教程的深入研究是写作“两论”的直接准备,它们反映了毛泽东从政治军事思想到“两论”的哲学“脱毛”过程[2](P134),是毛泽东从政治军事著作到哲学著作的升华的一个中介。然而毛泽东的可贵之处在于,决不是生吞活剥,而是经过仔细咀嚼和消化,准确地掌握其思想精华,并用它作为武器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践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也是他日后撰写的“两论”为什么具有鲜明的实践哲学特征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毛泽东通向哲学的道路有着其特殊的路径。正如李佑新教授总结的:“毛泽东不是从对自然科学的深入研究,不是从对思维科学、文学艺术的探讨,甚至也不是从对一般历史发展的深层规律的研究而通向哲学的。他是经由政治与战争实践,特别是军事思想的研究这样一条特殊的道路而达到一般哲学的。这就规定了他的哲学思想与两论的特点。也使他区别于其他的哲学家,甚至区别于马克思、恩格斯通向哲学的道路。更区别于那些通过概念思辨而构造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们的哲学思考历程。”[2](P133)正是这种通达哲学的特殊之路决定了毛泽东的哲学必然是一种彻底的实践哲学。
梳理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形成线索,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这样一条思想轨迹:从一师时期受杨昌济思想影响,追求大本大原的哲学兴趣以及立功立言的雄心壮志,到立志改造社会,再到亲自投身社会实践,是一个从书斋走向实践的实践思想磨炼阶段;从积极参加各种革命运动,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再到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是一个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返回到实践的实践思维发展阶段;从领导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到同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再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主张是实践智慧成熟的阶段;从清算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上的“左”右倾错误思想到集中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再到“两论”的完成是实践哲学的形成阶段。这条思想轨迹实际上揭示了毛泽东实践哲学形成过程中的两个并行的路径,一个是实践反思的路径,一个是理论概括的路径。毛泽东是一个善于实践的人,更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人。所以他才有“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16](P186)这样的说法。总结经验的过程就是一个从理论上对实践活动进行反思和升华的过程。通过这样一个思想发展轨迹,我们便能深刻地理解,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和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是如何在实践哲学上统一起来的了。
[1]李佑新.毛泽东实践哲学论要[J].哲学研究,2007,(12):12-17.
[2]李佑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杨昌济.杨昌济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5]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6]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李佑新,陈 龙.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与湘学的经世务实传统[J].湘潭大学学报,2008,(1):1-4.
[8]汪澍白.毛泽东思想的双重渊源[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
[9]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0]何显明.超越与回归——毛泽东的心路历程[M].南京:学林出版社,2002.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金 羽,石仲泉,杨 耕.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新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4]弗兰西斯·苏.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15]毛泽东.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16]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From the Wisdom of Practice to the Philosophy of Practice——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Internal Conditions and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Sources of Mao Zedong’s Philosophy of Practice Formation
LIU Jing-zhao
(The Rescearch Centre of Maozedong Thought of Xiangtan Universtiy,Xiangtan,Hunan 411105,China)
Mao Zedong’s philosophy of practice formation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that changes from wisdom of practice to philosophy of practice.This transformation is from a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the internal conditions and personal theory and ideology contributed to the preparation.Mao Zedong’s philosophy of practice isn’t to explain the concept and theory building system of philosophy from the beginning on,but always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realit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process of summing up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 and reflection.
Mao Zedong;the wisdom of practice;philosophy of practice;historical background;internal conditions;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sources
A841
A
1000-2529(2010)06-0010-05
2010-08-2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毛泽东群众路线的集体意向性基础研究”(07BKS004);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及其当代意义”(04JA710001)
刘景钊(1957-),男,山西太原人,湘潭大学毛泽东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校:彭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