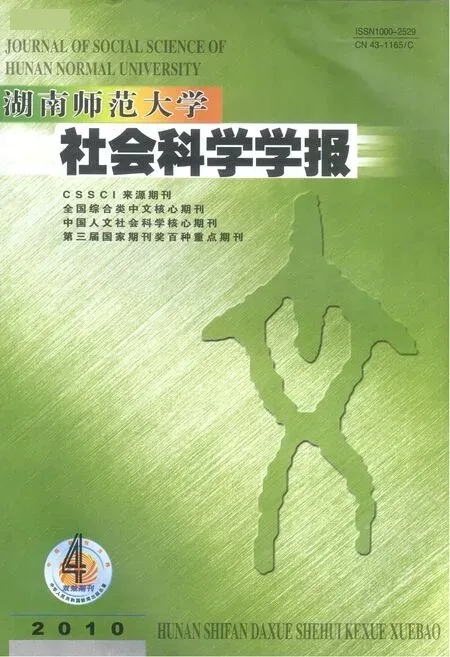美国新左派运动研究中的“衰落假说”
谢文玉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美国新左派运动研究中的“衰落假说”
谢文玉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新左派运动一直都是学者们颇为关注的研究领域。“衰落假说”是美国新左派运动研究中的一个醒目的解释框架,是该领域的学术权威。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假说受到年轻一代学者的质疑和挑战。美国史学界新左派运动研究中的发展趋势体现了时代变迁与学术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衰落假说”;新左派运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
20世纪60年代是当代美国学者最为关注的时代之一,而“60年代最有意义的就是社会抗议运动”。新左派学生运动是60年代社会抗议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贯穿于60年代始末,并延伸至70年代。自60年代开始,美国学者就对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进行了研究。许多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新左派最有影响力的白人学生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学民社”)的兴衰史上。这些研究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解释框架,被称为“衰落假说”。“衰落假说”从70年代初期开始形成,到80年代末达到鼎盛时期。在此期间,这种阐释框架受到其他学者的修正和挑战。但是,它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不仅成为新左派研究领域的主流解释框架,还激发了其他学者的研究兴趣,使新左派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本文拟对美国史学界有关新左派研究中的“衰落假说”进行考察,探究“衰落假说”的形成过程、主张和观点以及受到的挑战和修正,从而说明美国史学界新左派研究的发展趋势,管窥时代变迁与学术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衰落假说”简介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美国学术界对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群体登上政治文化抗议的舞台开始关注。从6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们即开始关注新左派运动中重要组织的研究,其中尤以“学民社”为主要研究对象。
但以“学民社”为中心的早期研究并不深入。研究者大多是学生运动的同情者,他们整理和编撰了有关文献集,探讨了“学民社”的历史根源、起因、学生主体的特征及其创立、发展、壮大、衰亡的过程,组织原则和政治目标等。简言之,早期有关“学民社”的学术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1973年,一位同情学生运动的年轻史学家科克帕特里克·萨尔出版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编年史,详细地叙述了“学民社”形成、发展、壮大和衰亡的过程。此后,在关于60年代学生运动的研究中,美国史学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建立在萨尔阐释基础上的统一的叙述框架,被年轻一代学者称为学生运动研究中的“衰落假说”——即主要对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学民社”的兴衰史及其意识形态的研究,尤其注重对组织领导人的研究,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视角。
“衰落假说”学者所塑造的“学民社”形象大体一致:一批出身富裕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受到各种激进思潮的影响以及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的吸引,在60年代初期南下,与黑人学生民权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一起,为黑人争取公民权利而奋斗。尔后带着变革社会的伟大理想和抱负重返精英大学,创建各种新型政治组织,其中尤以“学民社”为代表,在“参与性民主”等乌托邦思想的推动下,最初试图建立与自由派的联盟,在现行体制内实现社会变革。但是,美国政府在冷战意识形态驱动下卷入越南战争,致使国内改革进展缓慢,青年知识分子对自由派改革日益失望,尤其是越南战争不断升级,更涉及其切身利益,于是,许多人走上了反对现行体制、与国家权力机构直接对抗的道路。最后,由于组织本身内在的矛盾性和后期领导人的决策失误,“学民社”逐渐走向衰落和瓦解,而该组织的衰落标志着新左派运动的结束。“衰落假说”也因此而得名。
“衰落假说”早期主要代表有科克帕特里克·萨尔、厄尔·安杰和威妮弗蕾德·布雷恩斯等,80代末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前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如詹姆斯·米勒、莫里斯·伊舍尔曼、托德·吉特林、汤姆·海登等,他们于1987年-1988年相继出版了有关新左派和“学民社”的著作,从而将“衰落假说”提升到醒目的位置,使关于新左派运动的研究达到高潮,也引起了年轻一代学者的挑战。下面将具体介绍他们的主要观点和主张。
二、“衰落假说”的主张和观点
“衰落假说”中有几个反复出现的主题。首先,他们都对“学民社”早期的政治改革予以了高度评价,对“学民社”政治纲领《休伦港宣言》和其核心价值观“参与性民主”甚为称赞。但他们也对“参与性民主”中存在的悖论,对“学民社”缺乏有效的组织机构,对组织后期领导人日益走向好战和暴力的倾向进行了批判。
萨尔指出,“学民社”不仅“塑造了一代人的政治”,还是“30年来第一次重新点燃了美国激进主义火焰”的组织,代表着“60年代美国左派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个组织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催化剂,先锋队和人格象征”。米勒则称早期行动主义者发起了“美国历史上最后的伟大的民主理想主义实验”,而《休伦港宣言》则是“战后美国历史上纲领性文件之一”,宣言提出的“参与性民主”是新左派对美国政治思想最突出的贡献。伊舍尔曼更是将“学民社”看成是学生激进群体中“最重要的”组织,并且声称,“不久,它将被认为是‘新左派’的同义词。
理查德·弗莱克斯则指出,尽管他们没能如愿以偿地构建一个他们在《休伦港宣言》中规划的美好社会,但“《休伦港宣言》至今仍值得重视,不为别的,就因为它为政治词典引入了一个新的词汇,即‘参与性民主’”。海登则不仅对“休伦港一代人”及其核心价值观“参与性民主”予以了充分肯定,还对“参与性民主”的思想源流进行了考察,指出他们那一代人的理论探索和政治改革尝试和试验是对美国传统的继承、发展和弘扬。
但是,米勒和吉特林等人认为,“学民社”的最后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参与性民主”中本身所蕴涵的“致命因子”和“邪恶种子”。
米勒指出,“参与性民主”是一个很宽泛的政治设想,但是,这个设想没有很好地受到审查。其中一些重要问题没有得到廓清,而且“参与性民主”没有作为一个正式的民主原则在休伦港会议上被讨论并获得通过。“休伦港一代”没有找到共同认可的途径来实现统一的目标。结果,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混乱性导致了一系列危机的出现,例如在领导权、组织形式、决策制定和目标等问题上的不确定性使“学民社”危机重重。这些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民社”成为非理性的、鼠目寸光的策略和战略的牺牲品,从而阻碍了它完全实现其道德力量。这些危机也为60年代后期新左派最终走向瓦解和崩溃铺平了道路。
这种“自我毁灭”的主题反复出现在这些前行动主义学者的论著中,他们都提到运动中的表现主义政治学是导致运动衰落的原因。他们认为新左派政治学是个人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而这种注重个人性和道德性的政治学推崇的是与政府的冲突和对抗,结果必然导致组织本身的衰落和灭亡。如吉特林毫不掩饰自己对后期新左派暴力行为的厌恶,他指责说,新左派运动的衰落是自取灭亡,因为到60年代后期,新左派运动不仅存在结构性的缺陷,缺乏组织纪律性,还推崇过度民主,埋没了运动中那些富有领导经验的人的才能,致使宗派主义激进派渗透到了组织中来,导致组织采取了毫无思想和远见的好战主张。结果,一种极端主义政治学和“死亡文化”应运而生,认为只有冲突、两极化和中断一切才是最重要的政治学,结果导致了“学民社”的灭亡。
另外,他们特别突出早期运动中男性领导者的地位以及他们当时所取得的成就,特别强调早期新左派领导层和“学民社”在运动中的作用。他们一般将1968-1970年期间,“学民社”逐渐走向衰亡的过程看作是整个新左派运动的结束。他们还特别注重对新左派尤其是“学民社”的衰落对于其他运动造成的后果的描述,以突出“学民社”在整个60年代新左派运动中的突出作用。而其叙述对1968年以后发生的大规模基层运动关注不多:即那些并不依赖全国性组织的区域和地方行动主义者所进行的活动。对于这场他们亲自参与的运动,他们认为,从短期看,新左派运动失败了,但是,从长远效应来说,新左派运动留给美国人的遗产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像大多数盛赞60年代运动的学者一样,吉特林认为,60年代运动的最大遗产就是一个具有民主意识的市民群体获得新生。他对美国社会中“市民直接行动原则深入人心”的现象表示赞赏。而海登对60年代运动产生的积极作用所做的总结可以说代表了这些学者共同的心声,他说,尽管有外部的压制和内在的荒谬,60年代这一代人比美国历史上以前的绝大多数其他各代人所取得的成就都要多。我们在南方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种族隔离。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掀起了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运动。我们对大学进行了改革,在政治上使千百万青年人获得了选举权。我们激起了妇女权利和环保主义的意识。我们用强有力的参与民主制伦理强化了民主。
他们在著作中多处强调学生运动是对激进主义传统的继承,而且,其著作中所表现的主题也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这场延续时间长达十年之久的学生激进运动,说到底是一场在体制内进行社会变革的运动,是承继了美国历史上激进主义传统的一场变革运动,而不是像有些保守主义学者所称的,是对美国社会造成巨大危害的、“离经叛道”的乌托邦激进主义运动。
他们还特别强调,南部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不仅给和平主义者提供了灵感和动力,也成为60年代激进学生运动的动力源泉。如海登在《重聚》中叙述了自己远赴南部腹地,积极投身南部黑人民权运动,帮助南部黑人进行投票登记的活动。他们认为,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不仅激发了60年代早期新左派行动主义者们的理想主义激情,激发了他们追求正义、公正、平等社会的信念,激发了他们与社会弱势群体同舟共济的决心,也为他们日后进行激进主义运动提供了组织、领导、战略策略等方面的准备。
总之,他们对于新左派学生运动的记忆和认知,尤其是他们关于学生运动衰落原因的分析与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和老左派差别不大,他们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评判新左派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也是从主流社会的立场来看待新左派后期好战和暴力所带来的危害性,他们也同样认为新左派后期失去理性的过激行为是一种愚蠢的乌托邦主义。可以说,他们对于新左派学生运动的认知与他们成长时期所受到的传统激进主义思想密切相关,与他们自己在运动中扮演的领导者角色相关联,还与他们在回归主流社会的过程中受到保守派猛烈攻击不无关系。他们从自己独特的经历和立场出发,讲述了新左派运动的兴衰史——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故事:“学民社”经历了从“休伦港”到“芝加哥围攻”,从“希望的时代”到“愤怒的岁月”,最后在一片喧嚣与混乱中走向了灭亡。这是一个关于“美国的分裂”的故事。
三、对“衰落假说”的挑战
在“衰落假说”形成、发展和不断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将关注目光投向新左派在具体领域和地方个案中的研究,开始对“衰落假说”仅注重新左派和“学民社”组织及其领导人物的研究路径提出了挑战并进行了修正。
一些论著从妇女解放运动和劳工角度对新左派进行了探讨。萨拉·埃文斯认为激进女权主义运动是从新左派内部和民权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它们为激进女权主义提供了组织形式和思想意识形态。但是从新左派中沿袭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也成为妇女解放运动在70年代支离破碎的主要原因。艾丽思·埃克尔斯的《大胆变坏》同样叙述了民权运动,“学民社”和黑人权力运动在无意识中催生了激进女权主义的过程。她们的研究表明,新左派运动并没有随着“学民社”的衰落嘎然而止。
彼特·B·列维则探讨了劳工与新左派的关系。他认为,应该抛弃把新左派看作是一场中产阶级革命的怀旧式的记忆。列维指出,一些学者认为新左派反对传统的政治观念和策略,尤其反对被赖特·米尔斯所嘲讽的“劳工形而上学”。事实上,在60年代前半期,青年白人和黑人激进派认同左倾工会组织的很多社会民主观念,也意识到要实现这些目标,蓝领工人阶级的地位不容忽视。而当时的工会组织对“学民社”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南部农村和北部贫民窟从事的活动也给予了极大的经济援助。该书对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阐释了新左派和劳工之间的复杂关系。
还有学者将新左派运动的结束时间往后推到了80年代。他们对60年代以后的新左派在基层的民主实践进行了探讨,从而突破了“衰落假说”所认为的新左派运动终止于“学民社”衰亡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到80年代,新左派作为一个为人们所认可的全国性运动不复存在。但新左派思想中一些重要观念和信念并没有消失,而是逐渐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生活中,形成许多新型的基层民主运动。学者们主要探讨了新左派在60年代所倡导的参与性民主以及“学民社”试验过的“经济研究与行动项目”在州和地方一级的繁荣昌盛。
哈里·波伊特在《后院革命》中探讨了“参与性民主”中体现的超验精神。以前行动主义者为基层民主运动骨干的“后院革命”围绕着公民权利展开,他们在地方和社区发起了反对大公司、公共权威机构和政府官僚机构的抗议活动,而这些都植根于60年代学生运动对官僚体制、公司制度化和技术统治的抗议。一些学者还考察了前行动主义者从60年代到80年代的生活轨迹,发现他们在成年生活中继续其年轻时代的理想和抱负,将活动的舞台从全国转向了州和地方的政治和社区事务,开展“新市民主义运动”和其他各种涉及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权利和权力的活动,如环保问题、妇女权益、堕胎、同性恋权利、老年人权利、大麻的使用、核能问题以及消费问题等。
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当“衰落假说”达到其鼎盛期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或撰文,或著书,从不同的角度对其主要观点提出了质疑,新左派运动研究突破了单一的解释框架,在诸多学者的共同探索和努力下,研究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
最早撰文比较系统地对“衰落假说”观点提出挑战的是威妮弗蕾德·布雷恩斯,她在“谁的新左派?”一文中从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她认同“衰落假说”对60年代早期“学民社”的肯定评价,但认为他们过分强调了“学民社”的衰落对其他运动所造成的后果,夸大了学民社在新左派运动中的作用,忽视了1968年以后发生的大规模基层群众运动,对60年代新左派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描绘得过于狭窄。另外,“衰落假说”在分析新左派失败原因时,将衰亡责任归咎于运动后期的好战和暴力性,认为与政府的暴力行径和压制措施关系不大,对此布雷恩斯不能认同。她认为,运动中表现的暴力倾向和好战情绪是激进行动主义者对政府暴力行为的回应,他们的分析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性。最后,她对他们提出的新左派是一场失败了的运动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她认为,新左派和“学民社”包括策略性和预示性政治,如果仅从策略性政治看,新左派运动无疑是失败的,但是,新左派和“学民社”所推崇的“参与性民主”是一种预示性政治,它强调直接的民主形式、一致同意的决策制定、分权以及集体生活模式,这些对60年代以后的美国政治和文化,尤其对女权运动、环保运动以及基层民主运动的影响深远。
和布雷恩斯一样,一些学者也对新左派应该对“运动”的衰亡负主要责任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机构,如“联邦调查局”的反情报计划(Counter-Intelligence Programs:COINTELPRO)对政治行动主义,尤其对新左派运动具有灾难性影响,对60年代激进政治运动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在运动后期,美国政府及各级行政部门加大了对运动的控制,大量便衣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渗透到运动中并进行破坏活动,美国政府还通过司法机关采取法律手段对运动进行打压,美国国民警卫队和警察机关对学生抗议活动进行强制性压制的行为时有发生。社会学家杰克·瓦伦和理查德·弗莱克斯也特别强调美国当局的压制措施对新左派衰亡产生了重要影响。
年轻一代学者在以上修正观点的基础上,对“衰落假说”提出了更多的质疑。比较突出的有艾伦·史密斯,他总结了当代史学家对“衰落假说”的挑战。第一,当代史家更强调50年代对60年代抗议运动所产生的影响;第二,认为60年代抗议运动与70年代以降美国社会改革运动之间存在连续性;第三,认为“衰落假说”的解释不足以说明保守主义势力在80年代的兴起。同时,他还对“衰落假说”将新左派和早期“学民社”结合的历史编撰史提出了挑战:首先,他认为“衰落假说”夸大了《休伦港宣言》中表达的意识形态与老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分歧;其次,他们对和平主义在新左派诞生中所起的作用估计过低;另外,他们不能解释新保守主义的兴起,民主党自由主义的衰落以及新型社会运动在60年代以后的蓬勃发展。
学者们尤其对“衰落假说”只关注全国性组织和领导人物的精英视角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尽管“学民社”是新左派运动中是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组织,但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力量很大一部分来自下层民众的自发行动,所以,批评者提出,有关60年代新左派运动的叙述必须跨越组织史和领导人物传记的樊篱,走向某种“来自底层的历史”。90年代学者对“来自底层的历史”给予了更多关注,涌现出越来越多对新左派基层民众活动的描述。
在整个新左派运动研究中,从精英视角转向基层民众的研究路径是从反战运动研究开始的。学者们将关注焦点投向基层民众的反战运动,将新左派运动的结束时间向后推到了70年代初期。一些学者论述了“学民社”分裂后,其他新左派群体的反战活动及其作用。有的则转向地方反战活动,如肯尼斯·海涅曼对密歇根等州立大学的反战行动主义者进行了比较研究,从两个方面对“衰落假说”提出了挑战:第一,反战运动没有对结束战争起推动作用,反倒促成了保守主义势力的回潮;第二,在州立学校,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给反战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和价值观,所以,60年代的政治舞台上不仅有新左派学生运动,还存在其他各种反战力量,而“学民社”在他所分析的几所校园内的作用并不明显。
最先提出“衰落假说”一词的范·高斯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将新左派运动的起始时间向前拉到了1956-1960年期间,指出古巴革命和菲尔德·卡斯特罗对美国新左派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其次,他认为新左派不仅包括白人中产阶级青年,也包括黑人行动主义者;他还认为,新左派不仅源于自由派传统,也源自于60年代以前的激进派传统,它包括各种激进派群体和个人,具有结构多元性和非正式的特点;而且,他还特别强调大众文化对60年代新左派政治的发展和重新兴起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而最先尝试将各种运动放在一本书中来叙述的是特里·安德森,他认为70年代初期是“走向新美国运动”的时期,具有“行动主义万花筒”的特征。随着“学民社”的分裂和瓦解,美国社会中的行动主义者不能一言以蔽之;许多参与者转向其他各种问题,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与层面同权威机构抗衡。所以他考察的是60年代所有为了社会变革而参加运动的行动主义者,而不论其种族、肤色和性别。
一些学者“从底层写历史”的视角对地方新左派进行了个案分析。有的分析了60年代伯克利地区保守派、自由派和激进派之间的权力之争,认为6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社会动乱实际上就是关于权力的争夺战,折射出整个美国社会的图景。而道格拉斯·罗西诺则探讨了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校园学生激进主义的发展过程,认为60年代激进运动的源头可追溯到美国革命中清教徒的改革运动,指出宗教在新左派起源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保罗·里昂也通过对60年代和70年代费城白人学生行动主义者的研究,试图解释整个新左派的成功与失败。他指出,新左派是一个范围很广的运动,不是某一个组织所能涵盖。其研究表明,“学民社”在费城的影响并不大。他还强调,60年代的费城学生绝大部分对学生运动漠不关心,只有极少数人加入新左派,从而揭示出新右派在60年代以后取得胜利的原因。
四、总 结
通过考察近几十年来美国新左派研究中“衰落假说”的形成、发展、繁荣和受到挑战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时代发展、社会文化生活观念的变化与史学发展的密切关系。如前所述,“衰落假说”学者大多是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骨干,或者是对新左派运动表示同情的人士。60年代学生运动所引发的政治和文化剧变对当时还是青年人的他们产生了巨大影响。步入中年后,他们有的成为学术上的权威人士,有的是重要的左派政治人物。作为一个受过60年代政治熏陶的特定群体,他们成为撰写60年代运动历史的主要人选。
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尤其在里根保守主义势力上升时期,60年代新左派运动往往是保守派攻击的对象,而“衰落假说”学者作为运动的参与者,对自己年轻时代的激情和投入运动的热情并不感到后悔。作为回应,他们纷纷著书撰文,为自己年轻时代的行为辩护。他们所构建的有关新左派运动的解释框架,从内容到形式,不仅反映了他们成长时期所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熏陶,体现了他们作为参与者为自己的激进过去辩护的需要,也是他们对现实世界中保守派的猛烈攻击的回应,反映了他们对于自己当下存在所进行的必要解释,即利用过去历史为自己的现时存在作注解。可见,在“衰落假说”所构建的新左派历史中,在他们对于新左派历史意义的把握中,折射出他们的现实关怀和人生际遇。正如司马迁著《史记》,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志向外,也是他遭受酷刑后发愤而为的结果,带有“述往事、思来者”的意图。美国历史学家卡尔·戴格勒早就注意到了史学和现实之间的互动,认为:“作为价值的反映者和供应者,历史学既是现在的原因,同时又是现在的结果。”总之,历史学家生活在现实当中,现实生活必定要反映在他的论著之中。[1]
同时,“衰落假说”形成、发展、繁荣和受到挑战的过程与美国史学发展的趋势基本一致。兴起于60年代的新左派史学通过分析社会底层来研究美国历史,“自下而上”地重写美国历史,成为年轻一代史学家挑战“衰落假说”注重精英视角的重要武器;而新社会史学注重向来不为传统史学家所注意的种族和社会群体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并从这一立场出发对美国历史进行多元化解释,也成为新一代史学家构建有关新左派历史的重要内容。任何史学流派和解释框架,都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而受到质疑和挑战。新一代史学家,即那些没有经历60年代运动的学者们所构建的有关新左派运动的历史,必然不同于“衰落假说”,他们必定从自己所处的现实世界和个人视角来形成自己对于运动的阐释和认知。但是,对于新一代学者来说,要写现在仍能做出回应的人们的历史很难,而要写的如果是那些对你的作品做出专业性评价的人的历史则难上加难。这也是“衰落假说”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主要原因。
在时代的变迁与社会文化生活观念的变更中,“衰落假说”受到年轻一代学者的挑战,但因为亲历运动的“衰落假说”学者仍然健在,使历史学家对于新左派运动历史的构建和保存成为一种动态的社会和心理过程,使不同史家对于新左派运动的交谈和思考形成对话和竞争的话语体系。“衰落假说”学者构建的解释框架激发了新的解释,形成新的认知,而各种记忆与认知互相作用,相互竞争,不断促进新左派运动研究的深入,从而推动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新左派运动的研究兴趣有增无减表明60年代新左派运动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也说明近几十年来“衰落假说”对推动美国史学界有关新左派运动研究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2]
目前,在“衰落假说”的推动和促进下,美国史学界对新左派运动的研究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第一,对新左派和新右派的比较研究日渐增多,对60年代的研究也从仅注重新左派和“学民社”的研究转向开始关注新右派;第二,将新左派和“学民社”的历史放在更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予以关照,在“衰落假说”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形成新解释;第三,跨学科趋势明显,学者们运用社会学、历史学、人类文化学、政治学和文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对新左派进行研究;第四,研究日益走向微观化,学者们通过对细微事件、具体个人的探讨,希图以小见大,从具体个案中得出普遍性结论。学者们的努力使有关新左派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
[1]李剑鸣.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的立场[J].社会科学论坛,2005,(5):19-21.
[2]杨 玲.美式民主掀起的“颜色革命”及其警示[J].求索,2009,(5):56-58.
(责任编校:文 心)
“Declension Hypothesis”in Study of American New Left Movement
XIE Wen-yu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American New Left Movement in 1960s has been a hot researching subject since 1960s.“The Declension Hypothesis”is a striking interpretation frame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New Left Movement and is an academic authority.But with times changing,the hypothesis is faced with questioning and challenges from younger scholars.The development and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field of American New Left Movement show the interplay of the changing times and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the declension hypothesis;new left movement;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D07
A
1000-2529(2010)04-0123-05
2010-01-05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的历史记忆与历史重构”[09YBA107]
谢文玉(1968-),女,湖南湘乡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