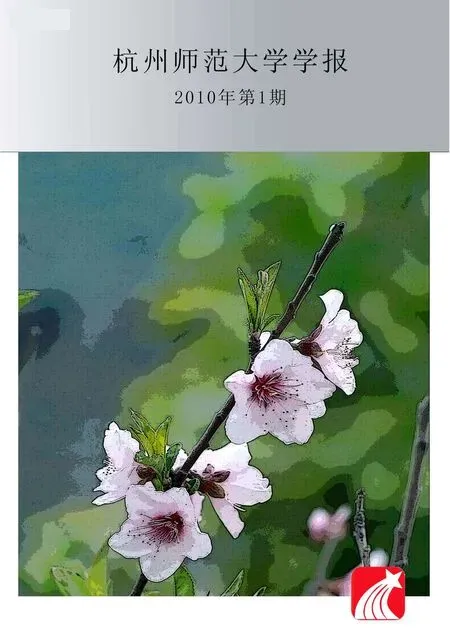正义的美感
——金庸小说的一种读法
徐 岱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正义的美感
——金庸小说的一种读法
徐 岱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金庸小说的意义无可置疑,但其价值确认仍有待进一步辨析。如果以“好小说体现文学艺术的魅力,伟大作品呈现精神境界的高度”这个观点为据,那么我们应该明确承认,金庸作品不仅是通常所谓的“好小说”,而且是能与古今中外那些文学经典相提并论的“伟大小说”。这着重在金庸的武侠叙事通过对以“侠士道”为核心的“中国精神”的艺术呈现,对“审美解放”与“诗性正义”作出了成功的文学诠释。
金庸;武侠小说;审美正义
一 经典的构成
若干年前,新武侠小说家之一的温瑞安在《析雪山飞狐与鸳鸯刀》一书里提出一个问题:金庸的小说是不是伟大的作品?他认为,“武侠小说只要写得好,一样可以成为伟大的小说。”作者对金庸小说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最终给予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已超越了‘好’,接近‘伟大’”的评价。[1]自此以后,这个评价陆续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响应。
从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萨克雷的“小说只会描写热恋的人和作战的人”*引自[俄]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31页。这个观点来看,中国的武侠文学无疑具有一种文体优势。侠士们不仅是英勇的战士,往往也是热血的情人。而在金庸小说中,这两者被演释得淋漓尽致。熟悉金庸作品的人大都会同意这样的评论:“金庸的武侠小说既可以当成武侠小说来看,又可以当成言情小说来看。”[2]但显然,侠骨柔情的故事可以成为好莱坞大片的票房保证,也是金庸小说构建情节和刻画人物的特色所在,但决不是其在20世纪中国文坛独领风骚的奥秘所在。
诗人聂鲁达说:使诗人难以忘怀并感动得柔肠寸断的,乃是体现许多人的愿望的事情,哪怕只短短的一瞬间。[3]这无疑乃经验之谈,问题是这“许多人的愿望”究竟又是什么?经验让我们的目光落在一个熟悉的词:人性。古往今来,所有优秀作品无不是经受住了人性这把尺度的评估才得以成为经典,对人性的关注无疑是优秀作家们的共同点。从古往今来的艺术与文学杰作来看,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艺术对人类是根本性”的这一宣言,而不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政治修辞,那就有必要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理解过去300或者400多万年以来,由自然选择进化出来的‘人性’这个框架之中。”[4]所以沈从文这样阐述他的创作理念:“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零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引自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00页。
不受政治学欢迎的人性,总是受到文学艺术家的青睐。但它失之于抽象。有个最常见的界定:小说家所关注的人性主要是爱情。托尔斯泰在其《安娜·卡列尼娜》里,借女主人公的口说:人之需要爱情犹如饥饿的人需要面包。这肯定有道理,于金庸小说当然说得通。认为“爱情事件是金庸小说故事的根,若非爱情,则许多部金庸小说势非今日的面貌”,[5](P.140)这肯定言之成理。很难想象,没有爱情故事的金庸小说会成什么样子。但事情的“吊诡”也在这里:金庸小说其实同时表现了爱情的动人和消解。回顾金庸小说就不难发现,在作者笔下,真正动人的爱情故事无不以“有情人不成眷属”的不幸结局收场。
比如《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和霍青桐与喀丝丽这对草原姐妹的关系,《飞狐外传》中胡斐和袁紫衣的关系,《天龙八部》里的萧峰和阿朱,《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和苏普的关系。相反的故事在满足读者的期待的同时,也减弱了其艺术感染性。比如《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最让人们为之动情的是他俩的爱而不得。当他们的爱情终于如愿以偿尘埃落定,便只有退出江湖的结果。令狐冲和任盈盈的故事也同样如此。否则,这两对英雄情侣的结局就会像郭靖和黄蓉那样,由一代侠侣沦为一双知名武将与主妇的故事。所以,《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不幸遭遇催人泪下,而以一种忧伤旋律结束的《廊桥遗梦》更能让人回味。通过人世缠绵动人的爱情,让我们窥见生命的难以承受之重。
美丽总是愁人的,我们为如此美好的缘分只有死神方能为其祝福而深感震撼。历经人世苍桑的金庸先生无疑深悉这个奥秘,他曾说:“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淡成了茫然。”*据杜南发等《长风万里撼江湖》,载《金庸茶馆》第5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第25页。在小说《飞狐外传》的结尾,我们从出家为尼的圆性口里读到这样的佛偈:“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因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咀嚼其中的意味,我们会从这对有情人的这种际遇中,领悟到更为复杂的体会。从这个意义上看,真正伟大的爱情小说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其歌颂爱情,而是由此及彼地触及了生命中更为深层次的东西。
由此而言,即便在爱情小说中,也存在着“言情故事”与真正优秀的“爱情小说”的不同,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以爱情事件为目的,后者则以爱情事件为借花献佛的手段,呈现出更为深刻的人性奥秘。事实上,这也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和《飘》这样的小说的伟大之处。安娜的悲剧显然比“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地爱上了别人”的问题更复杂。让安娜走上不返之路的不是渥伦斯基不再爱她,而是爱情本身的困境。同样,郝思佳的形象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魅力,不在于她是个爱情失败者,而是她在与终身之爱错位后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品质。
爱情之于金庸小说,无疑处于相似的情形。在某种意义上,其意义仍然在于充当了表达作者更广更深的人生体验的媒介。新武侠作家温瑞安有句话:金庸的武侠小说,能使不看武侠小说的人也看武侠小说。[6]这道出了“金庸现象”的一大特点。所谓“不看武侠小说的人”也即“不喜欢武侠小说”的读者,这些人终于“也看”起武侠小说来,这武侠小说当然除了金属作品别无其他。这意味着,他们事实上并没有把金庸小说当作纯粹的武侠小说来读。那么,他们究竟在看什么?除了“人生”二字,我想不出有更好的概括。面向中国现实,叩问人生真谛,这就是金庸小说的奥秘所在。
熟悉现代中国武侠小说史的读者不难意识到,如果说平江不肖生的小说是以江湖异闻为基础,还珠楼主的小说是以魔幻神话为特色,那么金庸小说则是以人世的悲欢离合作为基础。读金庸小说,雅俗共赏的焦点殊途同归于一个关键词:大悲大喜的人生。叩开金庸小说的“门道”最终也在于体验一种巨大的生命激情。用一位论者的话说:“金庸之书所以凌越各家者,一言以蔽,动人也。以其书中凡有情处,必深情也。”[5](P.16)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激情由何来?其源头是什么?丹麦哲人克尔凯郭尔把它归之于上帝,认为“信仰就是激情。”[7]这也无可置疑,从那些虔诚的善男信女身上,我们总是能够意识到一种激情。但困惑犹在:正所谓“回到精神并不意味着回到神学”,信仰并不是宗教的专利,精神更不只属于上帝。事实表明,“哪怕是文艺复兴以宗教为题材的绘画中,照亮艺术的也并非圣徒头上的光圈,而是人性。”[8]
事情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如何超越这种“解释的循环”?冯其庸先生的这句话,让许多人颇有同感:金庸笔下的那些侠义人物具有一种豪气干云、一往直前的气概,所以读他的小说总是“给人以激励,给人以一种巨大的力量,一种要竭尽全力为正义事业奋斗的崇高精神。”[9]这说到了事情的本质,让我们看到了金庸小说的现代性、普世性和伟大。比如在《堂吉诃德》中我们看到,这位把大风车当作魔鬼、将羊群看作来犯的敌人军队、甚至把狮子当作地狱之王而欲与之决斗的同名主人公是如此的滑稽可笑,但当我们在跟随叙事者的笔墨尽情地嘲弄他后,最终却为他留下了深深的同情。原因就在于我们理解了他的那些不合时宜的举措背后的执着,意识到了“除此之外,堂吉诃德还要寻找正义。”[10]这正是这部小说能够成为伟大小说的地方。它的成功证明了一个诗学定律,“不能被对正义的激情所激发的艺术是微不足道的。”[11]
事情当然并不能就此了断。需要进一步追究,这种激情所归属的这个“正义事业”究竟是什么?在政治学视野里,再没有比“正义”的范畴更暧昧的了。就像西方史家所说:今天被受到人们普遍赞扬的所谓“正义,在过去它的最重要任务就是确保王室的伟大。”[12]但超越这种咬文嚼字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相通的精神品质。诗人们对大海的体验,主要在于一种自由感。就像俄国诗人普希金所说,“大海啊,自由的原素!”让我把话说得明白些:阅读金庸小说的最大愉悦就在于“体验自由”。自由不仅意味着从专制主义政治中获得解放,也意味着对唯物是从的拜金主义束缚的超越,让自我成为欲望的主人。自由意味着灵性的诞生和信念的复活。
造反并不总是有理的,挟持民众为人质的恐怖主义暴力不仅是对人类文明的否定,甚至连兽性都不如。和平永远是令人向往的,安居乐业的家园总是为普天下善良的人们所珍惜。但这一切决不能以“自由”为代价。关心人类进步的思想家们始终强调:“进步的惟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还是自由。因为一有自由,有多少个人就可能有多少独立的进步中心。”[13]用哈耶克的经典性表述来讲:“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此一状态与一人必须屈从于另一个人的意志的状态适成对照。”[14]归根到底,只有确立“自由”的价值观,才会有“平等”与“正义”等伦理诉求,有“尊严”与“责任”等道德规范;只有在这样的诉求与规范中,才能拥有名符其实的“人”的位置。唯其如此,才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声音。
诚然,艺术价值不取决于“政治正确”,将擅长吟风诵月的诗人与敢于抛头洒血的革命战士相提并论并不合适。但无论如何,文学要想超越茶余酒后的谈资、道听途说的消遣,那就必须直面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复活,人的胜利,这是一切作家的梦想。”所以,如果说文学苑地里的一些精致之作,能够凭借其“优雅美学”而受人称道,那么真正的伟大艺术只能以其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赢得尊重。这种关怀只能落实于“自由”这个关键词上,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工具。这意味着尊重以人格为前提的人权。
所有这一切,从来都是那些属于全人类共同遗产的伟大艺术的共同品质。当无数时代的无数读者们为那些无数的艺术经典所深深打动时,他们之所以热泪盈眶是因为心怀感激。这些优秀的艺术作品殊途同归于一个目标:让几千年来一直跪着、甚至趴在地上的人们,渐渐懂得并努力学会站起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伟大的艺术也就是一种伟大的激情。所以从美学的角度讲,仅仅强调情感的真挚与否仍是不够的。王安忆早已意识到:情感有着自己的体积。用哲学话语来表述,情感是对价值的反应。不同的情感体积取决于不同的价值对象,最终造成了艺术品质的区分。重申这点对于我们中国人尤为必要。
二 激荡文坛,笑傲江湖
钱穆先生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观点:中国传统只言“学问”,不言“思想”,“思想”二字是西方来的。如果以陈寅恪先生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立场而言,钱穆所说无疑言之成理。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都只是一种为了谋生需要的话语游戏,真正的思想所要求的独立性与客观性在这里都不在视野之内。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独立思想的缺席导致了一个相应的后果,就是“自由之精神”的消失。德国人鲍吾刚就认为:中国人没有真正意义的“自由”这个术语。[15]这话听起来是似乎有些绝对,但细想想却不能不承认。真正的“自由”属于有自我意志的主体,而这样的生命意识是受到儒道佛三教共同排斥的。
所以当代中国学者中也有人撰文提出:“中国传统的‘自由’就是取消自由意志之后的一身轻松、无所谓和玩世不恭;中国传统的‘人格’就是自觉地扼杀自己的个性,使之抹平在‘自然’、(泛)道德、‘天理’的平静水面之下,就是坚持自己的无人格。”[16]这就是表现于庄子逃避主义哲学的“逍遥游”主张,和林语堂回避主义的“悠闲”立场。鲍吾刚认为:初看去,林语堂的小品文似乎主要在关注悠闲的价值,这种“坐在椅中的艺术”以及对中式服装的常识。但是,如果我们更加细致地阅读这些文字,我们便会有一种逐渐增强的压迫感,这种极度的无忧无虑是对人生黑暗面的麻木。而这种麻木并非来自天真,相反,它来自中国人长期以来痛苦的经历。”[15](P.386)中国士大夫传统所标傍的所谓“苦中作乐”,其实是消极地回避现实的以苦为乐,而不是积极地改变现实创造快乐。
美籍华裔学者孙隆基教授认为,如果说非洲人和阿拉伯人多少有点动物化,那么“中国人多少地有一点‘植物化’。”[17]这是很精辟的见解。与动物相比,植物虽然拥有生命,因而也算是活着,但也只是没有生命意识的“活着”而已。中国式的人道意识,也就是表现为“可怜”之心的,以维持生命为基准的,对最低级的生命状态的恩惠。显而易见,这种生存状态正是讲究“静寂”追求“圆融”的佛教思想所向往的境界。中国正统文化的“圆”的范式,正由此奠定。中国艺术精神的萎靡不振也由此而来。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文化之痛,但不能就此以为中国不具有融入世界文化、认同普遍价值的资格。像一位日本学者那样,说“民权、平等的思想并非源于法国,而是二千余年前中国古代的孔子所首倡”,[18]这或许言过其实;但认为在孔子思想里蕴含着一种崇尚自由的理念,这未尝没有依据。
诚然,孔子这里没有柏拉图式的平等“对话”、在孔子之徒中也不存在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闻名天下的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学生。但孔子毕竟还有一位敢于与他争执顶撞、并且得到了他由衷喜爱的子路,这意味着这位开创了中国精神之源的思想家,仍然有着一种愿意对话的态度。从“吾与点也”这则著名典故以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等孔子的行为踪迹中不难发现,虽然中国没有西方民主思想的传统,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天生就喜欢专制主义;中国文化中的确有着根深蒂固的无赖习性,但也决非原本就习惯于“受虐文化”。荀子说过:“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
这里的关键在于,在“中国文化”中把“正统”与“传统”进行区分。何谓“传统”与“正统”的区分?以“义”为例。被看作正统文化的“义”有两个内涵:其一,私人间的知恩回报,如《三国演义》里的关羽。这个形象之所以在历史上逐渐被捧上圣坛建庙供奉,就在于其已成为中国人“义”的典范。关羽的义气的突出表现其实不仅仅在于与刘备、张飞的“桃园结义”,而是作为蜀汉大将的他,居然在华容道上放走了刘备的死敌曹操。其后果不仅间接导致自己的被杀,也让刘备的大业灰飞烟灭。而他的行为的伦理正当性,就在于昔日他曾为曹操收留,不仅相待甚厚,还尊重有加。
其二,就是以维护上下秩序的“忠”为义。《左传·隐公四年》记载:卫国大夫石厝的儿子石厚与公子州吁同谋杀死桓公,作为其父的他就把石厚抓获杀掉。成为后世“大义灭亲”的范例。此举有两个关键点:一、父杀子;二、儿子参与公子的谋反活动,对主君不忠。这两种义都显得冠冕堂皇,但有个共同点:不讲是非。这是中国正统文化。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这种文化形成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儒生董仲舒,所谓“君者民之心,民者君之体。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虽然在他的“春秋之治,以人随君,以君随天”中的学说中,还有试图以“天”对君权的独裁进行抑制的设计,强调“故屈民而伸君,屈君以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但事实上大权在握的皇帝以天自居,只剩下了“屈民忠君”的内容。
沿着这样的历史轨迹,也就能更好地理解辜鸿铭所提出的,真正的中国人可以称之为被驯化了的动物这个著名观点。他认为,对皇帝的“忠诚教”即男人之道,为男人献身的“无我教”是女人之道。只有弄懂了这两种教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男人和真正的中国妇女。[19]我们也同样能够理解雷海宗先生的总结:“二千年来中国总是一部或全部受外族统治,或苟且自主而须忍受深厚的外侮;完全自立又能抵抗外族甚至能克服外族乃是极少见的例外。”为什么秦以上为动的历史,历代有政治社会的演化更革。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为简单起见,我们可以称它为‘无兵的文化’。”[20]
由这种愚蠢驯服的忠诚与无我的个体组成的无兵的文化,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所谓的“正统”就此产生。显然,中华民族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但“传统”未能得到延伸。真正控制中国政治的,乃是有着大儒身份的董仲舒所代表的阴阳学说。[21]但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貌合神离,后者以孔子的“仁”为根据,这尤其表现于对“孝”的解释上。在孔子而言,孝决非盲目被动地服从,而是一种主动关怀。有人请教他:“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明确否定,告之:“父有争子,是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孝经·谏诤章第十五》)体现于君臣关系上,决非单向的上尊下卑的服从,而是双向对等的关系。
从孔子的视野看去,能够真正以礼待臣的君决不可能是专制独夫。“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这个思想由孟子和荀子作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比如《孟子·梁惠王下》记载:曾有人问孟子,周武王伐纣,这种以下犯上、以臣弑君的行为是不是忤逆作乱?孟子明确回答:我没听说有这样的事,只知道杀一独夫民贼。同样,《荀子·子道》也有“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话。由此可见,在正统文化中,能与“仁”相提并论的“义”作为伦理范畴的提出,强调的是其在世俗权力和亲情私谊之上的价值。尽管这种思想未能真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但毕竟它是中国思想之源,也为金庸先生借武侠叙事而创造现代小说提供了可能。
无须赘言,这是金庸先生反复重申,“武侠小说中的道德观,通常是反正统,而不是反传统”[22]的道理所在。问题的症结在于真正个体意识的缺席和个性的尊重。当一些有识之士诚实地提出“作为个人,传统中国人是完全绝望的”[16](P.8)这样的观点,无奈地发出“我们是个需要被拯救的民族”[23]这样的感叹,我们不能不为能让每个中国人真正挺直脊梁、自尊自强的中国精神的缺失而悲哀。这样的精神存在吗?我们需要到哪里去找?毫无疑问它是存在的,正是凭借这种精神,中国文化才曾在遥远的先秦时代有过一段令人怀念的辉煌。也正是因为中国传统中有这种精神,现代中国才有走向未来的真实希望。这种精神存在于与儒家学说貌合而神离的孔子思想。通过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与“正统”之分,有助于我们还孔子思想以本来面目,从而去认识真正的中国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拨乱反正”。有评论家提出,在现代的民主、科学、平等、自由、博爱等一系列观念中,金庸重点选取了自由,作为他对传统文化革新的突破点。认为在《笑傲江湖》里,“令狐冲决不单单是道家思想的代言人,他的身上还浸透了近代的自由精神。”还有论者强调,“要懂得武侠小说如何开导一个人走向自由王国,《笑傲江湖》不可不读。”也有学者评价《笑傲江湖》,是一部“自由与正义之书”,认为“令狐冲有一种自由自在的心态与自由创造的精神。”*以上参见卢敦基《金庸小说论》,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93页;曹正文《金庸小说人物谱》,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28页;韩云波《金庸妙语〈笑傲江湖〉卷》,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287页。这些见解很精辟,笔者也能为此再提供一份根据。1997年4月4日傍晚,我陪同金庸先生在杭州金沙巷文化村用餐。席间我向他请教:在那么多大侠中,有无可能只选出一位代表性角色?
金庸先生想了想后表示可以作这个选择,而此人物非令狐冲莫属。我明白,金庸先生此说并不是认为《笑傲江湖》是他最好的作品,而是指这部小说在他的创作中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对一种自由精神的弘扬,用金庸写在小说“后记”里的话说:“‘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追求的目标。”这种立场有意无意地始终贯彻着金庸的侠义叙事。事实上,让诸多“拜金者”能够通宵达旦读金庸小说而乐此不疲,也就是对这种精神的体验。所以,从“自由意识”强调金庸小说的现代性是言之有据的。但需要作些补充。我们不能说《笑傲江湖》就是一部高举“自由主义”旗帜的书,小说不仅没有描写自由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笑傲江湖》是一部展现自由失败的书。
纵观书中的众多江湖豪杰绿林好汉和道中侠客,纷纷为权力走火入魔,渴望洒脱的令狐冲最终能够凭借任盈盈的帮助而“笑傲江湖”,但本质上这是个愿意放弃自由的人。显而易见,只要能重返师门,即便无法与岳灵珊两情相悦,令狐冲仍会“改邪归正”。到整个故事即将结束的“嵩山大会”时,书中还有一段关于令狐冲内心的描写:“后来师傅将他逐出门墙,他也深知自己行事乖张任性,实是罪有应得,只盼能得师父师娘宽恕,从未生过半分怨愤之意。”套用裴多菲的一首诗,如果说郭靖的人生可以形容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仁义故,两者皆可抛”,那么令狐冲的人生则能这样来概括:“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两者皆可抛。”
但《笑傲江湖》里毕竟还有一位不能忽略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正是他的故事昭示了小说的基调。这就是衡山派副掌门刘正风。他的“金盆洗手”无疑表现了一种追求独立人格、试图自主命运的立场。乃至于有论者因此而套用现代术语认为,“他是一位追求个性自由,追求人的权利的自由主义者。”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看,他与曲洋共同创作的“笑傲江湖曲”,以及他为此而付出了全家生命的代价的结果,是发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喊。[24]这种套用是否恰当可另当别论,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与行为无羁的令狐冲不同,刘正风对自由人生的选择是相对自觉的。但问题也正在此:他彻底失败了。刘正风本人及妻子儿女以及众徒弟惨死的下场,宣判了此路不通。
但尽管如此,不仅这部小说的确赞美了自由精神、表达了对自由的呼唤;而且我们也能够推及开去,坚持“金庸小说的关键词是自由”的结论。人们看到了金庸小说中无所不在的言情,也注意到了其前无古人的谐趣,同样还看到了金庸世界里的大侠们的隐士作派:《书剑恩仇录》里的陈家洛豹隐回疆,《碧血剑》里的袁承志远走海外,《神雕侠侣》里的杨过与小龙女隐居终南山,《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携爱归田,《连城诀》里的狄云回到遥远的雪谷,《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与任盈盈避世于西子湖边的野坡荒山。但人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事实:金庸笔下这些大侠纷纷退出江湖的隐士作派,其实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体现了他们自主命运的追求。他们的转身而去不仅是对武林体制的彻底否定,也是对总是以“集体”的名义控制个体生命意志的“大一统”文化的坚决拒绝。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金庸小说将趣味美学推进到了一个形而上的高度,将借艺术的游戏性表现了一种崇高的激情:呼唤自由。所谓“侠士道”也就是摆脱名缰利锁之道,和超越荣誉与权力之道。这种声音主要借助于贯通金庸世界的那些人物性格来体现,通过贯通带入金庸小说的那种“游戏精神”之中。不仅金庸作品里的大侠,即使是相对次要的角色也是如此。比如《神雕侠侣》的周伯通。小说第40回里黄药师感慨道:“老顽童啊老顽童,你当真了不起。我黄老邪对‘名’淡泊,一灯大师视‘名’为虚幻,只有你,却是心中空空荡荡,本来便不存‘名’之一念,可又比我们高出一筹了。”谐趣性是金庸人物的基本品质,无论正派还是反派,从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收山之作《鹿鼎记》里的韦小宝,不仅都具“有趣好玩”的品性,而且越来越强烈突出。即使在奴性十足的韦小宝身上也是如此。
这个喜剧角色将金氏谐趣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不仅让他在故事里大获成功,同时让他在读者视野中赢得了一种美学价值,以一种“消极的姿态”表现了“积极的意义”:争取自由。认为“韦小宝是自由自在的典型,是至性至情的典型,”[25]这言过其实。但韦小宝身上的确存在值得一提的伦理价值:不是作为江湖游民道德的最低级的所谓“义气”,而在于这个不愿做大英雄的无赖身上,有着不甘受人主宰的追求。小说中有一段,描写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诸人,劝说韦小宝取康熙而代之自己做皇帝。这让韦小宝大吃一惊:“我是小流氓出身,拿手的本事只是骂人赌钱,做了将军大官,别人心里已然不服,哪里能做皇帝?这真命天子,是要大福气的。”他说到做到,于是在故事结尾我们读到,韦小宝携带着多年攒下的钱财,“一家人同去云南,自此隐姓埋名,在大理城过那逍遥自在的日子。”这表现了他的世故和聪明,从中反映出他在江湖上混迹于侠客之中,虽然没有成为大侠,毕竟有点“准侠”的意味。
作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典型,韦小宝的艺术价值在于深刻揭示了中国民族性格中的一种丑陋品质,但他的美学意义则在于:虽然这是个人模人样的“坐稳了的奴隶”,但却是个不那么安分的奴隶。他脚踩江湖与皇宫两只船的目的不仅仅是谋生得利,还有一种不受约束、不被支配地享受自在空间的需要;在他的无赖哲学后面,隐隐约约地具有一种无意识的自由诉求。这是这个灰色人物所具有的一点亮丽之处,也是他之所以仍能博得人们欣赏的深层原因。不言而喻,金庸小说的这种价值主导同作者本人的性格有关。他在回顾其人生历程时,对“自己这一生过得自由自在、随心所欲”表示满足。他明确表示,虽然自己早年曾经有过当外交官的愿望,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作个“新闻工作者和不受拘束的小说家”为职业。原因只是“外交官的行动受到各种严格规限,很不适宜于我这样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自由散漫性格。”[26]但无论如何,有这种追求的从来都大有人在,唯有金庸将它成功投入其文学创造,让20世纪中国小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在这个奇迹中,不能忽略了“武侠小说”这个文类的特殊贡献。对自由的渴望不能通过祈祷来实现,而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力量去争取。和平从来不是投降的同义词,20世纪最优秀的哲学家波普尔说得好:历史一再强调着这个法则:祈求和平的善良人们要想实现愿望“必须以战止战”。[27]换言之,“我们不能把热爱和平、随时准备包括用武力来保卫它的爱好和平的人,与无论什么样的和反对什么人的战争都一概拒绝的和平主义混为一谈”。[28]就像奥斯卡影片《勇敢的心》所昭示的,渴望自由是人类本性,获得自由需要一颗勇敢的心。这正是金庸笔下大侠们的共同标记。让萧峰、郭靖、令狐冲、胡斐、杨过们区别于别的武侠人物的,就在于他们的人生轨迹早已超越了“快意恩仇”的方式,张扬着自由的精神,实现着自我的个性。
同样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对“金庸写作男性本位”这个问题,给予相对公正的评价。有道是武侠小说不仅是“成人的童话”,而且还是“男人的童话”。[29]这对于普遍采用“一男多女”叙事模式的金庸小说,似乎言之凿凿。认为金庸小说里存在“重男轻女”的不足,是不少评论家的一个共同观点。有些论者甚至还以此为据,论证出金庸写作受了有“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之说的孔子以来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听起来似乎言之凿凿,几千年来,孔子的这句话得罪了“半边天”们,成为伟大君子的一个污点。但杨绛先生有不同看法:读孔子的书感到的是位躬行君子,以此可推断他的家一定是融洽的。
在她看来,一部《论语》生动地表明,孔子是个美食家,饮食起居很讲究。这种讲究当然得由他身边的女人们照料,他的夫人一定很能干,对丈夫很体贴,夫妇间也很和谐。因此,虽然孔子嘴上把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但实际上不见得一视同仁。孔子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之说。孔子是个极具幽默感的人,所以与其把孔子此话当作小瞧女性的证据,不如把它看作“打情骂俏”的另一种方式。[30]杨绛先生的此番见解不容轻视。断章取义地对孔子思想下结论肯定不行,简单地凭借“女权理论”对金庸小说的“男性本位”观进行指责,这同样不妥。
科学史家戈革教授的见解值得注意。他一方面表示,金庸小说全都是男本位,从来不曾把女主角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这是使人深感遗憾的,因为金庸描写女子的本领似乎大于他描写男子的本领。但另一方面他也并不觉得,可以把金庸小说归咎于“男权主义”。他同时也指出:“金庸写过的男主角较少而女主角较多,而且他的男主角中很‘理想’的更少,而他的女主角们则往往各具胜长,十分可爱。这样一来,女士们挑选男士,可选之人便较少,而男士们则反之,于是男女到底不能平权。”[31](PP.91,185)这话不仅指金庸塑造女性的成功,也意味着我们应该承认金庸对女性的尊重。
对于普遍认为金庸小说擅长写女性的问题,金庸先生本人曾在一篇文章中予以承认并作出回答:“我应坦白地说,为什么我把女性写得比较好,因为我崇拜女性。”因为在他看来,女性的武功不一定比男性强,但她们具有男性所没有的一个根本优点:不把名誉、地位、面子、财富、权力、礼法、传统、教条等看得那么重要,而专注于爱情与家庭。对于有论者曾批评金庸小说,认为《笑傲江湖》中把东方不败、岳不群、林平之等“反面角色”偷练顶级武功走火入魔而呈现女性化现象,这是以男权主义立场将女性看作次等。他也明确予以了回应:“在小说的人物描写中,我把男性与女性的不同特点严格区分开来,不喜欢男性的女性化,也不喜欢女性的男性化,在我的小说里,愈是好的男人,男人气概愈强;愈是可爱的女人,女性性格愈明显。”[22](P.272)
无论对金庸的这个审美趣味作何评价,有一点无可置疑:就像脂粉气并非女性美的同义词,男子气概并不是男权主义的等价物。让男人真正成为男人,这是性别文化的必要分工。我们不能忘记,受到专制主义压迫的,如果说首先不是男人,至少也是普遍的男性与女人同样遭遇不幸。正是在独裁权威社会中,男人不成其为男人而普遍地阴柔化。就像不惜国破家亡的代价而弃武去兵,是专制皇帝的需要;专制主义统治所需要的最佳奴才,是侏儒化的男人而不是随时能够雄起的战士。所以,我们可以讨论金庸笔下的男性塑造是否真实可信具有艺术感染力,或者女性角色是否具有同样的意义,但不能指责金庸为何没有在其小说中留下能与男性分庭抗礼的女性。在金庸世界里的男女侠客们,在某种意义上殊途同归地都成了一个东西:自由精神的符号。
事实上,这也是金庸小说中情感生活的特色。金庸小说中一切情感的核心,是一种心心相印性灵相通的真挚友情,它是亲情的扩展,也是爱情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小说中对男女主人公之间爱情关系的描写,既有肌肤之亲和容貌的吸引,但更有超越肉体生理层面的心灵的契合。无论是陈家洛与香香公主喀丝丽,还是《倚天屠龙记》中张翠山和殷素素,以及《碧血剑》里的袁承志与温青青、《飞狐外传》中的胡斐与袁紫衣等,莫不如此。这既非“少年夫妻老来伴”式的传统中国的无欲之性,又不同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种欲望之情,而是以真挚友情为底色的、转化为一种亲情的爱。比如,金庸世界里最令人难忘的两段爱情:《神雕侠侣》杨过与小龙女之间的心心相印,以及《笑傲江湖》中令狐冲与任盈盈情投意合。
有位哲人说过:如果将爱情与其整个非现实的性质相分离,那么爱情的现实性便会被破坏殆尽。[32]换言之,爱情的“现实性”恰恰在于它的“不现实性”。爱情之所以浪漫美好,在于其本质上就具有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乌托邦”性。这是它往往借文学艺术的媒介而得到呈现的原因。金庸的上述作品,可谓将这种性质表现得十分到位。但这意味着,金庸小说中的爱情,在将爱情的理念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同时,其实已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那种以身体需要为本位的男欢女悦之情,而成了以友情为基础的转化为亲情的感情。这种感情的核心是人性的解放,意味着心灵摆脱名缰利锁甚至荣誉与权力等世俗欲望后,进入一种自由自在的境地。
林语堂说,人生的大骗子不只有两个,而实有三个:名、利、权。其实还有一点:性。《笑傲江湖》之所以能成为金庸小说精神的代表,就在于对这些作了最深刻的揭示。诚如金庸先生所说: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可能的,解脱一切欲望而得以大彻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而在江湖世界,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33]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方面看,自由的真正实现往往都无从谈起。但这恰恰也正是自由理想的意义所在。我们不能因为自由的不易实现而放弃对它的追求。这种追求并不是英雄豪杰们的专利,同样是芸芸众生的权利。因为这种追求并不要求行为上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更不意味着任性狂放为所欲为;最重要的是观念意识上走出自我中心的小格局,成为自己意志的主人。
在金庸小说里,有着太多的为情所困的悲剧。比如《神雕侠侣》里的李莫愁、裘千尺、郭芙,《天龙八部》叶二娘、阿紫、马夫人等皆是“因爱不成而生恨”的悲情角色。这些角色无疑有爱的权利、情的需要,她们的悲剧的成因在于被自己的这份情所困,成了欲望的囚犯。而在《笑傲江湖》中,这种“欲望的迷失”除了更多地体现于权力的迷失,也在于某些看起来不无正当理由的行为。比如林平之的复仇。“笑傲江湖”的故事从林平之父母被害、“福威镖局”被灭的惨案开始,因此,当林平之偷学辟邪剑法而如愿杀掉青山派掌门余沧海,读来给人的感受十分复杂。这个人物有着清晰的变化过程,出场时是位有正气、会任性的富家少爷,渐渐被家仇血恨所淹没,其全部生命意识被“复仇”之念所遮蔽。最终也步入歧途,成为残忍狠毒的畸形人。
所以作者对他的描写由褒而贬,读者同情其不幸,唾弃其对岳灵珊的绝情无义。与林平之形象的由美而丑不同,小说中的仪琳姑娘给人的感受是美的不断升华。理由无他,就因为尽管她被认为是“金庸所写的一切女子中最纯情最不幸者”,[31](P.133)但她却表现得十分从容坦然。她不仅明知自己的情思不可能有任何结果或回报,而且也不要求任何回报地去爱。仪琳不仅体现了名符其实的纯情,而且还揭示了这种情感的实质:在一种理性掌控中的精神自由。与其说这是令狐冲的幸运,不如讲这是人性的胜利。通过这份美丽,金庸从“男性本位”的叙事视角实现了对女性的赞美。这是金庸的侠义故事与众不同之处。无论是浪漫无比的爱情故事,还是出人意料的江湖传奇,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其实都只是作者表现其自由理念的媒介。
让我们再回到本篇开头,去面对“金庸小说何以伟大”的问题。18世纪英国学者约翰逊,在其《词典》的序言中写道:每个民族的主要光荣都来自作家。对20世纪后期迄今的中国文学,金庸小说无疑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这样的荣誉,在古往今来的伟大小说家阵容中,金庸小说理当拥有一个属于它的位置。
[1]温瑞安.析雪山飞狐与鸳鸯刀[C].//金庸茶馆:第6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174,251.
[2]陈墨.金庸小说之迷[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61.
[3][智]巴勃罗·聂鲁达.回首话沧桑[M].上海:知识出版社,1993.410.
[4][美]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6.
[5]舒国治.读金庸偶得[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
[6]温瑞安.谈笑傲江湖[C].//金庸茶馆:第6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8.
[7][丹]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43.
[8]高行健.文学的理由[M].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134-135.
[9]冯其庸.读金庸小说[M].//金庸.金庸散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363.
[10][俄]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371.
[11][美]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17.
[12][法]乔治·索雷尔.论暴力[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81.
[13][英]约翰·密尔.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76.
[14][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1997.4.
[15][德]鲍吾刚.中国人的幸福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45.
[16]邓晓芒.人之镜[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8.
[17][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58.
[18][日]桑原隙藏.东洋史说苑[M].北京:中华书局,2005.257.
[19]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85.
[20]雷海宗.中国的兵[M].北京:中华书局,2005.86-89.
[21]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16.
[22]金庸.金庸散文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251.
[23]薛涌.学而时习之[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243.
[24]曹布拉.金庸笔下的奇男情女[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168.
[25]韩云波.金庸妙语《鹿鼎记》卷[M].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1.288.
[26]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M].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1998.150.
[27][英]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0.
[28][法]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小爱大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208.
[29]曹正文.金庸小说人物谱[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39.
[30]杨绛.走到人生边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31-134.
[31]戈革.挑灯看剑话金庸[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2][法]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6.11.
[33]金庸.笑傲江湖:后记[M].北京:三联书店,1994.1592.
(责任编辑:朱晓江)
BeautyofJustice——OnReadingJinYong’sNovels
XU Dai
(School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The significance of Jin Yong’s novels can not be denied, but their values need to be further analyzed. If we look at his works by adopting the proposition that “while good novels reflect the charm of literature and art, great works represent a high spiritual level”, Jin Yong’s works are not only often so-called “good novels” but also “great novels” which can be compared to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This is because his martial arts novels artistically reflect a kind of Chinese spirit, whose core is the “Tao of chivalry”, and have made successful literary interpretations of “aesthetic emancipation” and “poetic justice”.
Jin Yong; martial arts novels; aesthetic justice
2009-12-2
徐 岱(1957-),男,山东文登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院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美学学会会长。著作有《美学新概念》《基础诗学》《批评美学》《小说叙事学》等13部。
I206.7
A
1674-2338(2010)01-005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