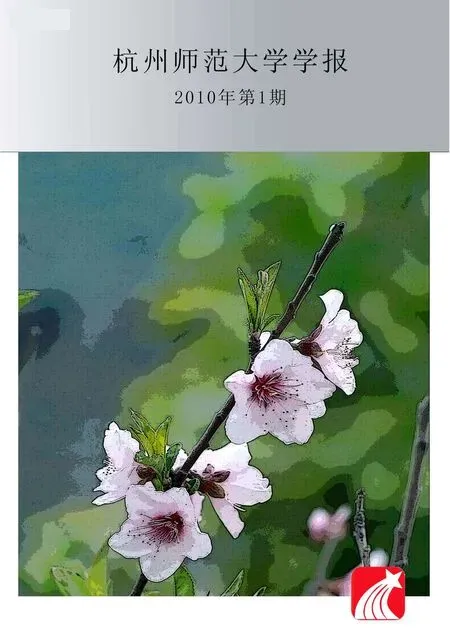唐君毅、牟宗三的阳明后学研究
林月惠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台北 11529)
唐君毅、牟宗三的阳明后学研究
林月惠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台北 11529)
阳明后学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其中唐君毅与牟宗三的阳明后学研究尤其重要,他们对于阳明后学问题意识的抉发,义理论辩的疏解,彰显了阳明后学研究在哲学上的高度与深度。尤其,唐君毅着重“融合”,牟宗三强调“判教”,各显特色,使阳明后学研究中“本体”与“工夫”两面论述,充分地辨明与融合。他们的哲学洞见给予后续研究者极大的启发,也带给当今学术界源源不绝的动力。
唐君毅;牟宗三;阳明后学;悟本体
一 阳明后学研究的契机
在宋明儒学的研究上,朱子(名熹,号晦庵,1130-1200)与王阳明(名守仁,1472-1529)思想的相关研究汗牛充栋,成果斐然。近年来,两大家门弟子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关注与重视,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为宋明儒学的研究另启新局。尤其,阳明逝世后,其亲炙或私淑弟子藉由大规模的讲学活动,宣扬阳明思想,产生各具特色的理学家,主导中、晚明的思想界。故黄宗羲所编《明儒学案》,王门的篇幅最多。本文所谓的“阳明后学”,即是指认同阳明思想,并对阳明思想加以阐释的王门弟子。其范围包括《明儒学案》所列举的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加上《止修学案》《泰州学案》之诸子。学界或以“阳明学派”、“王学”、“王门诸子”、“阳明学”、“阳明后学”*如嵇文甫《左派王学》(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麦仲贵《王门诸子致良知学说之发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书,所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大多以阳明门人为主。吴震认为阳明后学有广狭两义之理解,从广义上说,凡是阳明以后信奉阳明心学或在思想上受阳明心学影响的学者都可纳入阳明后学的研究范围,比如明、清时代乃至现、当代的一些学者都可以作为其研究的对象;从狭义上说,阳明门下及其再传弟子(包括与阳明有明确师承关系者)可以算作阳明后学的研究范围,比如黄梨洲《明儒学案》中的“王门学案”便是主要的研究对象。参氏著《阳明后学概论》,《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2卷第3期(2002年9月),第105页。笔者同意吴震的看法,本文所谓“阳明后学”采取狭义之理解。称之,名称虽有不同,其指涉则相同,本文乃以“阳明后学”概括之。
值得注意的是,“阳明后学”的思想内容并非阳明思想的复制品,而是对阳明思想的多元阐释,呈现绵密的思想论辩与理论创新。故黄梨洲乃言:“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1](《发凡》,上册P.17)当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1909-1978)以“千岩竞秀,万壑争流”[2](《王学之论争及王学之二流:上》,P.351)形容其盛况,牟宗三先生(1909-1995)则感叹阳明后学之思想“幽深曲折而难明,人多忽之而亦不能解”。[3](《序》,PP.2-3)上一个世纪,由于日本收藏大量明人文集,故日本学者如冈田武彦先生(1908-2004)、荒木见悟先生(1917-)等人,对于阳明后学的研究,较海峡两岸的学者投入更多心力,颇有贡献。另一方面,嵇文甫(1885-1963)、容肇祖(1897-1998)虽然开启阳明后学研究的先声,但论述不够全面与深入。台湾学界方面,钱穆先生(1895-1990)论及明代学术思想史时,也涉及几位阳明后学的研究,偏重史料之辩证。而真正从哲学义理层面来探讨阳明后学的学者,当属唐君毅与牟宗三两位先生。不过,囿于明人文集与阳明后学之原典文献取得不易,上述诸位前辈学者对于阳明后学的研究,多依附于阳明思想之下,所根据的文本,也多以《明儒学案》所选录之文本为研究之依据,难免有其局限。
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阳明后学在海峡两岸的研究中,逐渐受到青睐。*相关研究成果参钱明《阳明后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5辑(2005年3月),第37-40页。促使这股研究动向的蓬勃发展,除大陆学术环境的改变与两岸的学术交流外,最主要的原因乃在于大量明人文集与阳明后学原典的出版。近年来,除《四库全书》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许多未见的明清文集陆续出现,充实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资源。尤其,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2007年出版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10册),以及2009年出版的《阳明学研究丛书》(11册),更奠定阳明后学研究的坚实基础,也使阳明后学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此文献丛书与研究丛书的出版,使阳明本人的文献与阳明后学文献可以相互联结,交叉运用,对于今后阳明思想或阳明后学的研究,将提供更宽广的学术视野,以及更深入的阐释。相对于前辈学者,当今学者在文献资料上占有前所未有的优势。而从当今学术界的多元发展与论述来看,阳明后学研究可以从哲学、宗教、文学、史学、经学,乃至知识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角度,进行整体的研究。就此而言,此阳明后学研究的契机,必须及时把握。然而,再多的文献资料,跨学科的激荡,若无法呈现理论诠释的深度,或是议题的创新,也是徒然。因此,回顾并省思唐君毅先生与牟宗三先生对于阳明后学研究的贡献,不仅有助于阳明后学研究在哲学义理上的深究,也可以看出两位先生之学术见解,在其百年冥诞之际,仍带给当今学界源源不绝的动力。
二 唐君毅、牟宗三的阳明后学研究概述
严格地说,唐君毅先生与牟宗三先生的阳明后学研究,必须置于两位先生整体宋明儒学的研究中来考察。唐先生对于宋明儒学的研究,集中于《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也有部分的论述。前者出版于1973年,后者出版于1974年,但其论述内容多撰于60年代。其中,涉及阳明后学研究部分,《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有四章,《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有一章。牟宗三先生的宋明儒学研究,其成果俱见于《心体与性体》三册、《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前者以八年的心血撰成,出版于1968年,后者出版于1979年,大部分论述内容撰写于60、70年代;而牟先生对阳明后学研究见于《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之第三、四、五章。由此可见,唐先生与牟先生对于宋明儒学或阳明后学的研究,从其撰述与出版时间来看,二者有密切的关联,而其内容与思路,也可以对比而观。
大抵而言,唐先生对于宋明儒学的研究,按时代先后,论及邵康节(名雍,1011-1077)、周濂溪(名敦颐,1017-1073)、张横渠(名载,1020-1077)、程明道(名颢,1032-1085)、程伊川(名颐,1033-1107)、朱子、陆象山(名九渊,1139-1192)、王阳明、阳明后学、东林学派、刘蕺山(名宗周,1578-1645)。唐先生指出,周濂溪、张横渠之论,皆由天道言及人道、圣道,二人观天道之思想方式,已经与佛家之观宇宙方式迥别,与带道家色彩之邵康节不同。濂溪以人极上承太极,重视《中庸》诚明之工夫。横渠言太和,通贯天人之道;以存神与敦化之工夫,变化气质之性。至程明道直下言合内外而天人不二之一道,以识仁、定性,下学上达为教。程伊川承明道言天人不二,更于一心之内外两面分性情,以别理气;更开内为主敬、外为穷理致知之工夫。降至南宋,而有朱、陆之分流。朱、陆之学,乃缘周、张之言天人之际,二程之言内外之际,而措思于一心中之明觉与天理之际。陆象山发明本心,近明道之言一本。朱子之主敬、存养省察、致知格物之功,以兼致中和,实出于伊川之“涵养需用敬,进学在致知”。明代阳明致良知之学,缘朱子之格物致知之论而转手,而化朱子知之理之知为天理良知,以还契陆之本心。阳明之后,良知之学遍天下,不出“悟此良知或心性之本体即工夫”,以及“由工夫以悟本体”二流。浙中之王龙溪(名畿,1498-1573)、泰州之王心斋(名艮,1483-1540)、罗近溪(名汝芳,1515-1588)属前者,浙中之钱绪山(名德洪,1496-1574)、邹东廓(名守益,1491-1562)、江右之聂双江(名豹,1487-1563)、罗念庵(名洪先,1504-1564)属后者。至于东林学派,更重格物以名善之义,以补王学专言致知之失,更求会通朱子、阳明之教。最后刘蕺山既感晚明王学之弊,又鉴于东林学派之明是非、尚节义,未必皆能本于好恶之正,故倡慎独诚意之学。蕺山认为北宋五子及阳明之学,皆统于濂溪,故本濂溪之承太极而立人极之旨,以作人极图为人谱,归宗于立人极。论述至此,唐先生指出:宋明理学之传由濂溪以至蕺山,如一圆之象,终始相生。[2](《自序》,PP.4-6)
概括上述唐先生的宋明儒学与阳明后学各家研究,着重较特殊之承先启后之哲学意义。虽然唐先生兼顾本体与工夫两面的论述,但唐先生认为宋明儒对治工夫之鞭辟入里,正是宋明儒学之进于先秦儒学之最大端,[2](《自序》,P.2)故“工夫论”是唐先生研究宋明儒学与阳明后学时特别强调的角度。就阳明后学的研究而言,其脉络为:阳明致良知→阳明后学→东林学派→刘蕺山诚意之学。从阳明后学的义理分析来说,包含浙中王门、江右王门、泰州学派之主要代表人物。由此可见,唐先生的宋明儒学(含阳明后学)研究,是顺着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而展开内部哲学义理的分析。一方面照顾到学术的纵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呈现哲学义理的分析。唐先生自称这样的论述方式为“即哲学史以论哲学”,用他自己的话解释,即是“就哲学义理之表现于哲人之言之历史秩序,以见永恒的哲学义理之不同型态,而合以论述此哲学义理之流行”。[2](《自序》,P.7)在唐先生看来,宋明儒学之诸家理论,乃是永恒的哲学义理之不同型态的表现,藉由不同时代的哲人之言,落实于历史中,而呈现其分合、同异的历史秩序。在唐先生此“永恒的哲学义理”之信念下,宋明儒学诸家所见之同异,“皆由哲学义理之世界,原有千门万户,可容人各自出入;然既出入其间,周旋进退,还当相遇;则千门万户,亦应有其通”。[2](《自序》,P.8)依此信念,宋明儒学诸家之异,必“殊途而同归”。唐先生此论述方式与信念,还有其主观面的自我期许与文化意识之弘扬。唐先生说:
原此吾之书之所以著,对吾之一己而言,乃由吾既观义理之世界之门户之不同,又欲出入其中,冀得其通,更守其至约;亦使吾之心,得多所上契于昔贤之心,更无古今之隔。对当世之学风言,……唯意在展示中国哲学义理流行之不息,以使人对此中国之绿野神州上下数千年之哲学慧命相续,由古至今未尝断,有如实之观解,以助成其亦将不息不已于未来世,而永无断绝之深信。[2](《自序》,P.9)
显然,唐先生之研究宋明儒学与阳明后学,不仅止于客观的义理分析,更有“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的承担。这样的论述方式与态度,乃本吾人之仁义礼智之心,以论述昔贤之学,本身就是一种工夫论的践履,不仅要“以学心听”,还要“以人心说”。故唐先生也称这种态度是“兼宗教性之崇信的历史考证之态度”。[4](《自序》,PP.5-6)笔者认为,唐先生之此种论述方式与态度,有其独特性,不可轻忽。
至于牟宗三先生的宋明儒学与阳明后学研究,与唐君毅先生的论述方式不同。他将宋明六百年诸儒体道之言(语言文字)视为一整体的学术发展,先作客观了解。牟先生所谓“客观的了解”包含“知性之了解”与“理性之了解”,前者指的是“意义厘清而确定之”,后者则是“会而通之,得其系统之原委”。而牟先生也认为:“理性之了解亦非只是客观了解而已,要能纳于生命中方为真实,且亦须有相应之生命为其基点。”[5](《序》,P.1)言下之意,牟先生认为研究宋明儒学,主观上必须有相应之生命为基点,客观上要作“知性之了解”与“理性之了解”。因而,牟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不是一般学术史与哲学史的写法,而是着重“义理系统之确解与评鉴”。故牟先生选取九位重要的宋明理学家为代表(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胡五峰、朱子、陆象山、王阳明、刘蕺山),全面梳理与诠释诸儒的重要哲学文本,将宋明儒学的义理系统分为三系。显然地,牟先生宋明儒学三系说属于“类型学划分”(typological distinction),他也明确地指出其根据的判准。从先秦儒学的经典来看,宋明诸儒透过《中庸》《易传》《论语》《孟子》《大学》的重新诠释,创新并缔造宋明儒学的义理世界。从本体论上说,牟先生以“即存有即活动”与“只存有而不活动”为判准,来分判诸儒对心体、性体的理解与体会。就工夫论言,牟先生也以“逆觉体证”与“顺取之路”为判准,来分判宋明儒学。因而,在“经典”(文本)、“本体论”、“工夫论”的三组判准下,牟先生将宋明儒学分为三系:第一系是五峰、蕺山系,此承濂溪、横渠至明道之一本而开出,客观地讲性体,以《中庸》《易传》为主,主观地讲心体,以《论》《孟》为主。特提出“以心著性”的义理系统,其所体证的本体是“即存有即活动”,工夫则着重“逆觉体证”。第二系是象山、阳明系,以《论》《孟》为主来含摄《中庸》《易传》,着重于一心之朗现、一心之申展,一心之遍润,所体证的本体也是“即存有即活动”,工夫也以“逆觉体证”为主。第三系是伊川、朱子系,以《中庸》《易传》与《大学》合,而以《大学》为主,所体证的本体成为一“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强调横摄认知的“格物致知”工夫,此乃“顺取之路”。[5](P.49)如果从更严格的理论意义来看(本体论),牟先生三系说的判准可以紧扣在“心、性关系”(心、性为一或为二)与“自律、他律的区分”。前者之判定需要以基本文献的解读为根据,后者之判定需要对康德哲学有深入的把握。*参见李明辉《如何继承牟宗三先生的思想遗产?》(未刊稿)。
从以上牟先生对宋明儒学的研究来看,牟先生旨在凸显宋明儒学的三种义理型态(系统),宋明儒学的“哲学义理”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也有其独立性,他关切的是“哲学问题”,既无涉于学术史的考镜源流、师承关系,也不在于符合哲学史的周全论述。换言之,哲学义理系统的确定与判定,是牟先生宋明儒学研究的主要用心所在。因而,牟先生对于阳明后学的研究,是以其三系说为框架与脉络。从时间的推移言,其脉络是:阳明思想→阳明后学→刘蕺山思想。以牟先生的三系说的义理型态来看,阳明后学是“象山、阳明系”到“蕺山、五峰系”的“过渡”,本身不成其为独立的一系。更形象化地说,“阳明后学”是“阳明思想”与“蕺山思想”间的“罅隙”,藉以弥缝二者。[3](《序》,P.2)虽然如此,牟先生也与唐先生一样,涉及浙中王门、江右王门、泰州学派的研究。牟先生指出阳明弟子中能真切于师门之说而紧守不渝者唯钱绪山、王龙溪、邹东廓、欧阳南野(名德,1496-1554)、陈明水(名九川,1949-1562)五人而已。[3](P.403)其中,浙中的王龙溪为阳明思想的嫡传,龙溪与泰州学派的罗近溪是阳明思想“调适而上遂”的发展。[3](P.288,297,310)但江右王门的聂双江、罗念庵则偏离阳明思想,误解良知,遂亦渐启离王学而归于北宋之先言道体性命者;自刘两峰、刘师泉以至王塘南则归于以道体性命为首出,以之范域良知。此义理型态乃向刘蕺山之“以心著性,归显于密”趋近。[3](P.405)由此可见,在牟先生三系说的义理型态中,阳明后学中自聂双江、罗念庵开始,其义理方向已经由“象山、阳明系”走向“五峰、蕺山系”,严格地说,阳明后学之所以有异论,只显示出其义理型态的“过渡”性格。
承上所述,唐先生与牟先生的阳明后学研究,必须置于他们二人对于宋明儒学的整体研究来考察,才能显现其特色。虽然唐先生与牟先生都对阳明后学的浙中王门、江右王门与泰州学派予以关注,但所展示出来的义理结构与论断,却明显有别。善学者若能善解其异同,必能推进阳明后学之研究。
三 唐君毅、牟宗三对于阳明后学研究之异同
(一)基本态度
从前述唐君毅先生深信“永恒的哲学义理”与牟宗三先生强调“客观的了解”的不同来看,就决定唐、牟两位先生对于阳明后学研究的基本态度。笔者曾经以“调和”与“判教”来勾勒唐、牟两位先生对于阳明后学的研究进路,[6]其基本态度亦然。尽管两位先生都注意到明代理学或阳明后学内部,出现诸多论争,但二人处理的基本态度却不同。唐先生着重论争的消解,牟先生则以阳明“致良知”教为判准,严加区分“王学”与“非王学”。
唐先生《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的《王学之论争及王学之二流》(上)、(下)两章,可视为明代儒学史的导论,值得细读。唐先生指出,在阳明学外部,有北方的吕泾野(名柟,1479-1542),朱子学的罗整庵(名钦顺,1465-1547)批评阳明学;即使与阳明同属“心学”系统的湛甘泉(名若水,1466-1560),也对阳明学提出五端批评。同样地,在阳明学内部,王门诸子对良知之理解不同,而有种种论争。值得注意的是,在唐先生看来,举凡阳明学内部或外部的论争,皆有其义理价值,若能善观善解,未尝不能消解。唐先生说:
此中之儒者相争,亦皆可自谓出于其天理良知之是非。则天理良知之是非,又何以如此无定乃尔。……然若欲见此千岩万壑,并秀平流,各得儒学之一端,合以成此明代理学之盛,而不见诸家之学,唯是以互相辩难而相抵消,更见其永恒之价值与意义,则大难事。此则须知儒学之大,原有其不同之方向。……唯学问之事,人各有其出发之始点,以有其自得之处,更济以学者气质之殊,及互为补偏救弊之言,故不能不异。而于凡此补偏救弊之言,吾人若能知其本旨所在,不在攻他之非,而唯以自明其是,更导人于正;则于其补偏救弊之言,其还入于偏者,亦可合两偏,以观其归于一正,览其言虽偏而易初无不正。人诚能本此眼光,以观此最多争辩之明代儒学,则亦未尝不可得其通,而见儒学中之无诤法也。[2](PP.351-352)
以上的说法,唐先生称之为“在明代儒学争辩中见无诤法”,并意识到“亦只是一态度”,“而本此态度以消解诤论,能作到何处,亦自难言”。因为,一旦落在语言文字,以论无诤法,也可能引起诤论。[2](P.352)在唐先生看来,儒学内部无所谓正统与异端之别,儒学之发展,原有不同之方向;而诸家学术之不同,各因其出发点,或学者气质之殊,或补偏救弊而有不同,其“意”(初衷、动机)初无不正。这样的基本态度,是从唐先生“永恒的哲学义理”之信念引伸出来的。在此信念下,儒学内部不同的见解,都窥见儒学“永恒的哲学义理”之一端,各有其本旨,研究者必须跳脱论争的双方,以更高的层次,看出诸论辩的异同而消解之。因而,唐先生研究阳明后学诸论争时,偏向“舍异求同”,希望各种论争都能在儒家哲学义理世界中,各安其位。故罗整庵批评陆、王为禅学,乃是对陆、王之所谓“心之明觉乃通性理”之义有所误解所致。湛甘泉批评王阳明“致良知”之工夫“偏于内”,阳明批评甘泉之“随处体认天理”不免“求理于外”,此相互批评于两造皆不成立,究其实,“亦可无诤也”。即使在阳明后学内部,虽有种种异同之见,但皆本于阳明原有两种相辅为用的教法:“悟本体即工夫”与“由工夫以悟本体”,故阳明后学之论争皆是这两种工夫型态的呈现,二者未必对立,“及其终亦可并行不悖”。[2](PP.354-365)
由此可见,唐先生对阳明后学研究的基本态度,偏重“调和”。在此基本态度下,其优点在于较能相应每位儒者的气质或问题意识,对其学问尽可能进行同情的理解,力求其论学的本旨。然而,由于唐先生“于论争中见无诤法”的基本态度太强,不免使诸论争乃诉诸“彼此误解”的表面理由所致,难以清晰呈现诸多论争的义理架构与义理症结所在。类比地说,唐先生此“调和”的基本态度,不是“构造原则”(constitutive principle),而是“轨约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
相对于唐君毅先生的“调和”态度,牟宗三先生的基本态度是“判教”的,此“判教”的基本态度从前述宋明儒学的三系说即可索解。运用于阳明后学的研究,阳明本人思想即是唯一的判准。牟先生在论述阳明后学之前,先以七端论点作为阳明思想之大纲脉,再以此评判王门之分歧。牟先生说:
当时王学遍天下,然重要者不过三支:一曰浙中派,二曰泰州派,三曰江右派。……浙中派以钱绪山与王龙溪为主,然钱绪山平实,而引起争论者则在王龙溪,故以王龙溪为主。泰州派始自王艮……三传而有罗近溪为精纯,故以罗近溪为主。江右派人物尤多,以邹东廓、聂双江、罗念庵为主。邹东廓顺适,持异议者为聂双江与罗念庵,故以此二人为主。本文重义理之疏导,非历史考索之工作,故删繁从简。而评判此四人之孰得孰失,孰精熟于王学,孰不精熟于王学,孰相应于王学,孰不相应于王学,必以阳明本人之义理为根据,否则难的当也。[3](P.266)
牟先生认为面对竞相辩难的阳明后学,若顺其争辩则将流于支离,难知其本;但他也不采取超越双方以弭平是非的调和态度。牟先生明确地以阳明本人义理为判准,将精熟、相应于阳明思想者归为一类,此乃“王学”正统;不精熟、不相应于阳明思想者另归一类,此为“非王学”。前者以王龙溪、罗近溪属之,后者以聂双江、罗念庵属之。自双江、念庵横生枝节后,牟先生虽详论刘两峰(名文敏,1490-1572)之“以虚为宗”、刘师泉(名邦采,生卒年不详)之“悟性修命”、王塘南(名时槐,1522-1605)之“以透性为宗言几为要”,皆属于江右王门,但已经偏离阳明思想,也纳入“非王学”之列。
事实上,牟先生的“判教”不仅止于基本态度而已,它本身也是一“建构原则”。因而,阳明后学研究在以阳明思想为判准下,只有“王学”与“非王学”之分。在牟先生此种重义理疏导、严判教的基本态度下,“王学”与“非王学”的判定,泾渭分明,属于“王学”的义理系统洁净精微,属于“非王学”的义理系统难以自圆其说,更遑论有义理上的定位,充其量只有前述所言的“过渡”价值。如此一来,牟先生对于属于“王学”的王龙溪之四无说就有精辟的阐释,对于罗近溪之拆穿光景,也予以极高的评价。甚至对二人可能引起的“虚玄而荡”、“情识而肆”之流弊,也以人病而非法病视之。[3](PP.297-298)不过,对于“非王学”的聂双江与罗念庵,牟先生虽以阳明思想为判准,指出其义理的纠结处,但对于聂双江之“归寂说”、罗念庵之“收摄保聚”说,实未能有同情且相应的理解,其内部理论是否有逻辑的一致性,牟先生也未论及。因此,在牟先生重“判教”的基本态度下,其优点在于对阳明的义理系统有更严密精微的探究,而符合阳明义理思想判准的阳明后学也有义理的定位与价值。但由于牟先生以阳明思想为唯一判准的立场过于鲜明与强烈,推至其极,符合阳明义理法度的阳明后学之思想不过是阳明思想的复制与翻版,而异于阳明思想之阳明后学的独特思想面貌或问题意识,反而隐而不彰。
(二)问题意识
由于唐君毅先生与牟宗三对于阳明后学研究的基本态度有所差异,影响所及,他们对于阳明后学内部的“问题意识”也有不同的解读。平心而论,顺着唐先生“调和”的基本态度来看,较能同情地理解阳明后学中的种种不同见解,也能正视诸家思想的特殊性与其学问用心所在。因而,唐先生对于阳明后学的问题意识,就提出很有参考价值的论点,此即是“王学之二流”说。唐先生指出王学之论争,乃由于对良知心体所见不同,工夫乃因之而异。具体地说,从阳明晚年天泉证道提出“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后,就包含两种教法:一是“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二是“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当作“净”〕了。”(《传习录》下:315)王龙溪将前者悟本体的工夫称之为“先天正心之学”,将后者落实在意念之为善去恶工夫称之为“后天诚意之学”。不过,王龙溪以“先天正心之学”与“后天诚意之学”的对扬来区分阳明两种教法,可能令人误解“后天诚意之学”无先天的根据。因而,唐先生有更深入的解释:
盖由阳明之提四句教,乃是教法语、工夫语,并非客观的讨论心意是什么。即不管意有善有恶时,心体中是否有善恶在,人总可直去悟心体之明莹无滞、无善无恶之一面,以为工夫;而于见意有善有恶时,则可以知善知恶、为善去恶。若然,则不管人是利根、钝根,皆有四句教中所言之工夫照管。[2](P.363)
唐先生认为不论是利根或钝根之人,工夫之关键都在于“悟心体”(悟本体)。亦即“致良知之学应先见得此良知本体,方可言推致之于诚意之功。若徒泛言为善去恶以诚意,则一切世儒之教,亦教人为善去恶以诚意,此固不必即是致良知之学。”[2](P.364)就此而言,致良知之学的独特处,就在于“先悟得此良知本体”。因此,就四句教作为工夫教法言,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既可作为后三句之前提,亦可说第一句之成立,乃由后三句工夫之完成方能证实。依此思路,唐先生指出阳明后学源于“四句教”而发展的两种工夫型态:一是“悟本体即工夫”,一是“由工夫以悟本体”。值得注意的是,此两种工夫型态,都指向“悟本体”。换言之,如何“悟本体”就是阳明后学共同关切的问题意识。
在唐先生看来,王龙溪与罗近溪都属于“悟本体即工夫”的型态,其要点只在悟无善无恶之心体,其实义在于:唯是“即此本体之所以为本体,以起工夫”。此本体之所以为本体者,只是一先天之虚寂灵明之心。能悟得此虚寂的灵明之心,至善而无善无恶,有而非有,而自藏密,即无待于如聂双江之以静坐归寂为转手工夫,以洗心退藏于密,而直下见此心体之即显即密。[2](P.379)唐先生也同时指出,王龙溪虽重悟本体,但亦不能谓悟本体后更无善恶意念之起,故龙溪亦不废后天诚意之学。换言之,龙溪以悟心体为第一义工夫,依此悟以致知诚意格物,则后天诚意之学才能“简易省力”。同样地,罗近溪也面对“学有以用功为先,有以性地为先者”的选择,近溪强调“性地为先”的理由是:“以用功为先者,意念有个存主,言动有所执持,不惟己可自考,亦且众所共见闻。若性地为先,则言动即是现在,且须更加平淡;意念亦尚安闲,尤忌有所做作。岂独人难测其浅深,即己亦无从验其长短。”[7](P.189)由此可见,“悟本体即工夫”才能当下彻底解决意念之潜伏与憧憧往来之问题。
不过,唐先生也指出另一种“悟心体”的工夫,即是“由工夫以悟本体”,举凡钱绪山、季彭山(名本,1485-1563)、邹东廓、聂双江、罗念庵,皆属于此一工夫型态。此一工夫型态所思考的另一方向是,人人皆有良知本体,但于现实生活中,良知之真实呈现,原有不同之程度,未免有搀杂,或其呈现未能充量(充分),或其呈现之程度不足以自任持而自贞定。故此工夫型态乃着眼于良知本体之呈现是否充量之问题,以及此良知本体是否有种种障蔽之问题。若良知本体更无一切障蔽,能充量呈现,则人之意念之发方能纯善无恶。因此,“由工夫以悟本体”之实义在于:“由此工夫方能去此障蔽之谓恶念所自发者,以实引致此一明莹无滞之心体之呈现与证悟矣。”[7](P.364)换言之,“由工夫以悟本体”仍是以“悟本体”为关键工夫所在。但却对于障蔽良知呈现的种种因素,逐步加以克治,或透过“无动于动”(钱绪山)、“戒惧于本体”(邹东廓)、“于本体警惕”(季彭山)、“归寂”(聂双江)、“收摄保聚”(罗念庵)等具体的工夫次第,使良知本体充分呈现。凡此工夫皆有“对治相”“工夫相”,但其工夫的重点并不在意念交杂时的对治,而是拨除障蔽,使良知本体充分呈现。诚如双江所言:“所贵乎本体之知,吾之动无不善也。动有不善而后知之,以落第二义矣。”[1](卷17,P.374)
唐先生以“悟本体即工夫”与“由工夫以悟本体”来掌握阳明后学工夫论的两种型态,凸显阳明后学的问题意识在于“悟本体”,对于阳明后学研究具有启发性,后续研究者不能轻忽此问题意识。根据阳明“致良知”教的义理,“悟本体即工夫”与“由工夫以悟本体”都是以“悟良知本体”为第一义工夫,二者皆是先天立体(立本)之学,其相异处在于“工夫相”、“对治相”的有无,或是“顿入”、“渐入”的不同。龙溪也曾以“即本体为功夫”、“用功夫以复本体”来表述*王龙溪《松原晤语》云:“夫圣贤之学,致知虽一,而所入不同。从顿入者,即本体为功夫,天机常运,终日兢业保任,不离性体,虽有欲念,一觉便化,不致为累,所谓‘性之’也。从渐入者,用功夫以复本体,终日扫荡欲根,却除杂念,以顺其天机,不使为累,所谓‘反之’也。”见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卷1,第42-43页。,但此两种功夫型态,不是截然地二分,因为就其“悟本体”言,皆是“顿入”,但从工夫次第途径言,才有“顿”“渐”之别。
另一方面,牟宗三对于阳明之四句教与王龙溪之四无说皆有义理疏导,极为精当,但在阳明基本义理的判准下,对于阳明后学围绕在工夫论上的问题意识,并未清楚地标示出来。牟先生虽然提到:
大抵自阳明悟得良知并提出致良知后,其后学用功皆落在如何能保任而守住这良知,即以此“保任而守住”以为致,故工夫皆落在此起码之最初步。如邹东廓之“得力于敬”,以戒惧为主;钱绪山之唯求“无动于动”,季彭山之主龙惕不主自然,此皆为的使良知能保任而常呈现也。此本是常行,不影响阳明之义理。[3](PP.309-310)
可惜的是,牟先生未如唐先生般地察觉到此“保任而守住”的工夫有两种不同型态的发展,也有其独特性,不能仅以“常行”工夫看待。
虽然如此,牟先生对于阳明四句教与龙溪四无说的义理疏导,也得出与唐先生两种工夫型态类似的论点。牟先生认为龙溪《天泉证道记》中所记阳明和会四有四无之言*王龙溪《天泉证道纪》记载阳明对于四有四无之会通云:“吾教法原有此两种: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见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卷1,第2页。,表述有未莹之处,义理亦有滑转。牟先生认为王龙溪以“悟得本体”、“未尝悟得本体”的对翻来表述“四无”(上根之人的教法)、“四有”(中根以下之人的教法)是不妥当的。因为若“未尝悟得本体”,如何能致良知呢?换言之,致良知必须以悟得本体为前提才成为可能,故云“致知存乎心悟”。因此,牟先生认为四有、四无俱须悟得本体(悟得良知即是悟得心之本体),上下根之分不在悟得与未悟得,而在有无对治。据此,牟先生将四有四无和会的说法修改为:
上根之人顿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一体而化,无所对治。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中根以下之人虽亦悟得本体,然因有所对治,不免在有善有恶上着眼或下手,因而在有上立根即立足,是以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3](PP.279-280)
根据牟先生的解释,无论四有、四无,上根或中根以下之教法,都必须对良知本体有一种“心悟”。若从工夫上说,四无是超越的方式,从先天入手,无所对治,必须顿悟,此即是“即本体便是工夫”。而四有是经验的方式,虽然从后天入手,对治之标准(良知本体)是先天的,此是渐教,可谓“即工夫便是本体”。但此渐教不是彻底的渐教,也不是彻底的后天之学。[3](P.273,280)事实上,牟先生所谓的“即本体便是工夫”/“即工夫便是本体”,即是唐先生的“悟本体即工夫”/“由工夫悟本体”。只是牟先生并未将此两种工夫型态的发展,作为阳明后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所在。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唐先生明确指出阳明后学的问题意识,聚焦于“工夫论”,因而,举阳明的四句教,王龙溪的四无说,聂双江的归寂说,都应从工夫论的角度着眼。唐先生此角度相较于牟先生辨析阳明四句教与龙溪四无说而见阳明义理之一贯性,实更能相应于阳明后学的问题意识。虽然唐、牟两位先生都注意到阳明的四句教启动阳明后学的诸多争论,但对于内部的问题意识,笔者愿做更详细的补充。笔者认为阳明本人与阳明后学的问题意识已经不同,阳明的问题意识主要是针对朱熹“格物穷理”之“外求”与“支离”而发,故阳明关注的是工夫的“入路”问题,“良知”一反观而自得,此是阳明的回应。但对阳明后学而言,已经无须回应此朱熹所带来的工夫“入路”问题,而是在肯认人人皆有良知本体的共识下,转向阳明提问:如何“致良知”?因为阳明后学在“致良知”的工夫体验中,大多经验到在意念上用功并对治的繁难与弊端,故“致良知”工夫必须在“良知本体”上用功。在这个意义下,“致良知”工夫的重点乃聚焦于如何“悟良知本体”或“保任本体”。阳明所谓“乃若致知,则存乎心悟”*语出王守仁《大学古本序》,见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上册,第243页,但此句标点有误,笔者改订之。最能表示阳明后学的问题意识。因此,如何在先天心体(良知本体)上用功以彻底纯化意念,是阳明后学关切的工夫论问题。这种在本体上用功的工夫趋向,称之为“先天之学”、“究竟工夫”或“第一义工夫”。大抵而言,追求第一义工夫的阳明后学,大多肯认良知本体须“自修自悟”,也多体验到“识得本体,方能做工夫”,故无论“悟本体即工夫”或“由工夫以悟本体”都是“顿教”,因为本体必须顿悟而得。但“悟本体”之前与之后的工夫途径,阳明后学的看法就不同。属于“悟本体即工夫”型态的龙溪、近溪等人,偏向“顿悟顿修”,其工夫似无具体的“次第”可言,强调“勿忘勿助,未尝致纤毫之力”、“无工夫的工夫”。属于“由工夫以悟本体”型态的邹东廓、聂双江、罗念庵等人,偏向“顿悟渐修”,似有工夫次第可持循。总之,在先天心体上用功而追求第一义工夫是阳明后学共同的问题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阳明后学所发展出来的两种工夫型态,龙溪曾借用禅宗的顿/渐范式来类比。从上述的讨论来看,龙溪提出的“即本体是工夫”/“用工夫以复本体”、“先天正心之学”/“后天诚意之学”,唐先生所谓的“悟本体即工夫”/“由工夫以悟本体”,牟先生所区分的“即本体便是工夫”/“即工夫便是本体”,以及阳明四句教的两种教法,都可上溯到《孟子》的尧、舜“性之”/汤、武“反之”,且与顿/渐范式有“家族类似性”。不过,上述阳明后学的顿/渐之分,不若禅宗“南顿北渐”般地截然二分,或具强烈的宗派意识,诚如龙溪所言:“理乘顿悟,事属渐修;悟以起修,修以征悟。”[8]此就阳明后学的两种工夫型态而言,实属持平之论。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儒学内部的工夫教法也有顿/渐之别,此问题意识从阳明晚年的“四句教”启其端,至阳明后学凸显两种工夫型态而成为清楚的问题意识。日本学者荒木见悟也点出此问题意识:
阳明殁后的思想界……关于良知体验的顿渐争论越发活泼,终于促成了新的顿悟渐修论的发生。前面已经提过,阳明的顿悟主义包含了渐、修的层次。阳明自身对于顿悟渐修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因此这个问题,与其说不是阳明思想的核心部分,不如看作是因为致良知顿渐相关的实践哲学上的论议,在此之前并未达到十分成熟的阶段所致。[9]
论述至此,阳明后学的问题意识有其独特性,掌握此问题意识,就能对辩难多端的阳明后学有更相应而深入的理解与诠释。
(三)个案义理分析
如前所述,唐君毅先生与牟宗三先生都不约而同关注阳明后学的浙中王门、江右王门、泰州学派,并对各派的代表人物进行个案的义理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对今后阳明后学内部的义理分析,仍具有指引性的作用。大体而言,唐、牟两位先生对王龙溪与罗近溪的义理分析,差异不大。但对于江右王门聂双江与罗念庵的义理分析,就出现很大的差异与评价。故笔者以聂双江、罗念庵为个案义理分析之例,比较唐、牟两位先生论述与评断之异同。
牟先生对于聂双江的思想理解,是根据王龙溪所记载的《致知议略》《致知议辩》而来,《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之第四章,就是对《致知议辩》的逐条疏解,义理辨析精微。此一论辩为阳明后学的重要论辩,牟先生的疏解有其贡献。不过,此一论辩在王龙溪与聂双江的文集中,皆有记载,双方的记载略有出入。但基于牟先生以阳明思想为判准所致,加上牟先生疏解此论辩时,双江文集也不易取得,故牟先生的疏解,以龙溪思路为主轴来批判双江的立场非常鲜明,而对双江以其归寂说之思路所提出的辩驳,则难以认同理解,正视其本旨所在,更在“非王学”的判定下,屡屡显示双江思路缴绕不通。同样地,牟先生也未详细论述罗念庵的思想,迳将罗念庵思想视为聂双江归寂说的同调,连罗念庵最核心的“收摄保聚”说,牟先生皆未提及。牟先生对双江与念庵的整体理解是:
双江与念庵底主要论点是已发未发之格式想良知,把良知亦分成有已发与未发,以为表现为知善知恶之良知是已发的良知,当不足恃,必须通过致虚守寂底工夫,归到那未发之寂体,方是真良知;若于此未发之体见得谛,则自发而无不中节矣,此是以未发之寂体之良知主宰乎已发之良知,而所谓致知者即致虚归寂以致那寂体之良知以为主宰也。[3](PP.299-300)
若参照牟先生的《致知议辩》疏解来看,概括地说,牟先生判定聂双江归寂说不符合阳明思想的义理法度有三:第一、反对“见在良知”;第二、以已发未发之格式理解良知;第三、主张工夫在归寂,格物无工夫。这三个要点,是以阳明义理为判准所得出的结论,但却未能内在于双江归寂说的思路来客观理解。
首先,就“见在良知”作为道德实践的先天根据言,它本身是个“本体论”的概念,也是诸多阳明后学的共识。但是一旦论及“见在良知”之根源性动力具足之义,就往往受到怀疑与曲解。对双江与念庵而言,因有感于道德生活的现实面中,当下良知的发用未免有诸多盘根错节的搀和,不是真纯良知本体的充分呈现,因而怀疑龙溪所谓当下呈现、当下具足的“见在良知”,恐怕是实然层面的“感性知觉”之作用,不是“良知本体”的发用。因而,对双江、念庵而言,“见在良知”是知觉,不是良知,只有“良知本体”自身,其根源性动力才是具足的。就此而言,双江、念庵虽不契阳明言“良知”的当下活动义,但他们要求肯认“良知本体”的存有义之客观性,也代表另一思路。
其次,双江有鉴于“见在良知”在工夫论上所产生的流弊,故必须严辨良知(本体)与知觉之别,强调未发之中的性体,寂然不动的虚灵本体才是良知本体,以凸显良知本体的超越性。故未发的性体是良知,已发的心之作用是知觉。此思路与阳明将未发已发紧扣于良知本体而言其隐显的思路诚然不同,但对双江而言,未发之中才是良知。其论学之重点,即在凸显良知本体作为工夫着力所在。就此而言,双江之“归寂”是工夫论的论述,它并不意味着良知不可靠,必须头上安头,无穷后返,另寻一本体来做工夫。不过,双江以“归寂”说来诠释“致良知”,致使“致”的首出意涵,由“向前推至”转向“向后复返”,此思路也与阳明“致良知”教有一间之隔。
最后,双江之言“格物无工夫”是其归寂说逻辑的必然发展。从双江追求先天之学、第一义工夫的问题意识来看,“致知存乎心悟”,故透过静坐而归寂是“悟本体”(良知本体)的关键工夫。在这个意义下,双江认为阳明“格其不正以归于正”的“格物”工夫,对于意念的对治终非究竟工夫,所谓:“动有不善而后知之,已落第二义矣。”故双江以“常惺惺”、“常存本来面目”为阳明格物之定论。“本来面目”即是“良知本体”、“未发之中”,工夫只集中于涵养未发之中。就此而言,双江认为致知、格物、诚意三者之中,只有“致知”有独立的工夫意义。据此,双江以“充满虚灵本体之量为致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为格物”,认为“工夫在致知,不在格物”[10](《答王龙溪》第2书,P.388),“格物特功效耳”[10](《答王龙溪》第2书,P.398),故宣称“格物无工夫”[10](《答王龙溪》第1书,P.382)。对双江而言,“致知”即是“归寂”,其意涵是:“充满虚灵本体之量”,亦即是“致养这个纯一未发的本体”。故“致知”(致良知、归寂)是立体(立本体、悟本体)的第一义工夫、先天之学,“格物”是致知工夫所达到的效验。依此思路,双江直接推断出“格物无工夫”。此与龙溪强调的“未尝致纤毫之力”相近,只是表述重点不同。
严格地说,若从阳明义理法度来衡定,牟先生以上述三端来判定聂双江、罗念庵之思想为“非王学”,有其精当处。然而,“王学”或“阳明后学”的判定,是否要用如此严格的义理系统来衡量,仍有商榷的余地。因为,若以阳明义理为唯一判准,则阳明后学只有“王学”与“非王学”二分,何以有异见,何以歧出,以及诸家的独特性都无法如实地显现出来,也削弱阳明后学研究的丰富性。如果从唐君毅先生的角度来看,情况就为之改观。因为,“王学”或“阳明后学”的界定若以共同肯认良知,或从追求第一义工夫的问题意识来看,范围就扩大了。亦即在“肯认良知”的共识与“追求第一义工夫”的努力下,阳明后学诸家的本旨或论辩,都可以有更相应的理解与阐释。唐先生对聂双江、罗念庵的思想论述,即是明显的实例。
唐先生把聂双江的“归寂”说与罗念庵的“收摄保聚”说都纳入王学“由工夫以悟本体”的工夫型态,由此确定聂、罗二人在王学中的系谱及其合法性。唐先生澄清聂双江的“归寂”说是工夫语,而非本体论的主张,以免除不必要的误解。唐先生内在于双江思路指出:
盖双江言归寂主静,原是工夫上事。良知本体固即寂即感,即静即动,未发而未尝不发;不可头上安头,其体之上之后,亦更无体;亦非一不能感之寂体。此乃阳明学者之共许义,双江亦无异辞。其所以必言归寂,为良知寂体,不同其当下现成之已发之用,乃自此当下现成已发之用,不必为良知本体之充量呈现,而恒不免于夹杂,更不必自知其夹杂说。于此即须先将此体,推高一层,提于其已发之用上以观,而先肯认此未充量呈现之良知之体之存在。顺此一念,便可使其良知之已发之用之流行,不免于夹杂者,得一止息之机,以还得自照见其夹杂。[2](PP.371-372)
唐先生一再强调双江“归寂”说原是工夫之语,并非意味着良知须再归寂,藉此消解龙溪或其它王门诸子对于双江“判寂感、动静、体用为二”的批评。不仅如此,唐先生还从积极面与消极面来看“归寂”说的意义。要言之,唐先生指出双江之说与为善去恶在意念上用功的工夫相较,其义自是转进一层,即:“此工夫之所以次第成就者,乃只是此心之虚灵本体之呈现,而别无其它。”[2](P.373)此为归寂说的积极意义。至于消极意义则是:“全在其能对治一般人心憧憧往来之妄动,与一般人心中良知之发用,不免于夹杂,及散于事物之感应变化之标末,而自离其本寂之处。”[2](P.372)从唐先生以双江之说“其言虽偏,而其意为未尝不圆”[2](P.373)的态度来看,他的解读既能相应地理解双江的“归寂”说,也能凸显其说的独特与用心处,其诠释较牟先生周全。
同样地,唐先生并未将罗念庵思想与聂双江思想等同而忽略之,反而对于念庵之学有极高的评价,也能正视罗念庵的“收摄保聚”说。唐先生认为“念庵与人论学最切”,其文集中之书信与短文,皆有“安闲深静气象”,更重要的是,念庵论学不同于双江之自立其说,也不同于龙溪、近溪之意在启发他人;故唐先生指出:“念庵之学,乃纯是一为己之学。”[2](PP.392-393)此“为己之学”的真切,显现在工夫受用的层层转进上,亦是宋明儒者论学最为紧要处。唐先生细察念庵学思历程有三转(三变),此说法大抵相应于《明儒学案》“先生之学使致力于践履,中归摄于寂静,晚彻悟于仁体”[1](卷18,上册P.388)之说,也取自念庵《甲寅夏游记》之自述工夫历程[11]。念庵为学之初,苦于欲根难断,无法于龙溪之“见在良知”受用,乃由双江之归寂主静之工夫入,以解决良知发现之搀和问题。后来其学更进,遂疑双江归寂说有内外之分,转而修正双江之说。最后,双江由“彻悟仁体”的体验中,悟得良知本体无内外、无寂感,良知本体虚而能通,凝聚纯一,故致知工夫在于“收摄保聚”*有关罗念庵思想之研究,参拙著《良知学的转折——聂双江与罗念庵思想之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亦详参张卫红《罗念庵的生命历程与思想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虽然念庵之学有数变,但念庵之“工夫”与其“义理”、“言说”之相应而转,唐先生站在工夫论的立场颇为赞赏地说:“此方真是本‘为己之学问工夫’,而为‘为己之言说’,以说其所见之义理者也。念庵可以当之矣。”[2](PP.412-413)显然,唐先生比牟先生更能客观且全面地理解罗念庵之思想,而其理解也与当时或后世学者对念庵的评价相近。
从上述“基本态度”、“问题意识”与“个案义理分析”来看,唐君毅先生与牟宗三先生的“阳明后学”研究,各有殊胜,也各有其特色。唐先生重“调和”的基本态度,较能敏锐地察觉到阳明后学的问题意识,也较能看出阳明后学诸家为学的本旨与面貌。而牟先生在重“判教”的基本态度下,阳明义理法度得到更精微的探究,诸多义理的分际得以厘清,但过于严格的义理判准,也可能忽略“致良知”教的多元诠释。
四 阳明后学研究的展望
唐君毅先生与牟宗三先生的阳明后学研究,其哲学的义理深度是无庸置疑的,他们对于阳明后学问题意识的抉发,义理论辩的疏解,是后续研究者的指引。牟先生于1993年应邀至第二届国际东西哲学比较研讨会作主题演讲时,所讲的题目是《超越的分解与辩证的综合》。牟先生首先指出:“超越的分解”是依康德哲学而说的,“辩证的综合”则是按照黑格尔的辩证义而说。并一再强调辩证的综合必先预设超越的分解。[12]类比地说,唐先生的阳明学研究,着重“辩证的综合”,牟先生则强调“超越的分解”。这两种研究进路,落实于实际阳明后学的研究上,前者着重“本体”与“工夫”的合一,后者充分辨明“本体”与“工夫”两面论述。就此而言,唐先生与牟先生在阳明后学研究上的哲学睿见,都给予我们后学者极大的启发。
与唐、牟两位先生所处的学术环境相较,目前是研究阳明后学的绝佳时机。随着前辈学者的耕耘,以及阳明后学研究文献与原典的大量出现,“阳明后学”也可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来探究,有其独立性,不必成为阳明思想的附属品。从哲学义理的研究来说,阳明后学文献与阳明思想的交相对比印证,可以加深两者的义理深度。又如阳明后学诸多难以董理的学术论辩,随着参与论辩者文集的出现,研究者可以透过多方文献的对比,较为持平地董理义理的症结所在,这也是深度的义理诠释。如唐君毅先生就指出阳明后学有关“无善无恶”,以及与东林学派的“至善”论辩,都需要重新深究。[4](PP.452-474)此外,明中、晚期以降的诸多“格物”说,也未有系统地予以义理的疏导。更值得关注的是,除阳明后学的内部义理发展外,阳明后学与明代朱子学或其它学派的论辩,阳明后学与释、道的交涉所丰富的“三教合一”问题,或是阳明后学与耶稣会士的种种辩难,都是亟待开发的学术领域。
当然阳明后学就其涵盖地域之广,人物之多,议题之丰富,其研究不仅止于哲学义理的探究。此研究领域更能容纳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向度。因而哲学义理的研究必须能与其它学科对话,以多元相济的态度,继续拓展阳明后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1]黄宗羲.明儒学案[M].台北:华世出版社,1987.
[2]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M].台北:学生书局,1984.
[3]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M].台北:学生书局,1984.
[4]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M].台北:学生书局,1974.
[5]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1册[M].台北:正中书局,1987.
[6]林月惠.良知学的转折——聂双江与罗念庵思想之研究[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21-24.
[7]罗汝芳.盱坛直诠[M].台北:广文书局,1977.
[8]王畿.渐庵说[M].//王畿集:卷17.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500.
[9]荒木见悟.佛教と儒教:新版[M].东京:研文出版社,1993.419.
[10]聂豹.聂豹集:卷11[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1]罗洪先.罗洪先集:上册卷3[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76-93.
[12]牟宗三.牟宗三先生晚期文集[M].//牟宗三先生全集:卷2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459-466.
(责任编辑:朱晓江)
AStudyofYangmingSchoolsofTangJunyiandMouZongsan
LIN Yueh-hui
(Insi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11529)
The Study of Yangming Schools has been given more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 in recent years, and it has become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field. This paper, based upon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fundamental attitude”,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the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cases”, analyzes and compares Tang Junyi and Mou Zongsan’s study of Yangming Schools. Their research and contribution revealed a philosophical height and depth. Especially, Tang Junyi and Mou Zongsan showed different approaches; the former stressed “dialectical synthesis” while the latter emphasized “transcendental analysis”, which proved to be obviously characteristic, caused the discourse on issues of “reality” and “cultivation”. Their insights not only inspired the later researchers but also provided the dynamics fo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in the academic field.
Tang Junyi; Mou Zongsan; Yangming Schools; enlighten the Reality
2009-12-10
林月惠(1961-),女,台湾彰化人,文学博士,,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宋明理学与中韩儒学之比较研究。
B248.2
A
1674-2338(2010)01-0022-12